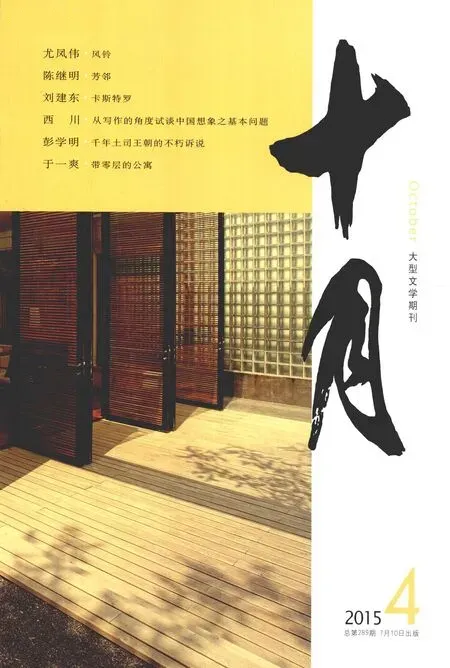鋼絲上的舞者
王干
認識于一爽的時候,還不知道她會寫小說。只知道她在一家網站當編輯。后來在《人民文學》上看到于一爽的小說,不敢相信是她寫的。問了施戰軍,果然是。原來光知道她是做網站的,是電影學院的研究生,沒想到還寫一手好小說,讓人刮目相看。于一爽說話特別逗,讓我時時想起王朔來。王朔現在封山了,小爽出山了。喜歡于一爽的小說是因為她語感非常好,語感是個不容易修煉的才華。好多小說家硬是練不出語感來,語感背后隱藏的是情緒。情緒是不好操練和模仿的,所以好的小說家是有著一般人沒有的獨特情緒。北京人的語感好,是他們的情緒里有一種反諷的情緒。而反諷,是現代小說最不可缺少的情緒。
于一爽很容易讓人想起張辛欣、劉索拉那些曾經在文壇桀驁不馴而又才情傲人的女作家。她們都不是正規學文學的,都是學藝術出身,張辛欣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劉索拉則是音樂學院的高才生,于一爽學的是電影,她們身上的藝術氣質帶到小說里,常常會開辟一番新的天地。小說家大概分為兩種,一種是藝術家型的小說家,一種是小說家型的小說家。小說家型的小說家常常是熟稔小說的歷史、套路、程式、技巧,因而小說也中規中矩,表現在形態上,常常是創作生命長,能夠寫長篇。而藝術家型的小說家,常常出手不凡,一鳴驚人,不按常規出牌,才華在瞬間爆發,流星一樣耀眼,但創作生命完成得快,也少長篇小說。
當然,于一爽與王朔更為親近。這不僅是時間上的近,而且是精神內核的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社會出現了精神信仰的危機,工業生產、物質水平的高速發展,各種矛盾不斷激化,人們對西方傳統文化以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產生了懷疑。“懷疑的精靈已經降臨”(司湯達)。無獨有偶,本土20世紀80年代后,王朔等人開始了反抗傳統話語形式的小說實踐,從而也把“懷疑的精靈”傳播到了讀者的心里,而先鋒文學則在中國延續二戰后的西方小說革命的命脈,對宏大敘事的解構日益加深,與此同時是小敘事的崛起,小敘事是90年代以后中國小說一項重要成果。這一崛起像是多方力量的合謀。提出小說發生學理論的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契說:“小說一定與一定歷史的文化結構形式之間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系,它以獨特的形式力量來重建一個史詩般的世界。”同構就是小說與現實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系。
和王朔不一樣的是,于一爽的攻擊目標不是那些宏大的敘事,不僅因為那些宏大的堅硬的玩意兒已經被王朔折騰得百孔千瘡,而是作為王朔孩子輩的80后感受的壓力已經不是外在,而是內在的存在感。他們的敵人是他們自己。于一爽小說中的年輕人處在懷疑主義盛行的新常態下,沒有信仰,懷疑愛情但相信情感,物質并不匱乏但生活中缺少存在感,他們很難參與到推動社會發展中去因而沒有都市主人翁感,他們需要“感覺到我的存在”(汪峰),一首叫《北京,北京》的流行歌曲居然有這樣的歌詞。這無疑是一種時代性的話題,“流行”已經暴露了一切,一代人的生命覺醒程度以方陣的形式達到了新的哲學高度,他們在找“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其實不是可以向社會討來的,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的糾結,自我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于一爽小說對女性主義的解構,女性主義曾經是女作家尋找存在感的利器,但過多的女性擴張和對男權的刻意攻擊,反而讓女性主義有更多的男權主義色彩。在女性主義作家那里,女性往往是愛情的受害方,或者犧牲品。而在于一爽那里,男女平等是骨子里的平等,不僅愛情,性愛也是如此。這和比較的另一個80后女作家周李立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把她們稱為中性主義敘述。
食與色,是于一爽小說經常采用的噱頭,這當然也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活。食色是本能,二者分不開,但每一代人的食色,意義完全不一樣。見面就問“吃了嗎?”也是一個時代的顯著特點,描繪饑荒的苦難敘事里面有公共記憶,而阮籍喝酒那是名士風度,他喝酒后寫文章。魯迅曾寫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批評那些學名士皮毛的人“許多人只會無端地空談和飲酒”。可是,一個時代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空談和飲酒?空談和飲酒為什么讓那么多人覺得欣悅,讓讀者覺得有趣、有味?這就不只是空談與飲酒的問題了,有人在空談與飲酒中看到遺憾,就有人在空談與酒中灌注對激情與活力的渴望,對存在的迷惘。
新作《三人食》中的“我”、楊天、王凡,《帶零層的公寓》中的嚴田、劉海東、舞蹈演員、毛小靜、齊玲玲都在找存在感。喝酒、做愛,他們通過這些參與性很強的活動,把自己和另一個生命聯系起來,從而確定“我在”。《小馬的左手》通過現實來回憶歷史的結構,但你能感到生活中的每一點能觸及小馬的痛,小馬麻木的外表更能讓人想起當年那場災難的劇痛。痛定思痛,但創傷難以愈合,痛變成了小馬家的空氣,無處可見,又處處可觸。
于一爽屬于那種藝術家型的風格,個性凜然,才情突兀,語感奇妙,《每個混蛋都很悲傷》等小說把同時代的作家嚇了一跳,而小說集《一切堅硬的都煙消云散》居然再版,可見她的小說風格征服了讀者。于一爽天性里的對人性、對情感的敏銳把握和奇特表達,幾乎是流出來的,但我隱隱擔心這種自然流淌會曲終人散,因為藝術家型的小說拼的是才情,而才情不是無限可以揮霍的,沒有其他支撐、其他資源輔助的才情是脆弱的。于一爽得天獨厚,有著張辛欣、劉索拉、徐星一撥人的語言氣勢,但又是當下年輕人的情緒特征。再一個或許是學電影的緣故,她的小說的場景經常跳動,時不時好像有音樂穿插進來似的。這就讓她的小說現代質地強烈,敘事是帶著旋律和鏡頭搖曳的。北京青年作家往往一鳴驚人,但好像任性而不韌性,常常流光耀眼,轉瞬又淡忘于江湖。張辛欣、劉索拉、徐星等當年的嬌子們遠離文學,留下一聲嘆息。
于一爽會不會呢?讀了她最近的作品,擔心有些多余。她不再是當年那種正面強攻的憤青做派,而喜歡在藝術上經營,尤其喜歡從側面去展現時代和人的印記。這種從側面落筆,從日常生活的場景去呈現內心的風暴和歷史的記憶,是現代小說攻克的難題。理查德·耶茨、理查德福特、門羅、卡佛等小說家對此都有深刻的體驗,于一爽委身于這種技術型的行列,說明她不想做一顆耀眼的流星,她想寫得長久些,不僅是為了寫長篇。另一方面,于一爽的敘事技藝不僅融匯西方,也是對一些非主流作家成功進行了移栽。她自己在創作談中就說過受到南京作家韓東、朱文的影響,她作品的京腔下有南方文體的特征,輕逸、輕靈,思絮如織,江南煙霧一般。京腔和北京,都不再是于一爽小說的單獨符碼。北京——“北上廣深”一線現代大都市之一,所以,南京和南方的文體,也不是于一爽這文體的唯一特征,她是承接南方作家的技藝,當然,敘事方式中也會帶著看問題的方式。不可否認的是,于一爽小說實現了南北交融。她的敘事作品,是一種“北腔南調”的聚合物,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話語平臺。如果不想到我們是在這樣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我們幾乎無法想象一個年輕的80后作家能完成這樣的整合。
于一爽的寫作采取的是一種近乎走鋼絲的方式,優美,高蹈,但風險系數比一般作家也要大得多,因為她沒有安全帶,隨時可能落地。另一個風險在于,才情與節制的關系如何把握,也是兩難。
責任編輯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