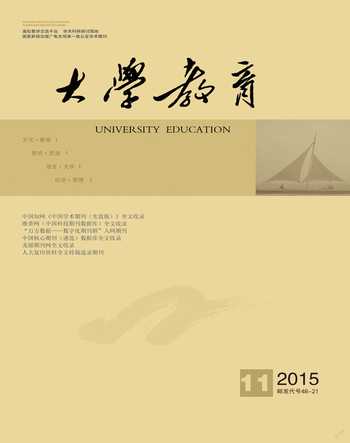功能理論下應用型口筆譯人才的培養
吳瀛 李珊珊
[摘 要]“功能派”作為一種研究范式,不僅是重要的翻譯研究切入點,也為應用型翻譯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其吸納了語言學、交際學、翻譯學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理論,才形成了今天的研究視角。在筆譯培訓初期,教師應當指引學生“四步走”的方法,用“項目化”方法進行日常訓練。在口譯培訓中,借鑒筆譯的“翻譯綱要”,對不同的口譯場合、口譯對象和口譯形式作出基本判斷,進而采取相應的口譯策略。在翻譯教學研究中借鑒傳統功能派的研究日漸廣泛,但功能派缺乏對微觀翻譯過程的進一步解析。研究者仍需要進一步借鑒社會人文科學的科研手段,幫助教師進一步了解學生,促進應用型翻譯教學的調整。
[關鍵詞]功能派 目的論 應用型 教學
[中圖分類號] H319.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11-0096-03
一、“功能派理論”的發展及評價
翻譯功能途徑在譯界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最早由韓禮德的功能語言學發展起來。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提出了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Halliday,1984)。翻譯,特別是筆譯,是書面語言標記在原語言和目標語言之間的轉換(孫致禮等, 2010),或是尋找概念、意義甚至是交際上的“對等”。譯者憑這個概念,可以從不同層面去思考“翻譯單位”的選擇:如果翻譯的重點在于語法和詞匯,那么翻譯單位較小,譯者的思維層面比較微觀,對應的翻譯策略可能偏向直譯或硬譯;如果翻譯單位較大,放在句段以上的語篇層,則要求譯者的思維層面更為宏觀,對應的翻譯策略可能偏向意譯和改寫。張美芳(2005)指出通過功能途徑,可以從微觀上進行翻譯分析,亦能從德國的功能派理論出發,進行翻譯的宏觀分析,如韓禮德的系統功能模式被芒戴(Munday,2001)評價是語篇分析中影響最大的分析模式,可以視作后來德國功能派的理論基礎之一。
盡管“功能”對于語言學和翻譯學來說并不陌生,但是“功能派”(Functionalism)的正式提出,由德國海德堡大學的賴斯(Reiss,1977)奠定了基礎——“翻譯應視特殊需要,有其特殊的追求,譯文與原文可能會有不同的功能”。弗米爾Vermeer(1989)師承賴斯,受霍斯—曼特瑞行為主義的影響(Nord,1997),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目的論”。該理論在翻譯界的影響一直沿襲至今。弗米爾的學生諾德(Nord,1997)則在20世紀80年代末將“德國功能派”進行總結和發展,并且提出了“目的加忠誠”的翻譯方法。
在諾德階段,已經不再思考“為什么這么譯”,而是要如何從倫理上既服務好讀者又不能背叛作者,破除了幾百年前德國學者施萊馬赫(Schleiermacher, 1813)提出的“譯者不是靠近作者就是要靠近讀者”的魔咒。諾德(Nord,1997)提到,除了將德國功能派前輩的各種翻譯理論作為指導,“忠實”也非常重要。對于譯文來說,譯者要采用“忠實”的翻譯方法,則很大可能上譯者偏向于使用直譯、顯性翻譯以及逐字翻譯,尋求語法或者詞匯意義上的對等(Nord,1997)。然而諾德的“忠誠”給予譯者更為廣泛的選擇。譯者要做到“忠誠”,只要確定誰是“委托人”即可。也就是說,譯者的產出可以偏向讀者,也可以偏向作者。
但是諾德的這個觀點,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張美芳教授(2005)提出,諾德的這個觀點有所偏頗,體現在該觀點將譯者放到了一個“從屬”的地位。譯者沒有發言權,沒有決定權,甚至沒有建議權,一切大權都操控在“委托人”手中。而且,該理論忽略了之前弗米爾提出的“目的至上”理論,偏向于譯者只對雇主負責。然而對于一些有重大價值的文本,如多文化荷載的文學作品來說,翻譯本身對于翻譯活動來說就不是完成“交易”那么簡單。這時候,譯者應當負起民族責任感,對譯作負責。假設“委托人”對翻譯任務并沒有相關認識,譯者還應當肩負著幫助“委托人”掃盲的責任。
二、“功能派理論”對應用型口筆譯教學的啟示
(一)對應用型筆譯教學的啟示
功能派在傳統研究中一直都放在筆譯研究的領域進行。而在實踐方面,亦可以看到這種研究范式為筆譯工作者提供的翻譯思維:首先,幫助譯者從宏觀上去把握原文。Reiss(1977)在德國學者Buhler(1934)的基礎上提出的文本類型學,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譯者從體裁上把握文本: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還是操作型文本。信息型文本的特點是有邏輯,文本焦點側重內容;表情型文本的特點是具有審美性,文本焦點是側重形式;操作型文本語言特點是對話,文本焦點是側重發揮感染作用 (Munday,2001)。Vermeer(1989)后來提出“目的論”,每一種文本類型,都有其譯文目的,于是譯者可以針對翻譯目的采取相應翻譯方法:對于信息型文本,如產品的功能說明書、讀者手冊、相關規章制度等,其譯文目的和原文一致,要表達其內容,翻譯方法應當用簡樸的白話文按要求做到簡潔明了;對于表情型文本,如詩歌、歌詞、概念寫作等,其譯文目的應當是表現其形式,因此翻譯方法就應當仿效并忠實于原作者;操作型文本,如新聞報導、電視訪談、廣告等,其譯文目的應當是誘導讀者作出期望的反應,因此翻譯方法采用編譯或者等效來盡可能地向目標讀者/觀眾靠近。
隨著語言的發展,有時候一個文本不可能只帶有一個功能,有可能多種文本功能重疊或交叉于同一文本當中(Munday,2001),例如廣告翻譯。廣告翻譯具備感染功能,誘使觀眾或讀者購買目標產品或接受目標概念,但是廣告同時包含大量的產品信息,真實的部分還具有信息功能,斟詞酌句、追求品牌溢價之時很有可能使用表情功能。如貴州茅臺集團“紅花郎酒”的廣告詞“醬香典范”,其中既表達出該酒的分類——白酒中的“醬香型”,又隱射出其使用的釀酒工藝。“典范”二字,強調其在白酒產品中的地位,讓觀眾潛意識中認為飲用此酒,是在延伸經典。
從功能語言學角度出發,韓禮德教授的語篇分析模式指導譯者要用語篇分析的模式去思考語境中的三個因素,即“語域”分析中的三個變量:語場、語旨、語式(Halliday,1989)。語場指正在發生什么事,所進行的社會活動性質、特點語言所談及或描述內容;語旨指交際者身份和他們的基本情況、特點、地位、角色、關系等;語式指代語言在交際中所起到的作用(Halliday,1989)。這三個方面,體現了語言中的人際功能,而語式則是語篇功能的具體體現。運用這一語言學知識,應用型翻譯人才在從事筆譯習作或筆譯工作時可以將這一語言學理論細化到具體的翻譯任務中。諾德(Nord,1997)提出,在做譯前準備時,譯者要按照語篇分析,羅列翻譯綱要,有效地指導翻譯工作,尤其是學生譯員對翻譯任務的性質、內容和“委托人”進行快速良好的判斷,從而在整體上對翻譯過程進行指導。即采用“1.翻譯綱要;2.原文分析;3.設計翻譯策略;4.開始翻譯實踐”四步走的應用型筆譯員的培養模式。如,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鄄nia San Francisco,2014)的應用醫學系在專業醫學翻譯課程中明確羅列出了“四步走”的模式。
在諾德對于功能派的集大成之作中提到歐洲傳統教學方法是“Y型模式”,即在確定具體的翻譯方向之前,對新生進行統一培養,然后根據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以及目的,分別往口譯和筆譯兩個方向進行深造。功能派認為,在最初期的培養當中,培養學生“釋義”(inter?鄄preting)的能力應當作為口筆譯方向的基礎(Nord,1997)。釋義的能力,是學生能夠正確判斷翻譯任務,初步在目標文化中重組原文本的基本能力(Vermeer,1989)。具體到筆譯教學中,學生是否能夠完成一份“翻譯綱要”,就成為了這種能力的體現。而在口譯培訓方面,國外口譯教學學者索亞也對這一方法表示支持(Sawyer,2004)。
“功能”理論中對于譯文質量好壞,采用了語篇的功能特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作為判斷標準,即銜接性、連貫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語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在應用型譯員的培養中,需要譯員在宏觀上把握整個筆譯工作:從筆譯任務的派發,到筆譯任務的評價,得出應用型譯員自我評判的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二)對應用型口譯教學的啟示
從功能途徑這種翻譯研究范式出發的口譯研究并不多見。使用功能途徑涉獵口譯研究的首先是弗米爾。受20世紀60年代法國釋意派創始人塞萊斯科維奇(Seleskovitch,1978)的目標導向觀點的影響,弗米爾形成了“目的論”,最終發展成以目標語篇為導向的研究范式(TT paradigm)(Pochhacker,2004)。
功能翻譯學派指出,口譯行為有“即時性和瞬時性”,即翻譯任務是一邊進行一邊在完成的。這一特點導致譯員的翻譯結果無法進行修改,對于口譯員,尤其是學生譯員來說,在付諸口譯行為之前,較筆譯學生更加嚴謹,必須思考口譯的場合、口譯的對象、口譯的目的,在頭腦中快速形成一個“口譯綱要”,例如:是什么級別的口譯場合,口譯的對象數量、聽眾的受教育程度、發言者的身份地位等。譯者還需要根據翻譯目的去調整自己的語域,使用正式文體還是口語化文體,進一步思考“語流、語速、語音”方面的控制和練習。
近年來從功能派的角度切入進行口譯教學研究的研究者當屬波赫哈克(Pochhacker,1995;2004)。波赫哈克認為,弗米爾參照行為理論、文化理論和互動理論,形成的目的論是翻譯活動的主控性原則,凌駕于原文—譯文對等、不變性以及忠實等諸多傳統的翻譯原則之上。在目的論的框架下,口譯活動的目的,也是由目標聽眾的交際需要和期待、情景語境以及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的。口譯活動往往是文化活動和交際活動。波赫哈克(1994)認為口筆譯在功能派的理論框架下都有交際目的(目的原則),都要有文內銜接,目標文本要和原文本相符(忠誠原則)。因此,在功能派的理論框架下,口譯作為翻譯行為,也需遭循文化翻譯和交際翻譯的原則,要關注聽眾反應,保證譯文質量通順易懂、清晰規范并符合特定語域。應用型口譯人才在口譯訓練中,要著重積累他國文化知識,廣泛涉獵,增加背景知識儲備。例如,在商務訪談的口譯場合下,譯員應當有經濟、金融的主題知識,懂得使用中英兩種語言的基本商務用語。
應用型翻譯人才的培養特別強調翻譯策略的培養,因此教師應當在“商務陪同”、“模擬會議”、“模擬新聞發布會”等現場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導學生照顧現場觀眾反應,以口譯聽眾為導向,使學生翻譯出“聽眾聽得懂的話”。同時,應用型譯員必須掌握“突發狀況”的應對策略,如發言者聲音過小,突然脫稿或是由于個人口音問題影響聽力理解,譯員若想完成口譯工作,達到翻譯目的,就必須采用一定的交際技巧“圓場”。例如,應用型譯員必須要懂得在講話者脫稿說話因為邏輯不明而導致聽眾理解困難時所應采取的“補譯”和“不譯”技巧,并且在講話者出現“口誤”時能夠及時糾正。
在功能學派指導下的應用型口譯教學評估的研究和結果現在尚屬少見。波赫哈克用基于語料庫的英語—德語語言對比來做實證研究。結果證明,弗米爾“目的論”的指導思想在口譯實踐及口譯理論中具有可行性(Nord,1997)。許明(2013)指出,現在國際同聲傳譯的教學研究已經大量使用實證研究方法。
根據口譯的形式分類來看,會議口譯常常使用的同聲傳譯形式也可以采用“功能派”的路徑進行研究和教學(Pochhacker,2004)。波赫哈克認為,國際會議上的說話者和聽眾,原文本就是一個系統變量,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中影響交際。文本的功能,內嵌于交際雙方的角色、理解、心情和意圖之中,最終形成交際文本。出于交際文本的性質,要使交際成功,口譯產品的文內互文性、銜接性要求特別高。在做會議口譯時,譯員應當忠實于原文。會議口譯,尤其是像聯合國內的國際會議,英語只是一個“世界語”或者是媒介語。接力傳譯的時候,英語只是一個過渡語言。因此,為保證信息完整和文化荷載,譯員必須要原原本本、地地道道地傳達原文的所有內容。而且國際會議的性質決定了會議任務高于文本任務,整個會議是一個集合,而各發言人的發言原文是子集。發言人的非語言行為,包括肢體語言等,都具有行為功能。翻譯產品只有照顧到子集中發言者的言語和行為,進行適當產出,整個會議口譯的翻譯任務才算是成功。
但是可惜的是,功能途徑理論的“目的論”僅僅是一個思想指導綱領,并非具體的研究方法。當口譯作為一個“行為過程”的時候,這種囊括了語碼輸入、大腦分析、產出、聲音控制、口音、受眾的理解,以及多種感官的調動和心理狀態的波動等多種變量的行為,功能派的傳統研究方式不能夠解決口譯中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口譯產品的量化評估,譯員的焦慮情況的反饋,需要進一步介入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統計學、社會學的方法進行評價。而霍斯—曼特瑞的翻譯行為理論因為還停留在翻譯行為的角色解釋層面上,并沒有深入涉及口譯行為中其他影響因素,如文化差異、譯員心理、現場觀眾反應甚至現場口譯設備對口譯行為的影響,所以尚不足以支持口譯行為的研究。
三、結論
綜上所述,“功能派”作為一種研究范式,不僅是重要的翻譯研究切入點,也為應用型翻譯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根據功能途徑研究者的建議,在筆譯培訓初期,教師應當指引學生“四步走”的方法,用“項目化”方法進行日常訓練。在口譯培訓中,借鑒筆譯的“翻譯綱要”,對不同的口譯場合、口譯對象和口譯形式作出基本判斷,進而采取相應的口譯策略。在翻譯教學研究中借鑒傳統功能派的研究日漸廣泛,但功能派缺乏對微觀翻譯過程的進一步解析。研究者仍需要進一步借鑒社會人文科學的科研手段,例如使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運用實證研究手段對翻譯產品進行量化研究,甚至借助神經科學對譯者的大腦進行剖析研究等,都能幫助教師進一步了解學生,促進應用型翻譯教學的調整。
[ 參 考 文 獻 ]
[1] Beaugrande,R.de and W.Dressler.Introduction to Test Lin?鄄guistics[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1.
[2] Buhler,K.Sprachtheorie:Die Darstellungsfunktion der Spra?鄄
che[M].Stuttgart:Gustav Fischer,1934.
[3] Halliday,M.A.K.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鄄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84.
[4] 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5] Nord,C.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7.
[6] Pochhacker,F.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New Yo?鄄
rk:Routledge,2004.
[7] Pochhacker,F.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Cultural Trans?鄄feror‘Voice-over Text?[A].In Snell-Hornby et al.(eds.),1994:169-78.
[8] 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In Chesterman.A.(ed.)Readings in Trans?鄄lation Theory[C].Finland:Oy Finn Lectura Ab,1977.
[9] Sawyer,D.Fundamental Aspects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M].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2004.
[10] ?Selekovitch,D.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M].Washington,DC:Pen and Booth,1978.
[11] ?Vermeer, H.J.‘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in Venuti L.(ed.)s2000.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
[12] ?孫致禮,周曄,等編著.高級英漢翻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10.
[13] ?許明.論同聲傳譯研究方法[J].中國翻譯,2013(1):99-110.
[14] ?張美芳.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覃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