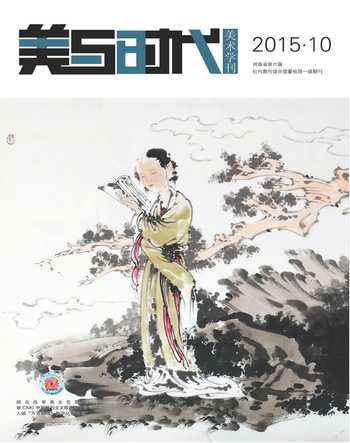芻議張掖大佛寺西游取經圖壁畫的文化價值
李慧國 張多金
摘 要:張掖大佛寺西游取經圖壁畫自20世紀90年代受到學界關注以來,逐漸成為大佛寺乃至張掖“絲路文化”“《西游記》文化”的一張名片。該壁畫以其高度概括的故事結構、精湛的藝術表現及獨特的描繪題材而具極高的文化價值。
關鍵詞:大佛寺壁畫;西游取經圖;文化價值
本文系2013年度河西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基金項目“張掖大佛寺佛教壁畫及其保護研究”(項目編號:QN2013-16)研究成果。
張掖大佛寺臥佛殿內現存一幅大型西游取經圖壁畫,該壁畫長約4.4米、寬約2.95米,面積約13平方米,位于室內涅槃佛像背立面的正中位置,畫前原有雕塑一尊,現供奉地藏王菩薩。壁畫環繞原有雕塑呈左右兩翼對成形式,以連環畫手法描繪《西游記》小說中的十處故事情節,分別是:大圣殷勤拜南海、悟空大鬧金山兜洞、心猿遭火敗、嬰兒戲化禪心亂、觀世音甘泉活樹、觀音顯像伏妖王、斷魔歸本合元神、圣僧恨逐美猴王、孫行者二調芭蕉扇、禪主吞餐懷鬼孕。此畫以重修大佛寺碑、銘文獻所載時間推算其繪制時間當不早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故學界亦客觀地稱其為大佛寺《西游記》壁畫。該壁畫作為大佛寺的重點保護文物,以其高度概括的故事結構、精湛的藝術表現及獨特的描繪題材而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下文便逐一論之:
一、文學價值
大佛寺此壁畫是《西游記》小說文學從明末以后在北方邊遠地區有效的視覺傳播。吳承恩百回本《西游記》小說問世以來,因其個性鮮明的人物角色與奇幻生動的故事情節深受民間婦孺喜愛,時至今日,《西游記》小說已然成為依托繪畫、戲劇、影視等形式在民間傳播力度最深遠的古代小說文學。早在明代萬歷、天啟年間,江南地區已經有大量《西游記》版刻插畫盛行,較有代表性的如世徳堂本、楊閩齋本、李評本等,清代亦有大量刊本行世,如康熙年間的證道書本、稀世繡像本,乾隆年間的新說本,咸豐年間的芥子園本等。地處偏遠的河西走廊不若江南文風鼎盛,《西游記》小說的有效傳播必須依托于戲曲、繪畫等視覺形式。明清河西商旅發達,為《西游記》版刻插畫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又依托于《西游記》小說與佛教的淵源,此類題材的壁畫方能大興于河西走廊的大小寺廟建筑。與此同時,《西游記》壁畫在河西走廊的盛行也為此小說文學從明末以后在北方邊遠地區的有效傳播發揮了文本無法企及的巨大作用。
二、藝術價值
首先,構思巧妙。該壁畫選取的《西游記》十處故事情節以連環畫形式巧妙組合,表現共時性空間。十幅圖畫首尾相連,背景連貫統一、銜接自然,圍繞前方原有雕塑形成弧形對稱排列,左右各五幅畫面。為達到理想化的構圖效果,作者在李評本的基礎上做了少許巧妙的調整,如畫面右下角“禪主吞餐懷鬼孕”一節(圖1)所做鏡像化的處理等,體現了創作者巧妙的構思及高超的藝術處理能力。
其次,線描精湛。該壁畫與敦煌壁畫宋、元、西夏時期的風格相一致,都是采用先描線、后設色的方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壁畫中線描藝術的精湛。例如畫中“觀音顯象伏妖王”一節(圖2),觀音與悟空腳下祥云的表現就是采用雙勾鐵線描,層次分明、凝重圓勁,還充滿動勢,造成一種宛如即將升騰而上的視覺效應。畫中“圣僧恨逐美猴王”一節(圖3)中人物之上的溪流則采用了行云流水描法,婉轉流暢、連綿不斷,似有馬遠《十二水圖》之神韻。
再次,墨色淡雅。壁畫中的用墨與用色都體現了創作者高超的駕馭能力,畫面中暈、皴、點、染并用,色彩熟而不燥、明而不火,輕靈通透、淡雅如菊。也許是歷經歲月塵煙的洗禮,畫面反倒透露出些許沉穩淡雅的“書卷氣”。
最后,文人畫創作傾向。壁畫中除了人物形象的生動刻畫外,最大的亮點就在于大量山水背景的描繪(圖4)。對山水林木的表現達到了筆墨精妙、皴染純熟,且重在營造一種“荒寒淡泊”之意境,局部還體現了對元人畫意的追求。綜合上文論及的線描與墨色方面對傳統畫法和“文人畫”意趣的追求,都能夠體現大佛寺壁畫的創作者們已經逐步脫離民間畫工畫風拙俗的特征,越來越多地偏向于文人畫創作意趣雅致的風格傾向了。
三、文物價值
首先,該壁畫是敦煌美術的補充部分。《西游記》取經故事壁畫為佛教題材,在敦煌壁畫中也曾出現了玄奘取經的身影。另外敦煌美術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包括安西榆林石窟、東千佛洞,甚至敦煌周邊一些小寺窟的佛教壁畫都屬于這個體系。元代以后,敦煌開窟造像的風氣逐漸消停,大批敦煌畫工為了生計分散到河西走廊的其它地區,仍以當地寺窟壁畫繪制為業,這就造成了題材上的連貫性與壁畫風格上的延續性,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這批壁畫都視為敦煌美術的補充部分。
其次,該壁畫是《西游記》取經圖像體系中的重要一支。自唐代玄奘取經東歸以后,玄奘取經圖像就逐漸出現。《西游記》故事成熟以后,小說故事情節也成為視覺圖像表現尤其是壁畫創作的熱點。現今,國內《西游記》取經故事題材壁畫的分布范圍之廣、數量之眾學界并無明確統計,但在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安徽、河南、山西、陜西、四川、甘肅、青海、新疆等地都出現有《西游記》取經故事壁畫遺存。這些壁畫與《西游記》小說形成很好的互文性,成為民間解讀小說內容的主要視覺語言,與《西游記》小說相輔相成,在圖像史和文獻史的歷史長河中一直流傳至今。
四、旅游價值
首先,該壁畫是張掖《西游記》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張掖是絲綢之路重鎮,也是玄奘取經的必經之路,與《西游記》文化有著很深的淵源。至今有學者認為張掖境內的許多地名如:高老莊、曬經臺、流沙河、牛魔王洞、火焰山、八戒墩、甘泉、平頂山、芭蕉灣等都是《西游記》故事的“遺跡”。[①因此挖掘和整理民間的《西游記》文化素材就成為張掖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迫切的文化使命。如今當地政府也提出了“打造《西游記》文化品牌”的策略,大佛寺此壁畫就成為張掖《西游記》文化品牌中最靚麗的一張名片。
其次,該壁畫是絲路旅游的一個亮點。絲路旅游的核心是文化旅游,武威天梯山、嘉峪關、敦煌莫高窟、陽關、玉門關等都是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為旅游核心資源,而張掖以國家濕地公園、七彩丹霞、軍馬場、康樂草原、焉支山、馬蹄寺等景區建立起來的旅游框架都以自然生態旅游為主。因此,隨著國家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大力繁榮,文化旅游將成為絲路旅游的核心品牌。大佛寺西游取經圖壁畫在今后也必將依托大佛寺景區成為絲路旅游的又一亮點。
綜上所述,張掖大佛寺西游取經圖壁畫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文物價值及旅游價值。該壁畫也必將成為河西走廊“西游”文學、寺窟壁畫研究以及絲路文化旅游新的熱點。
注釋:
①楊國學、朱瑜章《玄奘取經與〈西游記〉“遺跡”現象透視》、何建國《〈西游記〉與張掖地名的關系探討》二文觀點。
作者簡介:
李慧國,碩士,河西學院美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美術史論。
張多金,張掖市甘州區博物館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文物保護與壁畫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