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刪除掉生命中的過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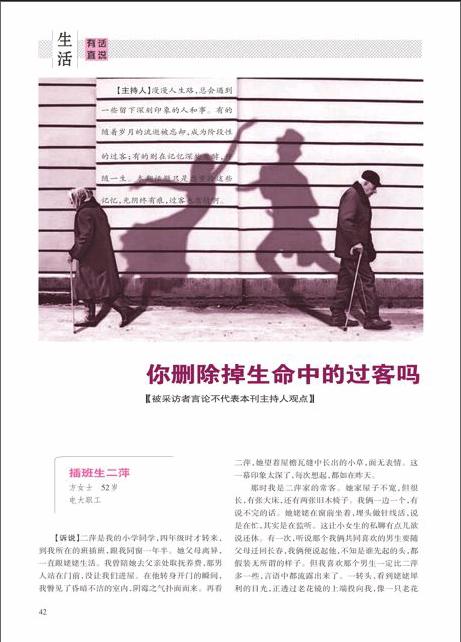

【主持人】漫漫人生路,總會遇到一些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有的隨著歲月的流逝被忘卻,成為階段性的過客;有的則在記憶深處發酵,伴隨一生。本期話題只是想重拾這些記憶,光陰終有痕,過客也有情啊。
插班生二萍
方女士 ? ?52歲
電大職工
【訴說】二萍是我的小學同學,四年級時才轉來,到我所在的班插班,跟我同窗一年半。她父母離異,一直跟姥姥生活。我曾陪她去父親處取撫養費,那男人站在門前,沒讓我們進屋。在他轉身開門的瞬間,我瞥見了昏暗不潔的室內,陰霉之氣撲面而來。再看二萍,她望著屋檐瓦縫中長出的小草,面無表情。這一幕印象太深了,每次想起,都如在昨天。
那時我是二萍家的常客。她家屋子不寬,但很長,有張大床,還有兩張舊木椅子。我倆一邊一個,有說不完的話。她姥姥在窗前坐著,埋頭做針線活,說是在忙,其實是在監聽。這讓小女生的私聊有點兒欲說還休。有一次,聽說那個我倆共同喜歡的男生要隨父母遷回長春,我倆便說起他,不知是誰先起的頭,都假裝無所謂的樣子。但我喜歡那個男生一定比二萍多一些,言語中都流露出來了。一轉頭,看到姥姥犀利的目光,正透過老花鏡的上端投向我,像一只老花貓的臉,哈哈,那真是一段好時光。
還有一個抹不掉的記憶。一個起風的日子,二萍上學遲到了,告訴老師是去送在外地工作的母親。她在眾目睽睽下走進教室,走到自己的座位,安靜地放下書包,打開了課本,看不出有什么事發生過。可是我開始想象起來,她穿著那件心愛的紫色罩衫,被母親緊緊地攥著手,在風里跟母親一同走向小城另一端的長途汽車站。車子未開動前,母親隔著車窗的玻璃對她擺手,讓她回去,說風里冷。車子開動后,母親的臉緊緊貼在窗玻璃上,看著她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一點點變遠、變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那眼里是有哀傷的。只是在那種已然習慣了送別的時刻,她與母親誰都沒有掉淚。
小學畢業后,二萍進了對口接收的中學,我“走后門”去了另一所教學質量較高的學校。我倆彼此好像都忘了打招呼,就不辭而別了。到了新學校,我快速適應環境,新同學個個鮮活生動,小學生活被漸漸淡忘,對二萍也不像開始時那么想念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跟大多數人一樣,被那個叫“謀生”的家伙綁架,不斷結交對自己有用的人。頭腦里最活躍的,都是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人和事。小小的二萍,不足兩年的同窗生活,在不知不覺中被刪除,抹鼻涕的小孩子歲月,放之生命的長河,真就是過客而已。
轉眼38年過去了,2014年5月,當年的班長建了小學同學群,用人盯人、人找人的方法,很快就將全班同學找齊。我入群是最后那批,第一眼就在頭像里找二萍。果然,在一張風景照下,我發現了她的名字,我倆就這樣在群里重逢。
春節前夕,群主張羅聚會,我倆終于見了面。她已是市政府的副局級官員,衣著端莊得體,說話滴水不漏,為人親而不昵。回到各自生活中后,我突然覺得,38年改變的,豈止一個模樣?我倆跟剛相識的陌生人相差不多,兒時那點兒模糊的記憶,咀嚼之后,就再無共同的東西了。
曾經那么的親密
趙女士 ? ?45歲
主婦
【訴說】17年前,我供職的公司攤上一場官司,成了被告。朱大姐是老板聘的律師,在業內很有名望。能請到她,是公司的榮幸,老板安排我做她的助手,協助準備庭辯,我倆就這樣認識了。
她看上去像女強人,但近距離接觸,卻很有大姐樣,跟她在一起工作,很舒服自在。一天,辦公室就我倆,一位50出頭的男人敲門進來。朱大姐一看,馬上把他請進了里屋。那是大姐的臥室,有床有衛生間,設施齊備,若忙到深夜,她就會住在這里。平時房門是鎖著的,現在竟讓一男人進入,我很吃驚。
兩人在里面待了一小時,出來時,朱大姐臉色慘白,眼睛血紅,顯然是哭了,而且哭得還挺厲害。那男人離開時,向我點點頭,門剛關上,朱大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嚎啕大哭。
我不知所措,只能坐到她身邊,不停地遞紙巾。她邊哭邊拉住我的手,說:“小趙,今晚別回家了,陪大姐一宿,我心里難受。”我一口應允,晚上,躺在里屋的大床上,她說那男人是她的初戀情人,現在是省直某機關的局長,得了晚期肺癌,日子不多了。兩人是當知青時相戀的,男人是走資派的兒子,黑五類。朱大姐根紅苗正,黨員、知青典型,前途無量。巨大的政治差異沒能阻擋熾熱的感情,兩人愛得相當投入,但一直處于地下狀態。
“四人幫”倒臺后,男人父母得到平反,他本人也順利考上大學。朱大姐則受到審查,歷時大半年,最終沒什么問題,卻錯過了高考。本想第二年再戰,報考戀人讀的大學,但男人卻在這時提出分手,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我能有今天,太難了,經歷的坎坷太多了,早就把他從生活中抹去了。但在10年后,我倆在一次省直機關大會上相遇,他已是宣傳處長,我在報社當記者,但已考取了律師證,準備辭職當律師。”朱大姐邊說邊流淚,我的鼻子也開始發酸。重逢的兩人,事業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績,年富力強,前程看好,各自也都有了和諧的家庭。百感交加之余,便是歲月締結的溫情和默契了。過去的恩和怨,朱大姐沒說,我也不好問,只知從此兩人相互關心、相互幫助,是相當親密的戰友、知己。
那晚聊到凌晨2點才睡,第二天繼續忙碌。不久,朱大姐說男人去世了,那天是最后一面。她不愧是大律師,庭辯非常精彩,案子最后庭外和解,她的工作也畫上完美句號。但我倆的交往沒有斷,那段時間,我經常去她的事務所做客,偶爾也在那住上一宿。但我懷孕后辭職做了全職媽媽,跟她的聯系就漸漸斷了。直到去年的一天,我偶遇原公司的同事,熱聊過后,她隨口說你知道不,當年代理咱公司案子的朱大姐,已經去世了,心梗,特別突然。
我大吃一驚,然后陷入深深的內疚。朱大姐以過客面貌出現在我的生活中,一度我們處得那么好,親如姐妹,本該成為一輩子的朋友,卻被各自生活裹挾著失聯。現在,她真成了劃過我夜空的流星,往日難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