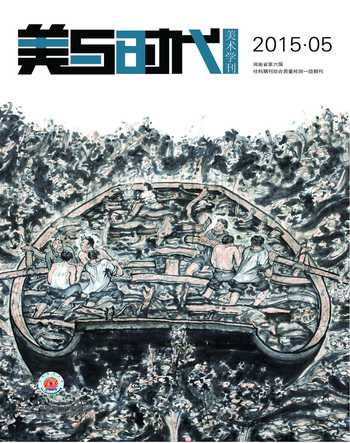被觀看的建筑
摘 要:五代關仝在《關山行旅圖》的前、中、遠景上分別刻畫了村落、棧橋和寺觀三處建筑,描繪了近30個細小的人物。這些建筑和點景人物,不僅增強了畫面的敘事性,吸引觀者,影響觀看的方法和進度,而且真正實現了山水畫情與景的統一,達到了建筑形象及其人文意義的多元呈現。
關鍵詞:建筑形象 山水畫 《關山行旅圖》
山水畫在唐代演變為獨立畫科,至宋代形成創作的鼎盛局面,此后千余年內,它一直是傳統繪畫的主要類型。五代山水,屬于承前啟后的階段,以北方的荊浩、關仝,南方的董源和巨然四位畫家為代表的山水創作,不僅促成筆墨語言、繪畫風格的成熟,也使得山水形象在地域景觀基礎上,進一步走向藝術的典型化,為宋代山水發展奠定了基礎。
山水畫脫胎于人物畫。粗略地說,它的成熟,是人物形象不斷縮小為點景元素,山水樹石不斷豐滿且獨立為藝術形象的過程。然而,人與景的交融和互動,是中國藝術審美的核心,是藝術意境確立和表現的手段,因此,與點景人物相關的人文景觀,尤其是建筑,及其象征的民居村落、交通郵驛、宗教場所、公共空間等,便成為山水畫創作探索的一個重要課題。隨著山水形象的宏大呈現,這些人文景觀,亦得到多層次的表現,由此誕生了亭、臺、樓、榭、塔、觀、橋梁、道路、水車等相應的形象體系,在四季朝暮的時間邏輯,和前后縱深的空間邏輯中,確立了形象及其語言系統,最終還逐漸形成獨立的界畫。回顧山水畫史,建筑形象在唐代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中已有探索和呈現,但只有到五代,才真正實現情與景的統一,達到建筑形象及其人文意義的多元呈現。在此,我們以關仝的《關山行旅圖》為例,予以分析。
一、建筑形象:從日常棲居到精神遠游
山水畫中的建筑,表現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空間,即日常衣、食、住、行所處的場所,大致包含日常居所和自然環境兩類。在魏晉以至隋唐時期的人物畫作品中,人物日常活動的場所往往是象征性的,以樹木和山水表示人物所處的自然環境,以樓闕、床榻、屏風、幾案等表示人物的居住空間,往往還借助這些象征性的空間符號,對畫面進行分割和連接,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竹林七賢》磚刻,楊子華的《北齊校書圖》,唐代周昉的《揮扇仕女圖》等,便使用了這些手法。人物畫中空間符號的象征性,要尋求最少的形象傳達最多的意象,因此,日常生活的空間形象,在隋唐人物畫中,便凝練至極少的境地,典型的如閻立本的《步輦圖》等。即使人物畫作品中山水形象較多,在宋元畫家看來,也往往存在“水不容泛”、“人大于樹”的弊病。
山水畫逐漸獨立的唐代,宏偉的宮闕是其描繪的主要形象,日常生活空間還未能得到深入表現。而到五代時期,對人物日常生活場所的描繪,便逐漸豐富起來,最為典型的,便是關仝的《關山行旅圖》。
《關山行旅圖》用全景構圖描繪關隴山川景色,畫中主峰高聳,河流深遠,溪岸回轉,彼此穿插。布景時,前景、中景和遠景中,依次都有建筑形象的呈現,而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建筑形象,便位于前景。平緩開闊的河岸邊,共繪有五棟房屋,或作酒肆,或為茶館,或作商鋪,或為店家居所,四周繪有雞犬飼舍、豬圈、草垛、道路等;分布其中的近20個人物,有些在屋內,或閑坐養神,或埋頭勞作,或對飲暢談,屋外的道路上,幾個旅客從河邊走來,孩童伏地嬉戲,動靜相宜;點綴其中的雞犬相聞奔走,廊檐下毛驢或立或臥,旗子斜插,全然一派閑靜。前景處的五棟房屋,三兩相對,形成一個濃縮的街區,街道結束處,是一座敞開的柴門,柴門臨河,因此,街道也止于此處,形成一個截斷的空間。但是,前方開闊處形成交叉道路,右側是停舟上岸的渡口,左側面向開放的空間,可繞過房舍,與中景的道路相連,似乎還有若干屋舍延伸到畫外。這樣來看,前景處的建筑,更像一個村落的開端部分(從最前方旅隊的行進方向來看,似乎也是走向畫外,而沒有落腳畫內茶館酒肆的意圖)。
畫面中景的棧道和木橋,既是前景的延伸,也是遠景的鋪墊。棧道與橋梁,一方面是人工構造的景觀,勾連鄰近的村落和城市;另一方面,它往往又是山水畫自然景觀的一部分,置身山水樹石中間,屬于人化的自然,是形象連接、隔斷、轉折的重要語匯:棧橋自身的形體和富于節奏的留白,以及往來于其間的三個人物,不僅與皴染密致的山體形成對比,也是與前景物象取得呼應的手段。在畫面中段,木橋和棧道再次隱退,被兩座凸起的小山隔斷,由此,中景的建筑,也被延伸到畫外。
遠景處,兩院宏偉的建筑掩映在主峰和附峰之間,因坐落深山,很可能是一處寺觀群落。畫面細致勾勒了這些寺觀的廊檐、瓦頂,和角脊上的幾個神獸,在最上方的軒廊上,刻畫了一個極目遠眺的人,與這些形象緊密相連的,是中景云霧上方再次出現的山路,和分布其上的兩個人物,其中一位杖策負笈,似乎是一位僧侶。不難發現,越到中、遠景,人物越少,建筑形象也愈加融合在自然山川之中,而遠景上的建筑,遠離塵世,不染煙火,正如王維《過香積寺》所言的“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一樣,成為人們遠游、觀覽、覲拜、遙想的去處,是精神遠游的一個象征。這個母題,在宋代十分受人關注,據傳,宋徽宗翰林圖畫院的畫學考試中,就有“深山藏古寺”的命題。
二、建筑、敘事與觀看
當我們遠觀全圖時,前景的建筑融合在樹叢、岸石之間,倚岸分布,疏密錯落,人物和動物又幾可忽視;同樣,中景上的棧橋,也依山勢布置,是山水形象的一個細節,人物純屬點綴;遠景處的宮闕,外輪廓與山體渾然為一,細小的人物同樣難以分辨。無論建筑形象多么精細入微,觀看者統觀全局時,似乎都是置身畫外,一方面把建筑形象作為山水的組成部分,感知它的起承轉合,體驗其自然分布的妙趣;另一方面,又能最大限度依據建筑物線索,感知延伸到畫外的村落、棧道,從而體察更為宏闊的圖景。在這個意義上,全圖是促成觀者精神遠游的中介,而畫面上的建筑,則是強化這一“可游”的“路標”:它勾勒出山水的獨特質感,標出觀者與山水形象的距離,提示觀看的方向、落點和路徑,點醒形象及其意義的關聯,拓展畫內與畫外的空間,增強山水樹石的人文內涵。
進而,當我們被建筑形象所吸引,走近幾步來觀察,這些建筑形象,連同人物活動,便轉換為風俗畫的場景,而與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郊區風光的描繪手法十分接近。但它又不是風俗畫,含有風俗畫因素、將景與人合一的細節,只占全圖很小的篇幅。關仝巧妙取舍,以點帶面,建筑和人物形象,不僅使得山水形象有所依托,更增強了畫面的情節感和敘事性,從而變得“可行”、“可望”;同時,建筑、人形之細微,與山體的宏偉彼此映襯,更顯出全景山水的波瀾壯闊。
最后,當我們近距離觀看時,精神遠游的方式立即被日常棲居的現實感所替代。我們會努力體察每個人物的身份、活動和去向,理解他們在建筑、山水中的意義。此時,觀者恍如進入畫家勾勒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依次與前景處年齡、身份、行止不一的人物,及神態各異的動物相見,被中景上俯身疾走的人、悠閑調皮的毛驢所感染,進而繞過云霧,跟隨上山的僧侶和游客,到達寺觀,并與亭廊下的人一起俯瞰山下。在此過程中,三種建筑形象統攝了人物日常生活中勞動、休息、攀談、旅行、玩耍等種種瞬間,通過移情,達到“可居”的境地。
事實上,也正是在五代時期,力求通過人文景觀的表現,將自然山川表現得與人親近,而達到情景統一的品格,是畫家的一個重要課題,其中涉及山水、建筑和人物的透視、比例、造型、筆墨、構思等具體問題,也包含諸如神韻等抽象命題。關仝的老師荊浩,就在繼承晉唐繪畫理論的基礎上,做過一系列關鍵的論述,他在《畫山水賦》中說:“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皴,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1]明確指出透視、比例問題,進而又在《筆法記》中指出與之相對的兩種病誤:“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園高于山,橋不登于岸,不可度形之類是也,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具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拙格,不可刪修。”[1]荊浩還結合山水創作,在謝赫“六法論”的基礎上提出繪畫的新法則:“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形,備遺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深淺,文采自然,似非因筆。”[1]
關仝師法荊浩,在他的作品中,三組建筑按照透視和比例法則,依次推遠,并達到與自然山川合乎情理的高度契合。然而,當我們流連于圖中細小的人物細節時,會發現近30個人物,并非按照透視法則,將形體依次減縮,尤其是畫面遠景亭廊下人物的大小,幾乎與前景、中景處一樣。當然,以其形體之小,并不影響全圖的比例和透視。相反,這些精微的點景人物,豐富了畫面的敘事性,是吸引觀者調整審視距離和閱讀方法,甚至減慢觀看速度,而深入體悟的線索;同時,作為與自然山川同在的因素,他們或身在此山,或觀覽此山,行游于山河棧道、寺宇大殿,是體現畫中山水“可居”、“可游”的關鍵。
到宋代以后,山水畫家對這些命題的理解更為深入,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說:“世之篤論,為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居可游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1]本著這個理念,除界畫以外,宋元山水中的建筑和點景人物日漸稀少,其旨趣,也向意象性的“渴慕林泉”發展,山水樹木變成更為獨立的藝術形象和繪畫語言。然而,在此之前,在山水畫中探索豐富多樣的建筑形象和點景人物,確立后世畫家可資借鑒的圖式,關仝等五代畫家,便是最重要的一環。
參考文獻:
[1] 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作者簡介:
朱杰,張掖實驗中學,副教授,主要從事美術創作和美術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