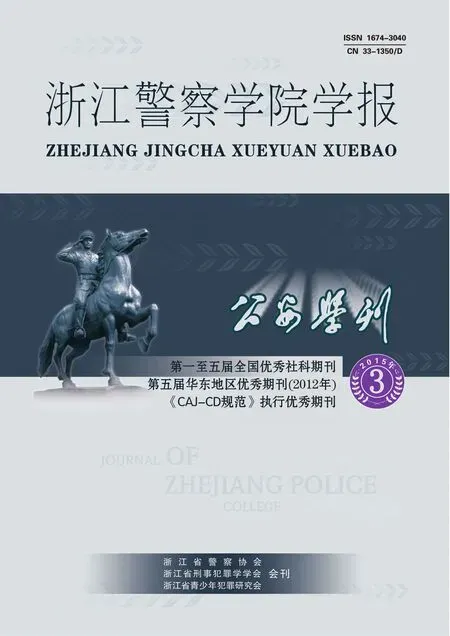近年來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研究綜述
□秦 帥,陳 剛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一、電信詐騙概述
(一)電信詐騙概念的界定。關于電信詐騙的概念,尚無統一的定論,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電信詐騙的概念做出過界定,如有的學者認為,電信詐騙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手機短信、固定電話、網絡等傳播介質和載體,以虛假信息為誘餌進行詐騙的犯罪活動;[1]有的學者認為,電信詐騙是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利用電信通信網絡媒介,致使受害人向非法賬戶匯款或存款,騙取數額較大財物或多次騙取財物的行為;[2]有的學者認為,電信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手段,借助電信網絡系統,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詐騙的行為。[3]綜合以上對電信詐騙概念的界定,筆者比較贊同最后一種表述,一是因為對電信詐騙的概念界定應當是概括性的,不應該對電信詐騙的具體作案手段、作案工具等內容作過多解釋,二是就目前司法實踐來看,電信詐騙仍作為詐騙犯罪的一種類型,對電信詐騙概念的界定,應該遵循延續對詐騙罪界定的基本思路。
(二)電信詐騙的緣起。電信詐騙起源于20世紀末的我國臺灣地區,最初是臺灣當地的詐騙分子采用刮刮樂、六合彩等形式實施詐騙,之后借助電信網絡實施詐騙,進而演化為一種新型的犯罪類型。2003年前后,迫于臺灣地區的嚴打態勢,這種“臺灣式詐騙”通過福建省傳入大陸,并蔓延到其他地區。2004年前后,一些學者根據此類詐騙中運用手機短信實施詐騙的特點,一度稱之為“手機短信詐騙”。2007年,福建政法機關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根據需要,將此類案件定性為虛假信息詐騙,并規定了此類案件的三個特征:一是借助電話、互聯網等通訊工具,向不特定的人群發送虛假信息;二是詐騙分子和受害人沒有直接的接觸;三是詐騙數額較大。[4]2009年,公安部為了便于各方交流,增進各方在辦理電信詐騙案件中的協作,將此類案件定性為電信詐騙案件。從此,電信詐騙一詞成為大陸司法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中的統一稱謂。
(三)電信詐騙的發案現狀。有關電信詐騙案件的數據紀錄連年刷新。據報道,2011年,全國共發電信詐騙案10 萬起,群眾損失40 多億元;2012年,全國共發電信詐騙案17 萬起,群眾損失80 多億元,比上一年分別增加70%、100%;2013年,全國共發電信詐騙案30 萬起,群眾損失100 多億元,比上一年分別增加了77%、25%。[5]根據公安部最新的統計,2014年全國共發電信詐騙案40 萬起,群眾損失107 億元,比上一年分別增加了33%、7%。[6](見圖1)

圖1 2011-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案件發案與損失情況
二、近年來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研究概況
(一)關于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的文獻數量逐年遞增。電信詐騙自2003年前后由臺灣傳入大陸,盡管受到內地公安機關和國際警務合作各方的嚴厲打擊,但電信詐騙技術不斷升級,詐騙手段不斷翻新,迫使各地公安機關和廣大學者針對電信詐騙的高發態勢,不斷提出對策,屢出研究成果。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為關鍵詞檢索,2009年檢測到的文獻數量共為80 篇,2010-2014年檢索到的文獻數量分別為159 篇、177 篇、184 篇、247 篇、392 篇。短短幾年的時間,學者們對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研究的文獻數量成倍增長,從側面反應了電信詐騙犯罪的嚴峻形勢。(見圖2)

圖2 2009-2014年中國知網關于“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的文獻數量
(二)公安機關對電信詐騙的打擊策略不斷作出調整。在電信詐騙犯罪十多年的偵查研究歷程中,學者們的研究內容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2003-2007年,電信詐騙犯罪在大陸處于蔓延發展階段,電信詐騙的概念尚未形成,廣大學者的研究內容聚焦于手機短信詐騙、虛假信息詐騙等具體詐騙方法的治理對策上。如2004年有學者提出要將打擊的策略放在做好調查取證工作、合理界定管轄等方面;[7]2008-2010年,大陸各地公安機關逐漸認識到電信詐騙帶來的巨大危害,逐漸加強了對電信詐騙案件的偵查協作和集中整治,尤其是2009年以來,在公安部的牽頭下,開展了多次“打擊電信詐騙專項行動”,突破了一大批大要案件;[8]2011年以來,開展深度警銀合作、斬斷資金鏈與通訊信息鏈“雙鏈”①、嚴打技術支撐團伙②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打擊策略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三)一些打防對策成為學者們的普遍共識。詐騙分子以通達的互聯網、電信網絡、金融系統網絡為掩體,肆無忌憚地實施詐騙活動,這種無接觸式的犯罪類型在大大降低犯罪成本的同時,也給公安機關的打擊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廣泛傳播詐騙信息致使受害者分布范圍極廣,一起案件往往需要許多地方的公安機關參與,偵查協作難度大;電信詐騙中的證據涉及很多電子證據的內容,具有很大的虛擬性,易破壞易篡改,給調查取證帶來難度;贓款到手后,經過網上銀行拆分處理,詐騙分子會迅速在世界各地將錢款提現,爾后,贓款經過地下錢莊、洗錢團伙的“合法化”處理后返回到詐騙集團內部,追贓難度極大。
針對以上困難,學者們從轉變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破案機制、建立警務協作機制、加強境內外聯合打擊電信詐騙案件的力度、加大宣傳力度等不同的方面提出打防對策,其中,開展部門協作、地域協作、海峽兩岸合作和國際警務合作成為最受關注的問題。如長期關注電信詐騙犯罪的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集團副總裁陳偉才認為,電信詐騙案件的迅猛發展,和電信運營商、銀行部門的監管不力有很大關系,一些電信運營商和銀行部門為了追求利益,甚至充當詐騙分子的支持者和“保護傘”,嚴重影響了對電信詐騙案件的治理,為此,運營商必須擔責。[9]四川警察學院的劉黎明教授認為,在電信詐騙的偵查過程中,需要核實與案件有關的IP 地址信息、銀行卡歸屬地信息、嫌疑人身份信息、作案手機號碼所屬基站信息等證據信息,但案件的偵查工作是有地域界限的,一個地方的警力不足以完成如此眾多的異地偵查任務,這就需要公安機關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以大局為重,深入開展異地偵查協作,實現異地用警常態化,形成打擊電信詐騙案件的合力。[10]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楊郁娟副教授認為,電信詐騙具有的高科技性、隱蔽性、集團化等特點,對傳統的警務合作機制、調查取證方式提出了極大的挑戰,特別是在近年來電信詐騙的跨國(境)犯罪趨勢逐漸突出的情況下,在電信詐騙案件偵查中廣泛開展國際警務合作已經成為提高偵查效率必須解決的問題。[11]
三、電信詐騙案件偵查中的部門協作問題研究
(一)源頭治理,強化“三張網”的自律作用。盡管公安機關針對電信詐騙的專項打擊行動已經開展了數次,電信詐騙案件的高發勢頭卻絲毫沒有減弱的趨勢。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堅定地認為,“追逐利益的運營商難辭其咎”。[12]電信詐騙在新形勢下逐漸呈現出智能化、虛擬化、國際化、專業化的特點,任意改號軟件、非法顯號軟件、短信群發器等高科技被廣泛應用到電信詐騙中,詐騙分子通過虛擬網絡誘導受害人存款匯款,獲取非法利益。同時,詐騙分子為了逃避打擊,通過國外服務器接入我國電信運營商的網絡,肆無忌憚地實施詐騙。在詐騙的整個過程中,詐騙分子需要依賴電信運營商提供的通信網絡,需要依賴銀行運營的服務網絡,需要依賴工信部門管理的互聯網絡,這“三張網”③已成為電信詐騙分子實施詐騙行為的載體,而相關的運營商并沒有出臺強有力的措施積極參與電信詐騙案件的防范與治理,這既體現了經濟轉型期我國社會管理部門存在的缺陷,又體現了現有的法律制度對此類行為懲處力度的有限性。
(二)明確分工,共建部門協作長效機制。電信詐騙案件不同于其他刑事案件,從監管的角度來講,此類案件往往涉及通信管理部門、電信運營商、金融監管部門、銀行等多部門的協作問題,通信管理部門需要及時檢查電信運營商的網絡運行與接入情況,電信運營商要保證所提供的通訊網絡安全可靠,金融監管部門要嚴格監督銀行賬號實名制的落實情況,金融機構要建立起科學的資金流動監管機制等。上述措施如果采取得當,落實到位,定能從源頭上減少電信詐騙案件的發生。
當前,公安機關在打擊和防范電信詐騙犯罪的限制在于,多數地方并未形成電信詐騙犯罪整治的長效協作機制,僅僅是在專項行動中或者在某個單一案件中,偵查機關才與其他部門開展協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網絡安全保衛學院馬丁教授認為,現在的聯合辦案,大多數是在面對單一任務或案件時的協同調查,事實上,公安機關與其他部門應該盡快形成完整的包含監管、預防和查辦環節的長效聯動機制。[13]
四、電信詐騙案件偵查中的地域協作問題研究
(一)開展地域協作勢在必行。電信詐騙案件具有虛擬傳播、廣泛撒網、全面詐騙的特點,這種“一對多”的詐騙信息傳播方式,極大增加了電信詐騙案件受害者的分布范圍,可以說,有電信網絡的區域都難以逃避電信詐騙信息的困擾。因此,一起電信詐騙案件受害者遍布全國多個省份的情況屢見不鮮,而刑事案件證據的完整性決定了公安機關在辦理電信詐騙案件時,要盡可能多地收集某一起或一系列案件的完整證據信息,包括涉案網絡服務器信息、嫌疑人作案窩點勘查信息、涉案銀行卡信息、涉案手機基站信息等,這些信息往往遍布在不同的省份和地區,受地域的限制,偵查人員不了解其他地區的案件情況,從而導致了嫌疑人作案活動地區的無限性和偵查人員案件管轄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北京警察學院的李蕤教授認為,“實現跨區域合作的飛躍發展,偵查機關不用隨著資金流全國各地跑,可以節約警力、精力和資金,突破傳統辦案調查取證時效性的制約”。[14]
(二)建立完善的地域協作機制。對于電信詐騙案件的偵查協作問題,四川警察學院的劉黎明教授認為,更好地完善電信詐騙案件異地偵查協作機制、拓展偵查管轄的觸角、遏制電信詐騙犯罪的高發勢頭,已成為當前電信詐騙案件偵查工作亟待研究的課題。目前存在的偵查人員協作意識不強、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警力資源缺乏等問題,影響了偵查協作的開展,成為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的絆腳石。四川警察學院的諶艷青認為,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的地域協作是偵查工作的重要環節,要加強各地區電信詐騙案件的串并案工作,落實好不同地區的電信詐騙案件信息通報與交流制度,同時協作雙方還要在調查取證、抓捕嫌疑人、起獲贓款贓物和作案工具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唯有這樣,才能克服作案活動范圍無限與偵查活動范圍有限的矛盾,遏制電信詐騙的高發態勢。[15]電信詐騙案件偵查協作應該是多層次、立體化的協作,在協作的基礎方面,各方應該具有積極的協作意識,建立完善的電信詐騙案件偵查協作團隊;在協作的框架方面,應該依托信息化平臺;在情報共享、調查取證等方面,應該明確各方的分工和責任;在協作的制度方面,應該拓展協作的內容和形式,使電信詐騙案件偵查的協作形成常態。[16]
五、電信詐騙案件偵查中的海峽兩岸合作和國際警務合作問題研究
(一)關于海峽兩岸打擊電信詐騙警務合作的論述。電信詐騙最初由臺灣地區傳入大陸,盡管兩岸攜手打擊電信詐騙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就目前的形勢來看,電信詐騙案件中,臺灣人涉案的情況最為突出,然而臺灣與大陸在刑事法律與司法制度上的差異,給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跨海峽兩岸的電信詐騙案件仍處于居高不下的狀態。對此,福建省公安廳的蔡小林等人認為,《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以下簡稱“《協議》”)已經實施,在公安部的領導下,在海峽兩岸雙方的努力下,兩岸攜手打擊電信詐騙案件已經進入具體實施階段,但是《協議》的實施細則和有關具體操作的內容尚未確定,面對日益復雜的電信詐騙形勢,海峽兩岸雙方應該在《協議》和各項共識的基礎上建立起更加密切、完善、常態化的協作關系,完善海峽兩岸攜手打擊電信詐騙案件的途徑,提高兩岸打擊電信詐騙案件的能力。[17]
(二)關于電信詐騙跨境和國際警務合作必要性和影響因素的論述。近年來,迫于國內打擊電信詐騙的強大壓力,電信詐騙的觸角逐漸向境外延伸,跨國電信詐騙越來越成為近年來電信詐騙案件的趨勢,跨國電信詐騙使本身就存在隱蔽性、智能性、專業性等特點的電信詐騙案件變得更加難以打擊,許多案件的服務器在國外,詐騙團伙在國外,取現團伙在國外,僅僅通過電信網絡、銀行網絡等高科技載體,就實現了坐收境內漁利,給公安機關的偵查與取證工作帶來重重困難,《經濟參考報》報道表明,“電信詐騙猖獗催生跨國產業鏈”,“擒賊難擒王,近10年境外頭目幾乎無一人落網”。[18]
毋庸置疑,打擊跨國電信詐騙,需要完善的警務合作制度作保障。雖然當前中國政府與東南亞各國就打擊電信詐騙的合作事宜進行過多次磋商,在中國警方和其他國家警方的積極參與下,破獲了一大批跨國電信詐騙案件,但是,電信詐騙案件開展警務合作難的現實依然存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楊郁娟教授認為,電信詐騙案件偵查中的國際警務合作往往會受到外交關系、法律制度和偵查能力等因素的影響。[19]西南政法大學的陳在上認為,司法協助在不同法域間的開展過程必然難以自然順暢,在國際警務合作中消除司法隔膜既需要各國立法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司法協助主體的積極溝通配合。[20]
(三)關于電信詐騙國際警務合作內容和方式的論述。電信詐騙案件的國際警務合作涉及到案件偵查工作的方方面面,案件線索的追蹤、詐騙窩點的查處、證據的獲取、嫌疑人的遣返、贓款的追回等各個環節均需要國際警務合作各方的參與。在具體的合作內容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楊郁娟教授認為,國際警務合作需要在情報信息的傳遞與共享、協助調查取證、涉案贓款的追繳等方面開展合作,而合作的方式包括個案偵查中的合作,也包括在各次打擊電信詐騙案件專項行動中的合作。中國人民大學的李超峰博士認為,防控跨國電信詐騙,需要充分發揮國際刑警組織的作用,在跨國調查取證、引渡與跨國抓捕、跨國追贓等環節加強溝通合作。[21]
六、電信詐騙案件取證問題研究
(一)電信詐騙案件主要證據類型。電信詐騙案件的主要證據類型包括在詐騙窩點以及有關地方查獲的記賬本、詐騙劇本、存儲案件材料的存儲設備、賬戶交易明細、員工名單等物證和書證證據;包括作案計算機與服務器中存儲的各類證明案件事實的電子數據證據;包括嫌疑人取款時的監控視頻資料信息,受害人收集記錄的嫌疑人詐騙通話錄音;包括嫌疑人供述和受害人陳述的言詞證據。北京市公安局的王小洪認為,“電信詐騙從犯罪預備到實施既遂,其間可分為預謀培訓、語音通話、提取贓款環節,每個環節的詐騙活動內容均不相同,每個環節所涉及證據的內容和作用也各不相同”。[22]
(二)注重對電信詐騙各環節證據的全面獲取。為了使詐騙過程順利進行,詐騙分子在實施詐騙前往往都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工作,這些環節一般包括成員的組織和培訓、作案工具的準備與服務器的搭建、雙方語音通話、受害人交款、詐騙分子提現以及分贓等六大主要環節,在每一個環節中都會留有實施詐騙的各類證據,[23]這就要求偵查人員在案件偵查中能夠循線追蹤,盡可能收集關于詐騙事實的證據材料。從案件偵查的階段性看,跨境電信詐騙在不同環節有不同特點,其取證的重點、難點及基本的策略方法也不盡相同。西南政法大學的倪春樂認為,“取證要以被害人對案件的描述為起點,注重對犯罪團伙的網絡數據進行有效監控,同時還要在查清犯罪窩點的基礎上多方配合實施窩點的現場取證”。[24]
(三)做細電信詐騙話務窩點的現場勘查工作。電信詐騙案件具有虛擬性、無接觸性的特點,許多情況下沒有受害人對嫌疑人的具體描述,并無證人證言,因此,查封話務窩點盡管對整個偵查過程而言只是收尾階段,但它在嫌疑人的責任認定、詐騙團伙的詐騙事實認定上都起著舉足重輕的作用,話務窩點查封得細致與否,影響到整個案件偵查取證的效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楊郁娟教授認為,對現場銀行卡、工作手冊、賬本等物證進行搜集、固定,并與犯罪嫌疑人工作內容一一對應,將電子交換數據、計算機日志、計算機文件等電子證據與案件其他證據進行比對核實,對于明確嫌疑人在犯罪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確定案件事實至關重要。[25]
綜上所述,電信詐騙案件在擴散蔓延中不斷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和作案手法,眾多專家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就電信詐騙案件的偵查理念、偵破思路、工作機制等方面建言獻策,公安機關應該充分吸收其中的研究成果,積極探索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新機制,切實提升偵查破案和執法辦案能力,維護人民群眾利益。
注釋:
①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孫延慶、徐為霞在河北省法學會2011年度法學研究課題《“雙鏈”偵查──打擊電信詐騙犯罪的模式》(批準號:2011DF023)中對電信詐騙的“雙鏈”偵查模式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②技術支撐團伙是指,在電信詐騙整個犯罪過程中,起到技術輔助作用,但往往不直接參與實施電信詐騙的團伙,盡管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技術支撐團伙的行為有時很難定性為電信詐騙,但此類團伙在電信詐騙中提供的技術與服務促進了電信詐騙的實現。
③筆者根據前述內容,將電信通訊網絡、金融服務網絡、互聯網歸納為電信詐騙中不可缺少的“三張網”。這“三張網”是詐騙分子實施詐騙的掩體,運營商疏于監管的現狀更是在無形中助長了電信詐騙犯罪。
[1][11][19]楊郁娟.論電信詐騙犯罪偵查中的國際警務合作[J].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1):6-9.
[2]楊宗.電信詐騙犯罪偵防對策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3:3.
[3][14]李蕤.比較視野下的電信詐騙犯罪防范與偵查合作[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2(5):119-123.
[4]吳照美,許昆.兩岸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演變規律與打擊機制的完善[J].青海社會科學,2014(4):110-116.
[5]任鵬飛等.電信詐騙爆炸性增長[N].經濟參考報,2014-10-27(5).
[6][9]2014年中國“電信詐騙”107億,代表建議“運營商應擔責”[EB/OL].[2015-04-01].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14/13553181_0.shtml.
[7]孫立智.網絡犯罪及其偵查對策[D].成都:四川大學,2004:9.
[8]公安部開展跨境聯合打擊電信詐騙犯罪行動取得成效[EB/OL].[2015-04-1].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8/id/1054679.shtml.
[10][16]劉黎明,劉旭洋.論電信詐騙案中的異地偵查協作[J].凈月學刊,2013(5):26-31.
[12][13]周婷玉等.打不倒的騙子還是割不斷的利益,電信詐騙井噴,運營商難辭其咎[N].新華每日電訊,2014-1-15(4).
[15]諶艷青.偵查通訊詐騙犯罪案件協作機制初探[J].知識經濟,2014(17):38-40.
[17]蔡小林,計蘇光,葉立暾.閩臺警方合作打擊防范電信詐騙犯罪問題研究[J].公安研究,2014(1):31-36.
[18]任鵬飛等.電信詐騙猖獗催生跨國產業鏈[N].經濟參考報,2014-10-28(8).
[20]陳在上.打擊跨境犯罪警務合作機制之構建[J].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2014(14):54-58.
[21]李超峰.跨國電信詐騙犯罪懲治與防范[J].社會科學家,2014(3):94-98.
[22][23]王小洪,陳鴻.淺論跨境電信詐騙案件證據體系的構建[J].公安研究,2012(12):37-44.
[24]倪春樂.跨境電信詐騙案件偵查取證問題研究[J].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4(4):53-68.
[25]楊郁娟.論電信詐騙犯罪偵查中的現場取證[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4(2):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