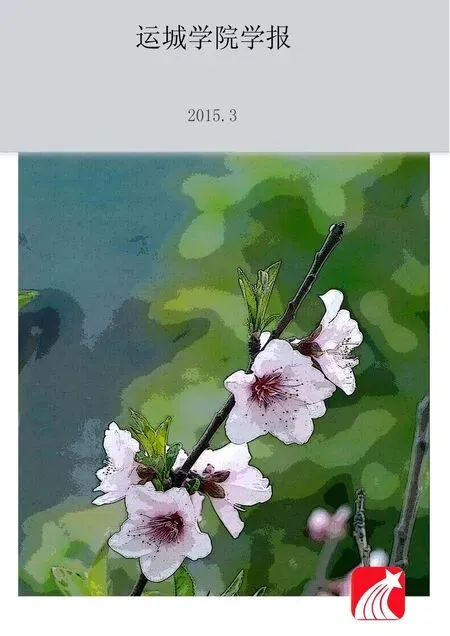語塊強化對二語口語流利性時間指標參數的影響
聶艷敏,張文俊
(運城學院 外語系,山西 運城 044000)
語塊強化對二語口語流利性時間指標參數的影響
聶艷敏,張文俊
(運城學院 外語系,山西 運城 044000)
時間指標是衡量二語口語流利性最直觀外顯的標準,而語塊強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流利性時間指標產生積極影響。接受語塊強化的實驗班受試語料樣本中語塊使用的數量、頻度和長度,以及口語流利性時間參數都有相對明顯的改善,說話者可以通過快速檢索提取以整體形式儲存的范例,提高話語輸出的流利程度。
語塊強化;口語流利性;時間指標
一、引言
隨著英語專業教學改革的深入,語言的運用能力成為判斷教學成效的標準。能將習得的二語成功輸出用以交流,是專業英語教學的目標所在。現階段,相對于書面語的輸出,學生的口語輸出能力略顯薄弱,口語流利性欠缺,這也成為中外學者近幾年來的關注點。陳平文通過對歷年來有關口語流利性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發現研究方向大致可表現為四種趨勢:考察口語產生中的實踐性變量;在時間性變量的基礎上考察上下文特征;側重言語產出的語音特征;關注考察語塊在口語流利性中的作用[1]40。由此可見,語塊論已進入眾多學者視線,語塊習得與二語口語流利性之間的關系是值得探究和證實的研究焦點之一。
二、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基礎
1. 口語流利性及時間指標
中外學者對于口語流利性的定義都曾做過嘗試。Fillmore[2]認為口語流利性表現為4種能力:一是“以話語填充時間的能力”;二是“用連貫的、合理的、語意密集的句子說話的能力”;三是“在不同場合駕馭恰當話題的能力”;四是“在語言使用中…具有創造和想象的能力”。Schmidt[3]將流利性定義為“自動化的程序性功能(automatic procedural skill), 是對語言的處理能力”。Brumfit[4](1984:42) 認為,流利性是“對所習得的語言系統的最大限度的有效運作(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language system so far acquired by the student)”。國內學者張文忠將Fillmore對流利性的定義歸納為“流暢性”、“正確性”、“靈活性”和“創造性”[5]206,并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闡釋:口語流利性是使用一種可接受的第二語言變體、流暢連貫地表達思想的能力,其流利性、連貫性和語言可接受性應為言語聽辨者所能感受。如果缺乏流暢連續性、連貫性和語言可受性中的任何一種,則語言表達的流利性就會受到影響[5]208。陳平文也在《基于國內外口語流利性理論的英語教學研究》一文中提到,口語流利性是指在語言的運用過程中言語所表現出來的流暢、自然、平滑、快速、連貫、具有可接受性的特征[1]41。
語言學家認為,口語流利性程度是可以測定的。張文忠、吳旭東歸納出12項流利性指標[6]343,其中包括5項時間性指標、1項內容指標、3項語言指標和3項表達性指標。在這四類指標中,時間指標是最直觀表現流利程度的參數,因為流利性首先是一種時間性現象。時間性指標由Goldman-Eisler (1968)等人在六十年代發展起來,后被Dechert and Raupach和Towell等一些研究者用于分析第二語言的產出。本研究中的時間指標采用Towell et al及張文忠研究中的五個參數,即語速(SR, speaking rate)、發聲時間比(PTR, phonation time/ratio)、發音速度(AR, articulation rate)、平均語流長度(MLR, mean length of runs)和平均停頓長(ALP,average length of pause)[6]343。
2. 語塊論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的關系
人的記憶中有大量預制語言單位,即預制語塊。語塊是指語言中出現頻率較高、形式和意義較固定、運用語境較確定、兼具詞匯和語法功能的語言單位,是由多個詞組成,可以以整體形式被記憶、加工、儲存和提取的成串的語言結構[1]44。語言的記憶、存儲、調出和使用是以那些固定和半固定的模式化了的板塊結構為最小語言單位的[7]。Lewis[8]將語塊分為4種類型:復合詞(complex words)和聚合詞(polywords);搭配(collocations 或word partnerships);慣用語(institutionalized utterances);句子框架和引語(sentence frames and heads)。預制語塊普遍存在于人腦的記憶中,隨著對記憶材料的熟悉程度而增強,數量也相應增加,從而使大腦可以存儲和記憶更多的信息[9]。
心理語言學和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s)理論都認為,語塊在二語的產生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對二語口語流利性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英語自然話語中80%由各類板塊結構組成[10],人們之所以能流暢使用語言交際,并不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抽象的語法規則,也不是單純的語法與詞匯的疊加,而是因為其記憶系統中存儲了大量的范例(exemplar)。Skehan[11]指出,二語學習者通過規則學習(rule-based learning)和范例學習(examplar-based learning)兩種途徑發展中介語,而范例學習就是預制語塊(prefabricated chunks)的積累。這些預制語塊按不同的語用功能范疇存儲在一起,使用者根據交際語境的需要,整體提取使用,從而達到正確性和流利性的統一[12]。大量習得語塊可提高英語口語的流利性,因為語塊是語言使用中形成的習慣性語言構塊,作為整體存儲在大腦中的語塊,在需要時可作為整體一并調出,無需過分依賴大腦的語言編碼能力,縮短了語言編碼或解碼的過程,使有限的資源可被用于高層次的語意構建,達到省事省力的目的[13]。所以,語言的流利程度不是取決于學習者大腦中儲存了多少具有生成性的語法規則,而是取決于學習者大腦中存儲了多少數量的語塊,是語塊使人們流利地表達自我。
三、實驗設計
1. 實驗目的
探究語塊教學對二語口語流利性時間參數的影響。并試圖證實如下假設:
(1)語塊教學模式下,學生口語流利性程度在時間指標上有明顯提高。
(2)通過語塊意識的加強及訓練,學生口語中語塊出現的頻率增加,復雜性增強。
2. 實驗對象
本實驗選擇運城學院2011級英語專業兩個自然班(控制班和實驗班)中各8名同學為受試者。為確保16名受試者閱讀速度及口語能力基本相當,實驗之前對控制班和實驗班共計62名同學的閱讀速度進行測試。選取高級英語第六冊教材中350字左右篇幅的言語樣本,排除部分學生提前看過的可能性,在不做準備的情況下要求所有學生大聲閱讀,并計時統計。相同閱讀材料和環境下,在實驗班和控制班各選擇閱讀任務完成時間接近的8名同學,共計16名學生作為實驗對象。
3. 實驗步驟
(1)口語流利性時間參數前測
16名受試者在學期初期進行英語口語流利性前測(pretest)。在測試之前,所有受試者被告知口語錄音只為收集語料用于研究,與學業考試測試無關,從而排除受試者焦慮心理因素對其二語表達的干擾。受試者在2分鐘的準備之后,要求進行3分鐘的自由陳述,表述內容關于畢業后就業與考研的選擇。該話題是所有大三學生面臨的實際問題,排除話題片面性因素。為確保錄音質量和實驗信度,要求受試者逐一單獨測試,并保證不向他人泄露測試內容。
(2)不同教學模式的實施
以高級英語課程為教學內容,在為期16周的教學實驗中,16位受試者所在的控制班和實驗班采取相同的教學環節、不同的教學模式。高級英語教學在處理課文時都分為三個環節:“讀前”文化背景的激活和補充→“讀中”文本分析和學習→“讀后”語言能力的鞏固和拓展。兩個班級教學模式區別于第二個環節,控制班使用傳統教學模式,注重信息傳遞和內容理解,不刻意灌輸語塊概念;實驗班則主要采取樹立語塊意識、講解語塊、分析句子意群并識記運用語塊等一系列環節來分析語言篇章結構。在整個實驗過程中,16名受試者沒有進行特殊對待,與各自所在的實驗班和控制班共同參與。
(3)口語流利性時間參數后測
學期末對16名受試者進行口語流利性后測(posttest)。與第一次錄音要求相同,受試者在2分鐘準備之后進行3分鐘的即興表述。兩次語料采集使用相同話題,以便更準確客觀分析數據。因為受試者并不知道第二次錄音還會采用相同話題,排除提前準備的可能性。
(4)語料收集、整理及計算
該研究語料整理分析工作量大,繁瑣復雜,需完成以下任務:
1)將16名實驗對象的2次錄音材料(32個)轉換為文字材料。
2)統計語料文本中語塊數量、使用頻度及平均長度
3)對32份文本材料進行整理,統計出各樣本的總字數與總音節數。
4)使用音頻軟件對32份錄音材料進行分析,整理出各文本中的停頓次數和停頓時間。
5)計算各語料樣本中的時間指標參數,即:語速(SR)、發聲時間比(PTR)、發音速度(AR)、平均語流長度(MLR)和平均停頓長(ALP)。
四、實驗結果及數據分析
1. 口語樣本中語塊使用情況分析
將控制班及實驗班各8名受試前、后測的語料樣本中的語塊使用數量、使用頻度及平均長度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到如下平均值:

表1 控制班與實驗班語料樣本中語塊使用情況
表1顯示,在控制班與實驗班受試者的前測語料樣本中,語塊使用的數量、頻度及平均長度均無明顯差異,后測在此基礎上都有所提高,但程度不同。
在語塊使用的數量上,控制班所有受試的語料中語塊使用個數的平均值為24.9, 16周的傳統教學模式后,平均數量上升為32.5個;以語塊輸入模式為主的實驗班的語塊數量由之前的25.1個提高至42.6個。其明顯程度高于控制班,說明對語塊的重視、識記及鞏固有利于語塊在口語表達中的運用。
語塊使用頻度是指語塊所占字數與文本總字數的比例。如表所示,控制班前測樣本中語塊比例25.83%提高到后測中的29.72%;而實驗班的比例上升幅度大于控制班,由25.79%上升至39.94%,也就是說平均有39.94%的言語是由語塊構成的,語塊的使用頻度明顯增加。
將樣本中所有語塊所占字數除以語塊總數,即可得到語塊的平均長度。控制班中語塊的平均長度為2.42個單詞,一個學期之后為2.45,實驗班則在相同的基數上上升為2.53,大于控制班。
2. 口語樣本中流利性時間指標參數分析
本次實驗采用的是Towell et al和張文忠歸納的5個流利性時間指標,及語速(SR)、發音速度(AR)、發聲時間比(PTR)、平均語流長(MLR)、平均平頓長(ALP)。其計算方法[14]如下:

表2 本研究采用的流利性時間指標及計算方法
通過以上方法可計算獲得控制班與實驗班語料樣本中各時間指標參數平均值,結果如表3:

表3 控制班與實驗班語料樣本中5項時間指標參數平均值
表3顯示,與前測各參數相比,控制班與實驗班的后測時間指標參數都有變化,表明流利性程度在之前的基礎上有所提高。
控制班第一次測試中,受試的語速(SR)為每分鐘108.47個音節,第二次平均語速為117.36,較之前有所提高;實驗班的語速提高程度更為明顯,由107.93個音節升至131.36,這表明說話者的信息內容的語言形式加工和語音實現加快了。發音速度(AR)指單位時間內(秒)發出的音節數量。控制班前測AR平均值為3.22音節/秒,后測為3.27/秒;實驗班增長相對明顯,由前測的平均值3.21音節/秒變為3.42。對比顯示,實驗班樣本發音速度變化較大。控制班與實驗班在前測中的發生時間比分別為61.35%和60.83%,后測中顯示為64.73%和71.49%,這表明,實驗班受試者用于講話的時間較多,言語計劃的效率明顯提高,“用話語填充時間的能力”增強。平均語流長度(MLR)表示兩次停頓之間所發出的音節數量,控制班的兩次測試語流長度平均值分別6.32和6.63個音節,實驗班則由6.34升至7.53. 這說明經過語塊認知及練習,實驗班學生語言處理能力提高程度更為顯著。同時,實驗班前測結果表明,受試在整個語料形成中的平均停頓時間為1.54秒,一個學期后停頓時間降至1.32秒,而控制班前測為1.55秒,與控制班基本無異,但后測中停頓時間明顯下降為0.97秒,與控制班相比,話語組織能力明顯增強。
通過數據分析,本研究可得出如下結論:1)控制班和實驗班在16個教學周之后,受試在語塊使用的數量、頻度及長度上都有提高,但以語塊輸入為主的實驗班提高程度更為顯著。2)相對于控制班中的五個流利性時間指標參數,實驗班樣本顯示的相關參數變化更明顯,說明流利性提高程度更大。由此可以推斷實驗班口語流利性時間指標提高幅度明顯高于控制班的原因,可能在于受試語塊意識的強化和鞏固練習增加了頭腦中預制語塊的數量,因而在口語交際時不必按固定語法規則生成話語,可通過快速檢索提取以整體形式儲存的范例,減少了編碼勞動,節約了編碼實踐,提高了話語輸出的流利程度。
五、結語
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是口語表達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二語教學追求的重要目標,是檢驗二語教學質量和學習者實際水平的重要指標,是二語學習成功與否的重要外顯標志[1]40。本次實驗證明,語塊教學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口語流利性,尤其是表現在5個時間指標參數上。同時也說明學生二語口語中語塊的出現頻度、長度及復雜性、流利性之間存在關聯。因此,語塊教學法可作為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一種新模式,教師應鼓勵學生不斷構建、豐富語塊知識,加強記憶與提取運用語塊的能力,克服母語對中介語的負遷移。但是,如何引導學生重視語塊學習、培養其自主學習的能力,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論證。
該實驗由于時間限制,沒能在更大的時間跨度上對受試者進行跟蹤調查以觀察語塊認知對英語口語能力的后續影響;同時,因為語料處理繁瑣和工作量大的原因,本研究只選擇了16名受試者的語料樣本作為參考,更多語料樣本的選擇可能能夠提供更詳實的數據。建議對更多二語學習者進行長期跟蹤調查,以獲取更大更有效的樣本分析。
[1] 陳平文.基于國內外口語流利性理論的英語教學研究[J].外語界,2008(3).
[2] Fillmore C. On fluency[A]. In Fillmore C, Kempler D & Wang W(eds.). Individual Differencesin Language Ability and Language Behavior[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93.
[3] Schmidt 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2(3).
[4] Brumfit.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oles of Fluency and Accuracy[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5] 張文忠.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的理論模式[J].現代外語,1999(2).
[6]張文忠,吳旭東.第二語言口語流利性發展定量研究[J].現代外語,2001(4).
[7] Becker,J. The Phrasal Lexicon[M]. Cambridge, Mass: Boltan Newman,1975.
[8] Lewis M. Implementing the Lexical Approach: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M]. Hove, England: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7.
[9] Nattinger,J.R. &Jeanette S DeCarrico. Lexical Phrase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0] Altenberg,B.&Granger,S. The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Patterning of “Makie”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student Wri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2).
[11] 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王立非,張大鳳.國外二語預制語塊習得研究的方法進展與啟示[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5).
[13]張文俊,秦建華.語塊認知和文化認知整合模式下閱讀能力的實證研究[J].外語教學,2013(4).
[14]原萍,郭粉絨.語塊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的相關研究[J].外語界,2010(1).
【責任編輯 馬 牛】
2015-03-16
山西省回國留學人員科研資助項目(2013-104)
聶艷敏(1984-),女,山西運城人,運城學院外語系助教,碩士,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G642.1
A
1008-8008(2015)03-006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