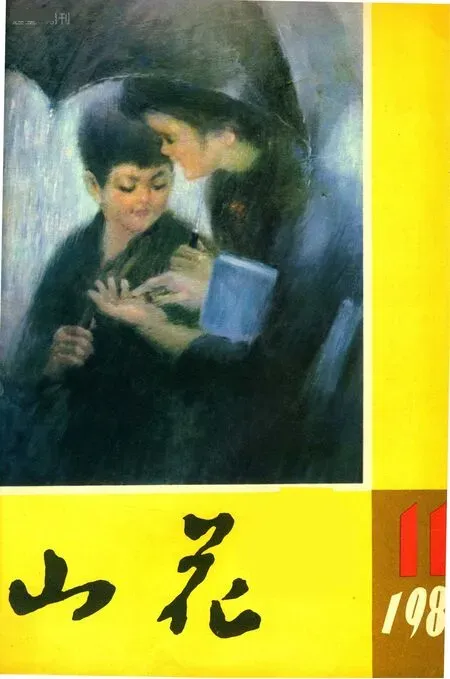桐花
何大草
李小山的爸爸給一位老爺爺專職開車。
每天早晨,他騎車到貢米巷25號的市委機關行政處,然后把伏爾加開出來,載了蕭秘書,進27號家屬大院的門,曲里拐彎,駛過鍋爐房、長滿牛筋草的大壩子、幾排核桃樹掩映的小平房,還有一片白果林,停在大院底端的一座獨立小院前。黑門終年緊閉,門上還有一扇小門。八點差十分,小門打開,老爺爺走出來,佩了毛主席像章的藏青色中山裝,沒有帽徽的毛料黃軍帽,肚子大凸著,微微打著顫。他的夫人端著他的包,像端著一只黑漆的點心盒。他走到車門邊,回頭接過包,對夫人笑笑。老爺爺面善,不笑也像是在笑。笑了,躬下身,就鉆進車去了。
伏爾加出了家屬院,就輕快地跑起來。可能是去隔壁的辦公樓,也可能去下邊的一個局、一個廠。
伏爾加亮錚錚的,跑在灰撲撲的街道上,宛如一匹漂亮、優雅的馬。
李師傅愛惜車,總把它里外擦拭得一塵不染的。車門一開,老爺爺總能嗅到一股干凈、爽潔的氣息。他深吸口氣,仿佛這比早晨的空氣還要清新些。
但李師傅更愛惜、敬佩的,還是老爺爺。老爺爺除了平易近人,還關心蕭秘書的女兒蕭小紅,李師傅的兒子李小山,他記得兩個娃娃的生日,必送小禮物,兩塊巧克力,兩小袋大白兔……兩個娃娃同年、同月,今年十歲生日,各得到兩本《十萬個為什么》、連環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
李小山對孔老二沒興趣,卻很快把《十萬個為什么》讀完了,還開始讀第二遍。不懂的,他就請教常識課老師。這老師是返城知青,一個造反派頭頭的兒子,滿臉小疙瘩,李小山不懂的,他也不懂,還拿指頭戳著李小山的額頭說:“不要讀迂了!白專典型。”
明代的親王府,有條很寬的壕溝,民間俗稱御河,在主城區腹心繞個圈,向南流入濯錦江,再向南流淌一百三十里,到江口鎮匯入岷江去。李小山的家,就在御河邊:
后窗推開即見河水,開了前門,就是西御河沿街。說是街,更像細長一條巷子,兩排女貞樹,門口拔地而起一棵巍巍老泡桐,樹影罩了半條街。冬天,泡桐枯枝如鐵,進了三月,枝頭突然鮮花怒放,成串、成串,白中透紫,姹紫粉黛,粉嘟嘟、透亮,把人的眼睛都映得亮堂堂。
不過,陰天是多數。本城窩在盆地中央,自古安寧,聚人氣,聚財氣,也聚云、聚霧,陽光天少有。西御河沿街地勢低,墻根、樹根,爬滿了青苔,不下雨,屋里地上也是濕濕的,暗暗的。屋頂有一塊玻璃亮瓦,一柱光落下來,靜得像古代,日子在發霉。解放前,這兒是有名的棚戶區。
街坊鄰居中,李小山找不到同齡的玩伴:大的正在鄉下當知青,小的還穿開襠褲、吊著清鼻涕亂竄。下午三點半放學,他沒參加文工隊排節目,也沒參加批判組出墻報。蕭小紅拉他參加故事組,宣講批林批孔,他也沒有去。時間長得沒盡頭,人無聊,就會像一根蔫了的豆芽,等著風干,變成一把灰。然而,他不是。他把紅領巾摘下來,團了塞進褲兜,光腳下御河去撈東西,酒瓶子,罐頭盒,一串鑰匙……有回撈起一尊砸了頭的領袖石膏像,就像撈起一塊燒紅的鐵,趕緊扔得更遠些。
河水潺緩,若有陽光,也是粼粼好看的。然而,水很臟,兩岸的人家都把臟水潑進御河去。河水飄著腥氣,像根爛腸子。魚是少見的,倒是喂金魚的紅線蟲很多,隨手一揪就是一團,在手掌心蠕動著,男娃娃覺得好耍,女娃娃感覺惡心。
李小山養過幾條金魚,都被紅線蟲撐死了。
暴雨前,御河上幾千只灰燕低空盤旋,捕食蚊子。雨后的晚上,青蛙嗒嗒嗒嗒地叫,焦灼得揪心。李小山就拿了電筒沿岸抓青蛙,手電一亮,青蛙就閉了嘴,愣愣地,束手待斃。他讀了《十萬個為什么》,要實證條件反射,就用兩分錢的鉛筆刀,在青蛙的小腿上切個口子,然后指尖拈緊向上一撕!青蛙已經死了,整張皮撕下來,畢露出肉、筋、血,還在痛苦地抽搐。
他母親見了,不敢看,喃喃罵道,“作孽啊……”
父親直接就甩了他一耳光。
李小山、蕭小紅蒙老爺爺安排,在第一師范附屬小學念完五年級,接著念初一,俗稱戴帽子。要到初二才能正式進中學念初二、初三,然后是高一、高二。那時學制短,中小學共十年。
夏至過后的一天,李小山的父親回家很晚,飯菜都涼了。他頭上纏了繃帶,浸出一大塊血跡。母親見了,嚇得嗚嗚哭。李小山恨恨問,“爸,哪個敢打你?”父親道,“算個×。”
他下午載了老爺爺和蕭秘書去肉聯廠跟造反派對話,話不投機,一大群人舞著小紅旗和趕豬棒、殺豬刀沖進會議室,高叫“打倒!”“打倒!”局面大亂,造反派頭頭也控制不住了。李師傅替老爺爺擋了幾棒,蕭秘書得空死活把老爺爺拖進了汽車。
“痛不痛?”母親問了句廢話。
“不算痛……也很痛。殺豬匠嘛,又不是殺青蛙。”
李小山不知咋的,嘿嘿地,傻笑了兩聲。
星期天,老爺爺請了蕭、李兩家人去吃晚飯,是表達謝意的意思。李小山的母親在被服廠做工,心細,膽小,咋也不肯去,說去了是站、是坐、該說啥不說啥,弄不清楚,飯也吃不飽。只好父子倆去了。到了才發現,蕭秘書也只帶了蕭小紅。
這是李小山頭一回走進27號家屬大院。說是大院,其實是院里有院,兩扇鐵灰色大門后,一條彎曲小道把八九個小院串起來,宛如一根藤上結滿了小瓜。院里樹多,蟬鳴鋪天蓋地,森森然,而又生氣勃勃。他看見人家的窗戶都掛了簾子,木門外加了紗門,有的種了牽牛花,向日葵,還有的種了玉米,苞谷穗子已然黃了,偶有幾只雞踱過……看著都是好看的。
老爺爺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孫孫一大堆,家里卻安靜得出奇。來開院門的,還是蕭小紅,眨眨眼,一臉笑,似乎是這兒的常客。獨立的小小院落,也像大天井,鋪了磚,不見泥,寸草不生,只擺口大木桶,種了一棵綠黝黝的樹,李小山不認識。蕭小紅得意地說,“《十萬個為什么?》白看了吧?它屬于第十萬零一個問題。”
“你得行,那你說。”
“無花果。”
聽著像是外國名。李小山把這棵樹多看了會兒,樹葉是格外綠,綠澄澄發黑,但也沒看出別的啥名堂。
蕭秘書在書房陪老爺爺說話。李小山的父親下廚幫忙。環小院一圈,好幾間屋子,都是空空的,再沒別人了。李小山正納悶,聽見父親叫他。
“小山,快叫奶奶。”
他嗯了一聲,卻沒叫出口。
父親挽了袖子,圍了圍腰,有點謙卑地躬著身子。邊上站了個婦人,年齡跟李小山的母親差不多,也可能略大兩三歲,那“奶奶”二字在他嘴里打了幾個轉,終于還是吞了回去。
“咋沒禮貌呢?快叫奶奶啊。”父親急了。
“別嚇著孩子了,老李。”那婦人微微瞇了瞇眼,像微笑,然而并不是。嗓音厚實,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平靜,好聽,但嚴肅。季節雖已入夏,她深藍的襯衣外,還罩有一件灰色的毛背心,袖口、領口,扣子扣得嚴嚴實實。下身倒是裙子,但裙擺一直落到了腳背上,隱約看見一雙皮拖鞋,一雙黑色的尼龍襪。這就襯得她的一張臉,格外的白皙。
李小山有點怕她,不覺就退了一步。
她伸出手去。“來,小禮物。”是兩支英雄牌鋼筆。
蕭小紅接過來,立刻在手心上寫了幾個字。“謝謝奶奶。”她笑瞇瞇的,補充一句,“好好寫哦。”
李小山手碰到她的指尖,覺得好涼,一種夏天背陰處的涼。“謝了。”他咕噥。
“謝誰?”他父親厲聲問。
“奶奶……”很模糊的兩聲。李小山的奶奶去世多年了,他沒有見過她,只看到過一張模糊的照片,她膝上坐著還是幼兒的李小山父親。
“不謝。”奶奶說。“成績好嗎?”
李小山不吭聲。
“我全班第二。”蕭小紅說。
“哦……那第一呢?”
蕭小紅拿一根指頭指了指李小山。
“是嗎?”
“向毛主席保證。”
奶奶瞇眼看了看李小山。“很驕傲。”她說。
“驕傲啥!”他父親又急了。“這娃娃膽小,見了奶奶就嘴笨,不敢多話……何況,他成績是好點,可白專,動手能力差……”
“他不差啊,”蕭小紅替他辯護。“實驗課解剖青蛙,他好厲害,全是一張張整皮揭下來,貼了一門板。”
李小山父親氣得臉煞白。
奶奶目光如刀,盯著他。“是真的?”
李小山埋了頭,腳尖在地上默默畫弧線。
兩只菜花黃的蛾,繞著無花果樹慢悠悠地飛。
“是真的?”奶奶重復問。
“嗯。”
奶奶的眼瞼輕微哆嗦了兩下。小院中一下子冷寂了下來。無花果的樹葉在微風中嚓嚓響。良久,她說,“今天的鯉魚你來剖。”
李小山剖魚時,奶奶支派蕭小紅去書房給老爺爺斟茶,他父親去屋檐下洗菜,她自己則站在身邊一聲不響地看著。那是條一尺六七的灰色鯉魚,肉質飽滿,生命頑強,肚腹白得像抹了層白胭脂,正有力地呼吸著,尾巴拍在案板上,啪啪作響!
但李小山握住菜刀,十分鎮定。
他一手拈住魚尾,倒提起來,刀刃隨即貼了上去,刷、刷、刷……倒刮魚鱗。魚身憤怒搖擺,還發出嘰嘰叫聲,像個撒嬌的女孩。然而他運刀如風,均勻、有力,魚鱗跳了起來,扇面灑開,像一群透明的銀箔,紛紛揚揚,嗶嗶作響。刮完了這一面,他再刮另一面。兩面刮完了,他彎曲了食指,伸進魚嘴,把魚腮一一摳出。這時候,魚似乎斷氣了,但肚子卻在一點點脹大,宛如臨近爆炸的氣球,他等的就是這一刻:菜刀瞄準魚肚中央一條隱約的凹線,一刀橫切,魚肚吐出一聲嘆息:一汪黑血緩緩流滿菜板,仿佛永遠流不完……這時,他才略感異樣,側臉看了看,奶奶已經不見了。
蕭小紅后來問過李小山,“想不想曉得奶奶的事情?”
李小山說,“可以。”
“那你要保證不說給任何人聽。”
李小山說我保證。
“要向毛主席保證。”
李小山說,“不。毛主席管不了那么多事情,接見外賓時,顯得很老了。”
蕭小紅大怒。“你太反動了。”
李小山說,“那你去工宣隊告我嘛。”
“工宣隊算啥?我直接給毛主席寫信。”
李小山哼了一聲,懶得理她。
她還是把所曉得的事,都告訴了李小山。就像她平日有了一塊綠豆糕,一只蘋果,一只梨,總愿意跟他分享。她說,老爺爺的兒女,都是他跟前妻生的,離婚后,他們都隨母親搬出了27號家屬院。這位母親不是黃臉婆,不是受氣包,很不簡單的,她小時候纏小腳,就大哭大鬧過,不依不從。十六歲參加八路,在晉南打過游擊,能騎馬放槍,做隊長時,手下有三十多號大男人。后來她去延安學習,遇見了老爺爺,由一位大首長做媒,把窯洞布置成新房,就成了紅色的伴侶。出席婚禮的客人中,有一位后來做了元帥,將軍就更多了。全國解放后,老爺爺的官運并不亨通,因為,他遇見了現在這位奶奶。
奶奶是南京人,父親是銀行家,母親是姨太太,很多姨太太中的一個,父親叫她老四,后邊還有老五、老六。母親在姨太太中、她在一群兄弟姐妹中,不算受冷落,也遠不是受寵愛,有一點落寞。抗戰爆發,日本兵攻破南京城前夕,她正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念英文系。父親給了她一口藤箱,就隨學校流亡到了成都華西壩。
從此她再沒有見到過父母。
壩上當時有五所大學,她換學到了華西協和大學念醫科。大四時,她去川南的雅安實習,醫治過一位川軍中校,他中了一槍,子彈穿過左臉頰,留下一個突兀的咬痕,很有英雄氣。還沒有畢業,他就捧了玫瑰來華西壩求婚。順理成章,她就嫁了。婚后才曉得,他的槍傷是擦槍走火所致,跟血染沙場沒一點關系。何況,他是軍需官,從沒打過仗。好在他除了嗜酒、嗜賭、偶爾嫖妓,并無大的惡習劣跡。他染過梅毒,傳染給她,好歹打針吃藥,梅毒是斷了根,卻再不能生育了。臨近解放,川軍起義,她算是起義軍官的妻子,與新社會相安無事。丈夫從軍需官,改做了糧站的副站長。
有個秋天,副站長帶人下去視察莊稼收成。晚上喝了很多苞谷酒,他抱著一棵板栗樹嘔吐,先是吐光了酒飯,后來就吐五肝六臟,再后來是吐命:一頭栽在嘔吐物上,嗚呼了。
奶奶料理完后事,依舊提了那口藤箱,輾轉來到本城,在王府正街的一家小診所做了大夫。也是合該有事,老爺爺有天晚飯后散步,從貢米巷走到正街上,風吹來,被沙子迷了眼,揉幾揉,居然紅腫了,痛苦不堪。他摸索著,敲了街邊診所的窗戶。診所已經關門,但奶奶沒事,還在里邊讀閑書。
她一手輕輕撥開他的眼皮,一手拿蘸了清水的棉簽,小心翼翼掃出一粒沙子。他一下子舒服了好多。
“可能是煤渣,有棱角的,再揉,就傷到角膜了……以后再不敢了,啊?”
“……”她的手,聲音,都有種夏天的薄荷涼。
他付錢,她不收,沒用藥,也說不上治療。他就隨口問她讀什么書,她說了,他一臉茫然,就把書抹過來細看,全是英文。老爺爺和老婆都是馬背上打天下的英雄,刀槍在手上玩得輕如鴻毛,可拿一支筆,卻重如城門閂,吃力得很。
老爺爺回了家,心里再沒把這女大夫放下。過些日子,他把這小診所劃入了市委機關,成了行政處下屬的醫務室。很多人在背后議論紛紛,但他不理會,反正也沒聽見。下了班,他總要干咳著,去醫務室讓她摸摸脈,測量下血壓。順帶說說話。他來得再晚,她總在,好像就是在專門等他。有天,她等來的是老爺爺的老婆,第一針織廠的黨委書記兼廠長。
她扇了她一耳光。還把醫務室砸爛了一半。
老爺爺和老婆離了婚。
奶奶和老爺爺再婚后,提了一個要求,去四川醫學院,即從前的華西協和大學,完成醫科學業。老爺爺沒答應,他說除了這一點,啥要求都答應。然而,奶奶啥要求也沒有了。
她辭去了醫務室的工作,退入了老爺爺的家。
李小山初次見到她的那個夏天,她已經幽居在家二十年了。
1977年10月,高考恢復。李小山和蕭小紅16歲,剛在念高二,但學校推薦了他們參加高考,說是積累些經驗嘛,考不上無所謂。這倒是,高考中斷了十年,文革前的老三屆畢業生堆成了山,都拼老命要擠過窄門呢。錄取率低之又低。
結果出來,李小山居然高高地中了,收到四川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這學院是老牌,重點大學,很不差了。但中學校長大喜之余,建議李小山放棄,等高中畢業再考,必能拿下清華。李小山也覺得可行。但他父親劈頭一通罵:“人不要貪心。貪心沒好報。李家八代睜眼瞎,總算出了一個讀書人,知足吧。”母親也勸:“聽爸的話,貪心不好,知足好。”他挨了罵,也不辯解,認了,那就讀吧。
蕭小紅也收到了通知書,是南充師范學院,她兩把就撕了。
次年春天,七七級入校。李小山收拾好一包衣服,一包書,一床捆好的棉被,插了一卷草席。臨行前一晚,父親說,應該去給老爺爺、奶奶告個別。
父子倆是吃了早晚飯過去的。天色還亮,也很暖和,主客就坐在寸草不生的小院中喝了會兒茶。蕭小紅沒人叫她,也主動跑來湊熱鬧。她父親已經提拔為辦公廳副主任,蕭家一年前已搬入27號大院,是老爺爺親自給找的一套帶紅漆地板的平房,便于蕭副主任的工作。
老爺爺更胖了,頗有倦意,但心情舒暢,氣色好,嘴一直張著,樂樂呵呵的。他胖大的身體坐在藤椅上,把椅縫都擠滿了。
奶奶還是瘦瘦小小,穿了高領黑色羊毛衫,還罩了一件灰色的開衫,手大半縮在袖里,只露出幾個指尖。她的頭發幾乎全白了;臉也是蒼白的。
氣氛比較沉悶,幸好蕭小紅話多,就她一個人嘰里咕嚕,還不時站起來,繞著無花果樹踱一圈,說自己下回就考戲劇學院的戲文系,做劇作家,寫一出當代的《雷雨》。老爺爺笑道,“好,好。”李小山父親也贊嘆,“還是小紅有志氣。”
奶奶點點頭,看著李小山,問他:“你覺得呢?”李小山沒聽說過《雷雨》,就嘰咕了聲,“夸夸其談。”
蕭小紅不依了,跳過去揪住他的頭發,要他道歉。
奶奶的眼瞼輕微地跳了兩跳。
李小山說,“好,道歉。”
“你這個乏味的現實主義者。”蕭小紅噘噘嘴,饒了他。
奶奶送了他一個筆記本。是她親手裝訂的,牛皮紙封皮,內頁是一沓厚實而輕的白紙,不是純白,有點米湯色,亞光,略澀,手感極舒適,宛如一冊素樸、雅致的線裝書。
李小山說著謝謝,雙手接過來。他父親說,“請奶奶給小山題句話吧。”
奶奶又把筆記本拿回去,去書房用蘸水鋼筆豎著寫了兩排字:
春天是最好的季節。
十七歲是一生的春天。
沒有落名,也沒有日期。
蕭小紅伸頭望了一眼,咕噥道,“我們還沒有十七呢。”
奶奶盯了她一下,眼睛刀子般一閃。
蕭小紅立刻閉了嘴。
奶奶隨口問了句,“家門口的泡桐開花了吧,小山?”
李小山微微一驚。奶奶咋曉得自己家門口有棵老泡桐樹呢?他回答不出來。這些天忙著下戶口,轉糧食關系,一系列入學手續,而且莫名的,情緒有些郁郁,埋著頭進,埋著頭出,根本沒抬頭看一眼泡桐樹是不是開花了。他就老實說,“我……沒有注意到。”
奶奶瞇著眼,笑了。這是他頭一回看見奶奶是真的笑了。她微笑道,“是有一點呆。”
奶奶手訂的筆記本,李小山始終沒用上。不是不喜歡,也不是舍不得,是用不上。他用了許多灰色、黑色塑料皮的筆記本,大開,半寸厚,橫格,紙張光滑,經得起磨損、摔打,而且,還有一點關鍵的,很便宜。念完了本科,又保送讀研,畢業留校任教,給大一上尸體解剖課,同時就在本校在職讀博。平日除了上課,就泡在實驗室、圖書館,吃食堂,睡單身寢室。
圖書館外有一塊荷花池,他有天晚上出來,星空睛朗,聽到魚在蓮葉間竄動,蓮桿被撞得啪啪響。他忽然起了童心,脫了鞋襪,要下水撈魚。但,腳指頭才一伸到水里,就抽了口涼氣,咕噥聲好冷,算了,就縮了回來。
奶奶的筆記本壓在了箱底,起初可能是有點珍藏的意味,后來就近乎遺忘了。
他沒有再見到老爺爺和奶奶。
父母已經退休,從西御河沿街搬到了三洞橋一處市級機關的宿舍。還是老房子,然而是樓房的底層,小三居室,有廚房、廁所,陽臺外有塊小花園,可以種花,老倆口種了茄子、絲瓜,開出繁繁的紫花、黃花,看著是喜人的。他節假日回去陪父母住幾天,父親總念叨要他去看望老爺爺和奶奶,但他拖著,提不起興致。父親罵他沒良心,他不反駁,只覺得言過其實了。研究生畢業的次年春節,他是要去給老爺爺和奶奶拜年的,但臘月二十九被老同學拉去喝酒,大醉后躺了兩天,迷糊了三天,也就罷了。
蕭小紅第二次高考的成績,總分相當高。填報志愿前夕,她父親跟她長談了一夜。她放棄了做劇作家的夢想,填報了中央財經學院。畢業后去了廣州,后來是深圳、香港、美國。頭兩年,她跟李小山偶有明信片往來,之后各自沒了音信。
十余年間,李小山只見過到她一次。那是個春天的午后,忽然燥熱了起來,他感覺到倦意,懶懶的,就上街去溜達會兒。大街空蕩蕩的,車和行人都沒了影子,空氣中飄著嫩葉的清香,這是好聞的;也是讓人倍覺春困的味道。錦江飯店國際商場的櫥窗前,站了個年輕苗條的女子,白色喇叭褲,黃色蝙蝠衫,手腕上搭了條紗巾,像是在等人,也宛如剛從櫥窗走出來的模特兒。
他走攏去,兩人一對視,都立刻認出了對方。“李小山。”“蕭小紅。”友好的,老熟人口氣,不是久別重逢的驚喜。
“留校了吧?”還是蕭小紅話多些。
“是啊。”他點點頭。
“應該是講師,在評副教授?”
“嗯,是。”
“有女朋友了?”
“嗯。”
“而且是師妹?也留校,同一個教研室?”
“是啊。”
“等分配到一套兩居室就結婚?”
“嗯。”
“最后一個問題:還計劃好了,結了婚,但要等完成一項國家級課題再生小孩子,是吧?”她臉上推出兩絲假笑。
“是呀……你咋猜到的?”他有點迷糊。
“還用猜嗎?這么乏味,想都想得到。”
“那,你是咋過的?”
“我?”她吐了一口氣。“也挺乏味的。”
蕭小紅抬腕看了下表。
李小山就跟她告別了。
深冬,是個星期天早晨,李小山熬了夜,還在熟睡。父親的電話來了,叫了聲“小山……”,半晌不出聲。
李小山迷糊應了聲,話筒擱在枕邊,保持著睡意。
“奶奶死了。”
他從沒見過爺爺、奶奶,生下來他們就死了。開玩笑,還能再死一回啊?“哪個奶奶?”他咕噥了一句。
父親破口大罵。“哪個奶奶?你說還有哪個奶奶!奶奶對你這么好,你這個沒心肺的。”
他一下清醒了,是老爺爺家的奶奶。“爸,對不起,我……”應該給父親說道歉,說句哀悼的話?這未免滑稽了吧。可說什么呢?他還沒想好,父親又說話了。
“奶奶留了遺囑,喪事從簡,不舉行告別儀式,不接受任何人的吊唁……遺體捐獻,供醫學研究。”
“奶奶很偉大。”
“不用你來表揚她。”
“……”
“奶奶在遺囑中,還提了個條件,必須由你來解剖她。”
“這……咋個可能呢?”
“奶奶給你寫了遺言。你回來看吧。”
“……”
李小山晚飯前回到了父母的家。這是一月的傍晚,空氣又冷又濕,底樓的陰暗又讓冷添了些僵硬感。屋里沒開電視,也沒開燈,父親就黯黯地坐在沙發上等他。母親則縮在廚房中,鍋、碗、盤子、碟子,不時傳來冷冽的聲音,像夏天的冰塊在杯子里碎裂。
那張寫了遺囑的紙,跟奶奶手訂筆記本的內文紙一模一樣。遺囑的字跡,也和筆記本上的留言相同,蘸水鋼筆,娟秀,堅定,而且新鮮,宛如剛剛寫下的。
小山,我活了一輩子,一生一世,是個無用的人。
死了,把遺體捐出來,是想為國家、為你,做一點有用的事。
請你親手解剖我,在尸解課上給學生們做示范。謝謝你。
小桐
李小山感覺腦子空白,很不真實。“小桐?小桐是誰?”
“就是你小桐奶奶啊。”父親唏噓道。
“老爺爺,他還好嗎?”
“他還好,昨天上午還在打門球……都以為他會先走的,結果是奶奶。”
“奶奶得的是啥病?從沒聽爸說起過……”
“不曉得。都說不曉得,組織上打了招呼,不許亂猜、亂說。”
“亂說啥?”
“別亂問。”父親瞪了他一眼。“奶奶上午還去菜市場買了菜,回來給老爺爺燉了雪豆、蹄花湯,涼拌了折耳根青筍絲。然后,她在沙發上睡一會兒。這一睡就沒有醒。”
“……”
李小山快想不起小桐奶奶的模樣了。這會兒浮現出來的,是裹住全身的灰和黑,灰黑中一雙微瞇的眼睛,輕微顫抖了兩下的眼瞼。
晚飯是熱騰騰的。母親端上來一大碗筍子紅燒牛肉,文火煨熟的,肉、筋、干筍都極為軟和,湯汁收進肉菜之中,嚼來極有滋味。還有一盤撒了干辣椒末的油酥花生米,一碟清爽、脆蹦蹦的跳水泡蘿卜。父親幾乎沒動筷子,李小山則胃口大開,吃了兩大碗飯,還喝了一杯母親斟的枸杞酒,出了毛毛汗,一身通泰。
飯后,父子倆坐在沙發上,無話可說。一個還餓著,一個撐圓了肚子。母親想開電視機,可不敢,就對兒子說,“你上街轉轉吧,消飽脹,順便給我帶一包鹽巴。”
李小山在街上轉了一個時辰,發現自己走到了西御河沿街上。御河已經填了,準備蓋樓房。老街在等待拆遷。自己舊家的門前,那棵老泡桐還顫巍巍站著,高出了街燈一長截,但還能看見枯枝如鐵絲一般,冷黢黢,托舉著夜色。泡桐樹在三月開花,花謝了再長出闊綽的綠葉……等到深秋,葉子黃了、落盡了,春天的花梗、花托,還一串串留在枝條上,像一個一個的鐵疙瘩。好多年了,李小山沒這么仔細地端詳過老泡桐。
盡管夜色深灰,如黏了厚霧,但他還是看清了那些小疙瘩。看得很清,甚至可以挨個挨個數出來。
風在街道里嗖嗖吹。一個小東西飛來,他一下子迷了眼。起初,以為是粒小渣,或小蟲,小心揉了揉,居然沒有了。街燈下,無數的小蟲子飄舞出好看的橢圓形,那是南方冬夜的細雪。雪中有雨,冷徹、干凈的雨夾雪。
李小山在泡桐下佇立了很久。雪花落在他的頭發上,也落在睫毛上,轉瞬化為清水,簌簌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