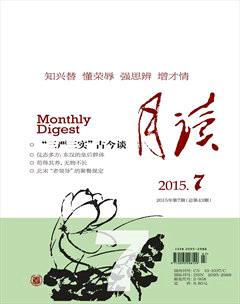茍得其養,無物不長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a,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b,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c。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d。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e。惟心之謂與?”(《孟子·告
子上》)
注釋:
a 牛山:在齊國都城臨淄南部。
b 萌櫱(niè):樹木萌發新芽。
c 濯(zhuó)濯:光禿的樣子。
d 梏(gù)亡:謂因受束縛而致喪失。梏,古代用于銬手的刑具。
e 鄉:通“向”,所向,趨向。
大意:
孟子說:“牛山上的樹木曾經長得很茂盛,因為它長在大都市的郊外,經常被刀斧砍伐,怎能保持其茂美呢?雖然它日夜生長,有雨露的滋潤,并非沒有新枝嫩芽生長出來,但緊接著的放羊牧牛,致使它變成了光禿禿的樣子。人們見到它光禿禿的樣子,便誤以為它不曾生長過成材的樹木,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
“在一些人身上,也有類似的情況,難道他們就沒有仁愛之心嗎?他們之所以失去了善良之心,是由于也像刀斧對待樹木那樣,天天砍伐它,怎么能茂美呢?盡管他們日夜息養善心,接觸清晨的清明之氣,他們的愛憎也與一般人有相近之處,但是他們第二天的所作所為,又把這些善的氣息消蝕了。反復地消蝕,就使夜里息養的善心不能存留下來;夜里息養的善心不能存留下來,便跟禽獸相距不遠了。人們看見他那近似禽獸的一面,以為他根本未曾有過善良的資質,這難道是他們的本質實情嗎?
“因此,如果得到一定的養護,沒有什么事物是不生長的;如果失去養護,沒有什么事物是不消亡的。孔子說:‘把握住就能存留,舍棄就會消亡;出入沒有一定的時候,就不知道何去何從。這就是針對人心而言的吧。”
【題解】
孟子把人性的仁義善良比喻為一座林木茂盛的山,而這座山一旦遭到日復一日的砍伐,遭遇過度放牧的損害,便不再是林木茂盛,而是光禿禿的了。接著,孟子又將山的破壞過程與人類善心丟失的過程相聯系,從而得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結論,“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這個富于哲理的結論,值得我們深思。
孟子在人性上主張善良,在政治上主張仁政,在做人上主張愛人,這不僅是孟子對人提出的理想要求,也是他的美好愿望。為了這一理想的實現,孟子提出了“養”的觀點,即社會環境要對善良的東西予以保護和培養,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把握住自己的善心并堅持不懈地加以培育。這一觀點,至今對我們的成長和社會的發展也是大有益
處的。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論養之道詳盡而深刻,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養人、養正、養德、養賢,以及萬物天地之養的真諦。(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