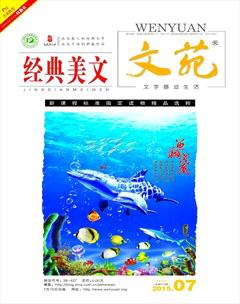玉米的聲樂課(外一篇)
何鑫業(yè),詩人,作家,記者,浙江省廣播電視集團藝術(shù)類一級文學編輯。上世紀八十年代寫詩,發(fā)表詩歌三百余首;九十年代寫小說,開創(chuàng)生物學小說流派,代表作《人,或化學元素喬》;二〇〇〇年后做電視,參與《我愛記歌詞》《中國夢想秀》《中國好聲音》的評審和策劃;到了二〇一〇年,開始進入繪畫界,進行油畫刮刀畫的創(chuàng)作。
如果你清早走進玉米地,半個時辰后出來,如果你沒有沾一身的水,那就不叫玉米地,那是露水,兄弟。
如果你太陽落山時走進玉米地,也是半個時辰后出來,如果你沒有染一身的紅,那也不叫玉米地,那是霞光,兄弟。
就算吧,玉米地中耕的時候,你開著拖拉機,或者你就坐在拖拉機上,你往前看,你只要往前看,如果你不覺得,這世界,充其量也不就是塊玉米地,黑油油,起起伏伏,一望無際,那你準是個糊涂蛋、二百五!
玉米地中耕,你該知道的吧?對,就是玉米長到小腿肚子高的時候,給玉米地松土,這在玉米的成長過程中,只能算一個簡單的培訓,或者叫未成年人洗禮——你的拖拉機劃過玉米棵棵,玉米低了一下,這就像,上課鈴響了,你用手劃了一下你的學生的頭皮:“去!上課吧……淘氣鬼!”——你是這些玉米的班主任,你得保證它們的學業(yè),釋疑解惑,茁壯成長。
等你拿一瓶子,在地頭喝酒的時候,你完全顛覆了教師形象。這時候你更像一個痞子,是啊,玉米愛長什么樣跟你有什么關(guān)系!半毛錢關(guān)系都沒有!這世道,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都,誰跟誰啊!而且,而且我要告訴你的是,當你是痞子的時候,玉米才是痞子他爹呢!玉米才不管你呢,它哧溜溜地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長,大路朝天各走半邊地長……拔節(jié),抽穗,灌漿,一系列的規(guī)定動作啊,完成得都很漂亮!也就是說,你酒喝完,玉米已經(jīng)長大成人了——這,有點像,你離家一陣,出差或者離異,三四年吧,突然回家,你兒子,這小子,長得那么高了……怎么有胡子了,難看死了!
其實,玉米就是找準我們不留意它的時候,才猛長猛長,一口氣地猛長。
接下來,我還是想說玉米地的大——這個東西非說不可——這樣說吧,還是玉米抽穗那會兒,你去鄰村參加一個婚禮,吃喜酒,發(fā)小的。你愛炫技,你騎著馬去,沿一條玉米地蹦跶。這天,也該你倒霉,玉米正長穗,有芬芳溢出來。你騎著馬,騎著騎著就犯嘀咕了,怎么就感覺這玉米地要比馬厲害呢!跑了一晌午,結(jié)果還沒跑出玉米地!你勒住馬,一掐表,一抬頭,哇哈!馬已經(jīng)呼哧呼哧的了,可玉米地還遠著呢。
玉米正長穗,有芬芳溢出來,剛才說到。其實,玉米長穗,就是玉米長胡須,像你兒子那樣,很普通的事情。是不是很Man,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芬芳溢出來,采粉授粉的就來了,你騎著馬過,你當然不是采粉也不是授粉,可玉米哪里會知道。最大的可能是,它騙昆蟲的時候把你也騙進去了。我說的它,是指玉米,當然啊。況且,你的迷路,與風向也有關(guān)。
風朝下風口走,你往上風口走,這不就迷路了嗎?玉米地多大啊,一望無際,風多大啊,一望無際,玉米多有范啊,胡須飄揚。小學五年級時,我們班主任講解宇宙時,舉的例子就是村外的玉米地——他說,像玉米地那么遼闊,像玉米地那么無垠,像玉米地那么有容乃大——至于,你說玉米抽穗時只有清香,幾乎聞不到芬芳,那是因為你不懂。如果你知道它要傳多遠,你就不會怪它了,它要傳三個村莊,行程四五華里,最后與鄰村的孢子結(jié)為伉儷,才告一段落。
我說的是段落,兄弟。我說的是段落,不是玉米的整個歷史。玉米的整個歷史比我們?nèi)祟惖囊L得多,也就是說,5000年前,我們不在的時候,玉米已經(jīng)在了,5000年后,我們不在的時候,玉米還一定在,是不是這個理,兄弟。
俗話說得好,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其實,你沒見過玉米地,難道還沒吃過玉米棒子嗎?就它的香,它的顆粒,它的糯,它的嚼口(我就是不說它的金黃),已經(jīng)可以見出這塊玉米地的非同凡響了——簡簡單單一根玉米棒子,要多少大自然的機構(gòu)參與啊,它的土壤,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坡,它的下風口上風口,它的鄰居友人,也就是那些昆蟲……
我插隊時的老連長說過,他是當年哈軍工的,了不起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出了多少人啊!他說:“……你以為呢?告訴你吧,玉米學齡前、身體發(fā)育前或者中學畢業(yè)前,誰給上的聲樂課知道嗎?誰?什么?錯!……是,烏鴉,鷓鴣,斑鳩,喜鵲,蟋蟀,紡織娘,還有蚯蚓,給玉米上的聲樂課啊,兄弟……”
棉花以溫暖著稱
棉花地在村子的東頭,很大的一塊棉花地,大得一望無際。
棉花沒開的時候,走夜路,走著走著,走進了棉花地,還以為是玉米地或者大豆地,捋一把葉子聞聞,扎手,才知道是該死的棉花。
該死的棉花還有個該死的地方,它不能當糧食。老人說,曾經(jīng),沒飯吃的那幾年,村里誰都傻想過,棉桃要能吃就好了,滾圓滾圓的,有個尖尖頭,那是下嘴的地方。現(xiàn)在想想,那么多的棉桃,要是僅僅只能吃,爛在地里可怎么辦!
說起爛在地里,主要是這棉花地大。這么說吧,趕早起,你就扛著個鋤,不用耪地,你就扛著鋤走就行,走到黑,沒準兒還沒走到棉花地的頭呢。還有,這棉花邪門,你想著它吧,它老不顯樣子給你看,懨懨的,只長風,不長搖擺。你不想著它了,哧溜,棉桃結(jié)出來了,哧溜,棉花開出來了,哧溜,連棉稈子都砍了,空蕩蕩一片,害得你瞎想……誰干的?都誰干的?都,哪會兒的事啊?
棉花地最近的地方,離村莊也有一華里路,可躺在炕上的老人,能把棉花地東南西北分分寸寸數(shù)落得清清楚楚,仿佛,棉花地就在炕沿,一探身子,一招呼,就信手拈來:“今兒個……該死的棉花,今兒個……把老張頭李叔王叔叫上,還有她嬸,再不頂,也得去打尖了!”這是在說,棉花的枝葉太盛了,會不結(jié)棉鈴,要打尖了。
打尖,就是整枝,把多余的枝打掉,讓風吹進去。打過尖的棉花地,像理過發(fā)的男人,頭皮青青的,鬢角推得很高。風,吹進棉花地,整個棉花地就喝醉酒,既長風,又搖擺,一波浪一波浪的。一只大鳥擦著男人的鬢角飛進去了,飛進去就不見了,等到飛出來的時候,由于遠,由于太遠,變成一只麻雀了……
大鳥,可能是一只鸛一只鷺鷥,它是棉花的近親,相當于人類的表親;也可能是鄰居,是友人,反正,它們有邀約。鸛或者鷺鷥的到來,是天與地合同款項中的一項,有點像李龜年遇上突然漂泊南來的杜甫,是唐代詩歌中的一項,完全是造化,完全是奇跡,完全不受人控制。鸛鉆進去,稍作停留,鷺鷥鉆進去,稍作停留。這中間,棉花地少了一些什么,又多了一些什么,它們,有沒有吟詩作畫,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有沒有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沒有人知道。
楊樹再不濟,也是棉花的盟友,這與大豆不同。試想啊,再大的棉花地,沒有幾排楊樹,那簡直是失策,簡直是不懂得設(shè)計,簡直是客人來了,門開了,不讓棉花穿褲衩。況且,楊樹還是鸛和鷺鷥的婆家,喝口水,歇歇腳,再也是它飽腹后作亂作淫的地方。
種過大豆的地,農(nóng)人就再也不肯種棉花了,所以,大豆是棉花的仇敵,也是合同的下家,合同另一方。其中,大豆是小人,會使點小伎倆,這小伎倆就是饑餓,就是自然災(zāi)害,兵荒馬亂。而,棉花永遠不卑不亢,永遠慢條斯理,永遠只以溫暖著稱……
就因為,大豆與人的生存需求距離近,而,棉花與人的生存需求距離遠。大豆馬上可以吃,摘了吃,剝著吃,煨著吃。棉花,且得等呢,到了秋后不算,還得紡,還得織,還得絮,且與胃不搭邊,不落胃,該死的棉花還不產(chǎn)生熱量,雖說保護暖,但慢著呢。所以,大豆現(xiàn)實,棉花理想,所以,大豆是亂世安好,棉花是歲月靜美。所以,兵荒馬亂種大豆,現(xiàn)世安寧種棉花,所以,我們通通一致心甘情愿種棉花,打死也不種大豆。
打過尖的棉花地,你走進去,腳涼颼颼的。身子蹲下去,看見的不是棉花地,而是一條一條的棉花的腿,棉花大腿,是,不穿球鞋板鞋皮鞋的大腿,足足有千軍萬馬。
幾百年來,這棉花地,或者說這該死的棉花,還左右村子里人們說的話。譬如“今兒個……咋啦!像摘棉花似的,軟不拉嘰,還扎手!”這,明顯是對上眼的兩個男女在調(diào)情嘛——但,話頭子,怎么也是來自棉花。
而且,即使一天沒活干,老人也情愿坐在棉花地頭,看看云,看看天,說說閑話:“一是一,二是二……世道再不濟,這棉花中,也沒有不說人話的!”而且,這個村子的所有人,即使不去棉花地的時候,腦子里也都是這該死的棉花。
- 文苑·經(jīng)典美文的其它文章
- 經(jīng)典碎片
- 沒有人可以替代你努力
- 有你陪伴,不覺孤單
- 愛的圓規(guī)
- 一窗如畫
- 最美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