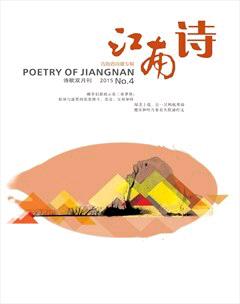累斯博斯島上的第十位繆斯——薩福
姜海舟
薩福(Sappho,約前630或者612~約前592或者560),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一生寫過不少情詩、婚歌、頌神詩、銘辭等。一般認為她出生于累斯博斯島一貴族家庭。豐盛的財富使她能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她選擇了在當時的文化中心勒斯博(Lesbos)島上專攻藝術。她的父親喜好詩歌,在父親的熏陶下,薩福也迷上了吟詩寫作。她是第一人描述個人的愛情和失戀的詩人。青年時期曾被逐出故鄉,原因可能同當地的政治斗爭有關。被允許返回后,曾開設女子學堂。古代流傳過不少有損于她的聲譽的說法,但從一些材料看,她實際上很受鄉人敬重。
當時的希臘女性沒有婚姻自主權,尤其是貴族婦女。現在無從考證薩福是否愿意,只知道她在成年后嫁給了一位貴族,還生了一個女兒,但是沒有過多久,她選擇了離開丈夫和家庭。她先是在西西里島住了一段時間,又返回故鄉,并在那里度過了余生。在羅德斯島,薩福建立了一所女子學校,專門教導女孩子們寫作詩歌。當時有不少少女慕名而來,拜在她門下。薩福以護花者的愛戀心情培育她們,同時也像母親一樣呵護她們成長,為這些花一般清新美麗的少女寫下了許多動人的情詩和婚歌。古希臘人對同性之間的愛情抱有很大的寬容之心,所以這些帶有強烈同性戀情感的詩歌不但沒有遭禁,反而廣為傳頌。薩福的詩打動了許多人,羅德斯島上的居民也因出了如此才華橫溢的詩人而感到自豪。為了表示他們的愛戴和驕傲,在薩福還活著的時候,他們就在銀幣上鑄上了她的頭像。薩福是古希臘的著名詩人,也是世界古代為數極少的幾位女詩人之一。從奧維德的傳說來看,詩人因為一名年輕水手法翁(Phaon),而心碎跳崖自盡,喪命英年。別的史學家則認為詩人一直活到公元前550年左右才壽終正寢。
有關詩人詩歌的史料同詩人的傳記一樣撲朔迷離。人們只知道她是上古時代的一位偉大的詩人:古希臘人十分稱贊她,說男詩人有荷馬,女詩人有薩福,柏拉圖曾譽之為“第十位繆斯”。她的詩對古羅馬抒情詩人卡圖盧斯、賀拉斯的創作產生過不小影響,后來在歐洲一直受到推崇。詩人的肖像曾上過硬幣。詩人的詩作大約于公元前3世紀首次輯成9卷行,但流傳至今的極少,僅有一首28行的詩作保存完好,到19世紀為止,人們主要是通過其他作者的引用得以了解詩人的。1898年學者們出土了一批含有詩人詩作殘片的紙草。現代的各種版本中,詩人詩作的殘片累計已達264片,但僅有63塊殘片包含完整的詩行,只有21塊含有完整的詩節,而迄今能讓我們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的近乎完整的詩作僅有4首。第4首是2004年新發現的,這首12行的詩作是在一具埃及木乃伊上面的紙草上發現的。該詩連同牛津大學學者馬丁·韋斯特的英文譯文發表在2005年6月第3周出版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
薩福被冠以“抒情詩人”之名,是因為在那個時代,詩歌是由七弦琴伴唱的。薩福在技術和體裁上改進了抒情詩,成就了希臘抒情詩的轉向:從以諸神和繆斯的名義寫詩轉向以個人的聲音吟唱。
薩福留有詩歌九卷之多,但目前僅存一首完整的詩章,其余均為殘篇斷簡。從公元前三世紀起,薩福的名字就開始出現在詩歌、戲劇和各種著述中,她逐漸被神化或丑化,按時代的需求——或被喻為第十位繆斯;或被描繪為皮膚黝黑、長相丑陋的女人。中世紀時,因她詩篇歌詠同性之愛而被教會視為異端,將她的詩歌全部焚毀。若不是在十九世紀末一位埃及農民在尼羅河水域偶然發現紙莎草本上記載薩福的詩歌,被淹沒的詩歌會更多。但薩福的傳奇始終流傳著,尤其是在各代詩人們心中成為一座燈塔。
薩福的詩溫婉典雅,真情率性,大多以人的愛和欲望為主題——不同于她以前的詩歌是以神作為歌吟的對象——詩中充滿了愛的勸喻、愛中的甜美與痛苦或兩者相互交織的情愫,以及彌漫著憐憫和嫉妒的悲鳴之聲。讀她的詩歌,猶如冒險去遠航。
薩福的詩藝很高,在目前僅存的詩篇中已經能夠看出她嫻熟運用暗喻(不像荷馬時代多用明喻)這種現代詩歌的技巧,使詩歌形象和內在涵義更為豐富和飽滿,如她描寫鴿子,意象優美而凄婉,鑲嵌著她難以述說的某種落寞情懷;又如上述引文中的“戰車和驍騎”,除了具體所指外還暗喻著男人。 此外,有時她的詩歌又像浪漫主義時期的抒情詩,將大自然的風物山川用來象征自己微妙心緒。
薩福的詩體是獨創的。西方詩歌史上把這種詩體稱之為“薩福體”。它們是獨唱形式的——荷馬時代和古希臘悲劇中有許多是歌隊的集體合唱——詩體短小,以抒情和傾述內心情懷為主,音節更為單純、明澈。在“薩福體”的格律中,每一節分為四行,每一行中長短音節在相對固定中略有變化,前三行有點像荷馬時代的六韻步詩體,第四行則音節簡短,顯得干脆明快。相傳,與薩福同時代的雅典統治者梭倫也是一位詩人,當他偶然聽到薩福的詩篇時說“如果我學會了她的音律,可以死而無憾了”。
薩福的詩體類似于中國古代的詞,目的在于供人彈琴詠唱,但她往往自己譜曲。薩福不僅在技巧上創立了“薩福體”,改革了當時詩歌創作的韻律,而且與其他詩人一起,在風格上把詠唱的對象從神轉移到人,并用第一人稱來抒發個人的哀樂,在當時相當革新。
薩福的作品多為柔美婉約的渴求愛戀的情詩,并且常常為她的女弟子所作。當時很多年輕女子慕名來到勒斯博島,拜學在她門下。薩福不僅教與她們藝術,而且寫給她們表達強烈愛慕的情箋。當弟子學成離島,嫁為人婦時,薩福還為她們贈寫婚詩。古希臘盛行師生間的同性戀情,師者授業解惑,弟子以情相報,所以這些帶有強烈同性戀情感的詩歌在當時不但沒有遭禁,而且還廣為傳頌,甚至連Lesbos島上用的貨幣都以薩福的頭像為圖案。在薩福由于家庭原因流亡于西西里島時,那里的居民為她豎起了雕像以表愛戴。
薩福詩歌的翻譯難度很高。因為很多片段已遺失,所以翻譯者需要根據上下文的意思和韻律用古希臘語先進行“補缺”。這種“補缺”不免帶有揣測成份,在技巧與風格上可能會與原詩有所出入,而譯者添加的表達也可能有別于薩福的原意。但是對于許多讀者來說,如果沒有這些努力,薩福的詩歌也許永遠會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