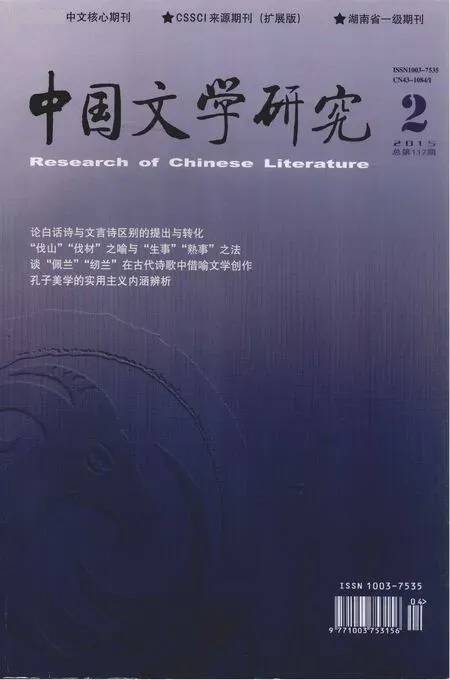平遠臺詩社與順、康晉安詩壇風尚漸變
翟 勇
(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終明一世,晉安詩壇雖然在萬歷、天啟時代受到了來自外部竟陵派“幽深孤峭”詩風的沖擊,但是內部主流詩風始終以尊盛唐面目示人。然而隨著朝代更迭,順、康年間晉安詩壇在詩學宗尚上不再是整齊劃一的鐵板一塊,少數詩人不再固守盛唐詩之昂揚雄渾的詩風,探尋的目光開始轉向宋詩之瘦硬樸拙的風格。初創于順治年間、興盛于康熙時代的平遠臺詩社前后綿延近百年時間,詩社無論成員人數亦或影響皆冠絕當時晉安詩壇。但是今人對此詩社以及這一時期關注很少,因此本文擬以平遠臺詩社為窗口,窺探順、康近百年晉安詩壇詩風漸變過程。不確之處,望方家指正。
一、平遠臺詩社的成立

平遠臺詩社成員眾多,為更直觀地了解其成員情況,特列簡表如下:

?
除上表所列32 人之外,李涵,浙江余姚人,都督;顧鴻典,長洲人,白長庚,延安人;張恒,上海人;何錦,不詳。

二、宋風漸起:“平遠社七子”的分化
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卷一載:“林偉,字草臣,康熙間侯官諸生,與孫學稼、許珌、許友、高兆等,稱平遠社七子。”文中僅提到五子,其他二字為誰尚不得而知?據“國朝平遠臺詩社,前則高云客兆文學、鄭山園宗圭大令、陳偶庵騄、叔舉驤兩文學、孫君實學稼隱君、許天玉珌大令、甌香友處士也”〔1〕(p680)的記載推測,另外二子當為鄭宗圭與陳騄、陳驤昆仲其一。
“平遠社七子”一生主要活動時間集中在順治及康熙前期,與曹學佺、謝肇淛等宗唐派大家尚能接武,但是在其內部卻出現了宗唐與趨宋的分化。隨著啟、禎時代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曹學佺、謝肇淛等人的離世,晉安詩壇在順治、康熙年間的全國影響力急轉直下,這時晉安詩壇急需一位文壇領軍人物,高舉宗唐大旗的高兆擔當了這個責任。林白云《閩詩選》云:“云客詩名藉甚,吾閩稱詩家者,無不推云客。”高兆不僅身列“平遠社七子”之一,并且“與彭善長、陳日洛、許瑨、卞鰲、曾燦垣、林偉俱有詩名,稱國初七子。”此外,高兆與當時詩壇大家周亮工、毛奇齡、紀映鐘、汪楫、施閏章等交往密切,通過他們向全國傳遞晉安詩壇的聲音。周亮工于順治四年(1647)任福建按察使時,高兆與周亮工即結為好友。后周亮工于順治十五年(1658)被捕下獄,高兆為其到處奔走,還特地為周亮工寫詩述哀鳴冤。周亮工在《題高云客詩后》中記錄了對高兆的感激之情:“自吾負雙腕來,未嘗書今人所為詩若文。頃為陳生駿乞茅屋入白云司侍其老親,頗為感動,賦詩二章示駿,駿因出高兆送其入燕詩示予,予讀之,不禁涔涔淚下。”另外,毛奇齡《西河詩話》記載與高兆的交往軼事:“丁卯客福州,……適同席者鄭畿庭先輩高固齋在坐。間并讀余所為《曼殊別志》,甚感。固齋因吟云‘豐臺人在翻新句,小調應名洗露紅’,遂作洗露紅詞吊之,……亦一佳話。”高兆與施閏章、紀映鐘、汪楫等人亦多有交往,不再一一贅述。高兆論詩宗唐不僅體現在與上述幾位宗唐派詩人的交往上,其在《與汪舟次》一書中亦有明確表述:“《唐詩正音》、《唐詩品匯》固當置案頭,然《詩歸》亦不必定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伯敬取譏,獨在好異耳。至如《唐詩選》、《正音》之約與《品匯》之博,三書自須時一參看為妙。”《唐詩正音》、《唐詩品匯》等書恰是終明一代宗唐派詩人奉為圭臬之書。鐘惺之詩雖為高兆貶斥,但是認為其詩論尚有可取之處,這恰在于鐘惺論詩亦主張學唐人。至于高兆本身詩歌創作,客觀地說總體成就不高,郭柏蒼云:“高固齋詩,酸澀而多排偶”,林白云亦疑惑“予未得其全集。遍搜他選,俱不甚愜意,豈予所見者隘,抑亦眼力未到耶?”但是從詩歌風格上高兆仍然努力實踐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主張,《消夏錄》稱其所作《荷蘭使舶歌》“紀述詳明,見微知著,真可作一篇籌邊策讀,卓然與杜□代興無疑也。”
“平遠社七子”之孫學稼、林偉等人詩作我們亦能看出步武晉安詩派傳統的影子。如孫學稼《登道山觀》:“高丘晴翠引登臨,彤閣巍然壓遠岑。遂有千蕤通羽騎,疑從五岳覓青琳。江光俯檻浮潮汐,山色橫霄自古今。清曉露寒聞禮斗,步虛聲入白云深。”詩格調清壯,氣勢雄渾,直接盛唐氣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七子之中的許珌、許友昆仲此時已經開始反思固守唐詩藩籬的弊病,轉向在宋詩中尋找養料。許珌(1614—1672),字天玉、一字星庭,號鐵堂,別號天海山人,侯官人。曾官安定知縣,客死隴上,有《鐵堂詩草》上、下二卷存世。許珌早負詩名,與著名詩人王土禎、申涵光等交誼甚密。許珌為詩“其大旨本于黃先生。”此處黃先生即指銳意變革閩詩風,倡導宋詩的黃道周。許珌詩作閻介年認為:“鐵堂之詩沉雄富厚,組練雕飾,一歸于老成;于閩中詩派稍為變化,不甚規矩唐人而骨骼堅凝,精光迸露。”施閏章也注意到:“許子之詩,絕不屑為靡郁之言,堅骨強氣、怵肝裂腸。”許珌作詩不規模前人,所作詩亦多情真意切,如《悼亡詩》:“千里窮交脫贈心,蕪城春雨夜沉沉。一官長物吾何有?卻損閨中纏臂金。”據《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十《文苑傳》載:“珌嘗與計偕過揚州。士禛時為郡司李,解內子金條脫,資其旅橐。”妻子脫金助夫,今日卻為一偏遠之地小官與妻陰陽兩隔,值否?再如《鐘山詩次杜濬四首》,即景抒懷,感嘆明亡后改朝換代之物是人非。明孝陵的破敗也暗含著作者惆悵的情懷:“孝陵陵上草凄凄,日落江南杜宇啼。金瓦久經麋鹿竄,玉環空鎖鳳凰棲。青氛大地歸科斗,紫氣中天散鼓鼙。一自尊靈茲永蟄,才非曹植敢重題。”
許珌昆仲許友,朱彝尊評曰:“有介才兼三絕,名盛一時。……要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許友不僅如許珌一樣,“不屑蹈襲前人”,同時師事倪元璐。陳衍根據風格特點把宋詩派分為兩派,其中一派為生澀奧衍,倪元璐正為其中代表。許友詩“為佶屈聱牙之辭,掉頭攘臂,坼馳其間。”如《學死》一詩:“置我空中山,破茅一間止。兩扇苦竹籬,風吹半歌倚。隔溪啼古猿,虎饑舌自舐。老狐帶粉髏,叉手習拜起。月暗窺我門,嘻笑露其齒。腥寒漸迫人,吹燈彈窗紙。此際身兀然,由我心先死。學死先死心,未死死同理。”許友詩又有“淡如菊,清如竹”的清曠脫俗之氣,如《神光寺看碧桃花》:
城頭二月綠苔侵,為訊桃花野寺尋。半樹香分疏竹影,數株白近古松陰。
蝶心蕩漾春高下,鳩語浮沉雨淺深。蔬筍偶然無酒禁,醉歸清夢戀空林。
明麗寂靜的美景之下隱含著作者的幽獨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寫照,有林逋、蘇軾疏曠之風。
但是我們要明確的是,順治、康熙前期晉安詩壇雖已不再是整齊劃一,但是宗唐詩風仍是主流。此一時期晉安詩壇詩風正如賀國強、魏中林二先生所描述:“由明代的風雅正體蛻變為變風變雅,同時在當時詩壇祈尚宋詩的感召下,終于如蠶化蝶般逐漸蛻去了格調圓穩的定式,而茁生出宋化詩風的枝條。上述諸家雖受宋詩范型的影響,但其詩風并不曾形成具有時代特宗宋風范。”
三、唐宋并峙:康熙四大家的崛起
“康熙間,郭雍、張遠、林豫吉、張崙為四大家。”郭雍、林豫吉二人為平遠臺詩社成員,其詩郭柏蒼贊曰“美不勝收”,因此二人可為康熙中后期平遠臺詩社代表。二張雖未有明確記載名列平遠臺詩社,但是在當時晉安詩壇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張遠與郭、林二家共同左右著康熙晉安詩壇宗尚的演變。
林豫吉,字不飛,長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工詩善書,挾智任術,明律令。有《林松址詩》。鄭杰《注韓居詩話》:“松址詩學杜,甚有骨力。”如《樓夜》:“野曠星偏大,江冥水自聲。人煙休遠市,漏鼓起荒城。鐙下一杯酒,樓頭萬里情。風塵空老去,吾亦感生成。”首聯模仿杜甫《旅夜抒懷》“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但境界狹窄。頸聯模擬李白《送儲邕之武昌》之“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全詩境界寂寥,中間又偶露崢嶸,最后歸于對自身遭遇的人生感嘆。詩學杜之老蒼勁健,但失杜之深情遠韻。
杜之詩既有老蒼勁健,亦有清麗明婉,亦為林豫吉詩風追求,如《夾溪桃花盛開得野老邀酌》:
溪上桃花春自開,漁郎煙棹幾時來。天留湖海吾為客,日靜桑麻此泛杯。
社鼓忽傳江燕至,鄉書猶阻塞鴻回。鹖冠野老行藏異,雞黍殷勤去后猜。
全詩清新明朗,富有鄉間田園氣息。同時對仗工整、用律嚴謹,嚴遵杜之家法。此外,詩亦吸收唐詩字、句之絕巧,“春自開”化用韋應物《滁州西澗》“舟自橫”,“日靜桑麻此泛杯”化用孟浩然“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雖為化用,但又毫不生澀,是為林詩中較好者。
郭雍(?—1723),字仲穆,又字書禪,福清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舉人,有《約園詩鈔》。郭柏蒼《竹間十日話》云:“時人愛郭約園者,極詆林松址;好林松址者,又極詆郭約園。”民國《福建通志·文苑傳》:“雍作,上焉者步趨王、孟,次亦刻露清新。”杭世駿《榕城詩話》:“(郭雍)古體學陶,近體宗王、孟,五言猶稱長城。”黃錫蕃《閩中書畫錄》:“(郭雍)博學能文,詩窺唐人閫奧。”郭雍自稱:“吾前后作詩不下千篇,今存其略成章法者,得律詩絕句若干首,古風歌行僅留一二,樂府絕無所解。俟十年后,別有窺尋,乃敢議及。”綜上所述,林、郭二人皆學唐,區別在于學唐人的哪種風格,亦即郭柏蒼所述“究之,各具體格”。舉例明之,《瀨溪夜渡》:“月明行十里,寂靜瀨溪船。遠火時過樹,幽禽早宿煙。村斜穿徑入,石碎斷橋懸。對此羈懷滿,臨風獨扣舷。”詩風在王、孟疏朗風神之下,暗含劉長卿清冷寂寥之感,然而缺乏王、孟、劉興在象外、雋永味長之妙。另外,其詩往往前兩聯學王、孟之清朗,后兩聯學劉長卿之寂冷,形成“五言律詩頗有局度”的特點,如《遙和諸子宿北阡草廬》:“不緣茲地迥,青屐肯為停。細草香侵露,高林遠帶星。鳥鳴千嶂白,簾定一燈青。更愛松風詠,惟余猿鶴聽。”
康熙四大家之一的張遠可謂晉安詩壇在康熙年間一轉關人物。張維屏評其詩“遙情逸氣,頓挫瀏漓,獨能拔出閩派之外”,陳慶元先生贊其是“清初閩詩人之冠”。張遠(1448-1522),字超然,侯官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舉人,官祿豐知縣,有《無悶堂集》。張遠論閩詩,于晉安詩派頗為不滿,在《張恫臣詩序》一文中較為集中地闡發了自己的詩學理念:“夫閩海之偏僻壤也,山高峭而川清冽。其風俗尚氣節,其為詩宜乎奇峭而秀異矣。自林子羽以平淡之詩鳴,嚴滄浪、高廷禮輩后先繼起,唱為盛、中、晚之說,遂習以成風,逮《晉安風雅》書成而閩風寢弱矣。后之作者,襲其膚淺浮泛之詞如出一律,自束其性情,以步趨唐人之余響,其不振也宜哉!’”綜上所論,張遠論詩強調獨創,有真性情:“詩言志而已,不知有六朝、三唐、兩宋。”并且應該根據閩地獨特的地貌風俗,詩宜奇峭秀異。但是這并非菲薄唐詩,而是反對晉安詩派詩學盛唐的狹隘觀念。因此張遠為避免熱熟,詩學宗尚更加廣泛:“漢魏詩渾含質樸,皆以意勝。至謝靈運變而璀璨,華采煥然可觀。嗣是而降梁陳,迄隋日趨綺靡,陳子昂以典雅澹遠振之。至杜少陵縱橫變化,集諸家大成,詩人之能盡之矣。而韓昌黎以刻畫排奡持立其間,其才氣沛然充滿,遒健雄深,詩人之杰也。宋詩之博大者,莫過于蘇子瞻,子瞻取法杜、韓,乃以才學變其體裁,不規規于古而自成一家,可謂善法古人者。”因此后人在評價張遠之詩時亦注意到其轉益多師的特點,《四庫全書總目》云:“(張遠)詩多近元、白長慶體,在晉安詩派中為別調。”陳衍亦曰:“近復細讀全集,乃知先生五古多學韓,近人鄭子尹作,甚與相似,《哭母》一首其最也。七言參以太白,才筆興象,足以軼長水、跨新城。”謝章鋌評價其詩風“筆意疏秀,得力于眉山為多。”張遠學韓較突出者如《下建溪諸灘》:“造物產湖海,至此窮變化。若匪眾盤渦,閩溪高可瀉。仙霞插霄漢,天險此其亞。”韓詩五古奇絕險怪,并以文為詩,此詩深得其味。學蘇軾“疏秀”,如“銜山斜月上,獨樹一舟維”,“春色荒村外,愁人細雨中”等。總之,雖然黎士弘云:“國初鰲峰、光祿諸老,猶守林、高矩鑊,孑而立者為張超然。鄭、張獨唱,不勝眾和,閩派固始終如故也”,但是“(張遠)所倡導的‘奇峭秀拔’詩風及他本人的詩歌實踐則為閩詩伏下學宋的潛流。”
四大家中張崙詩流布不廣。張崙,字蒼嵋,一字文園,侯官人。康熙間監生,授河間府中河通判,所著《晚香堂集》。張崙詩多學李白歌行體,風格清新郎暢,如《擬古》、《江上行》。但是一些詩亦有宋詩平淡清遠之格調,如《村居薄暮》:
遠岫銜殘照,高樓俯暮花。牧童喧在背,漁父水為家。
寵辱安時命,悲歡閱歲華。門無車馬轍,早晚此桑麻。
此詩前兩聯寫鄉間傍晚之閑適溫馨之景,語調平和而意態幽遠,即景即情,顯得清新自然。后兩聯表達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富于理趣,透漏出宋詩筋骨思理見勝的氣息。
結 語
順、康晉安詩壇與萬、啟時代相比,無論是從詩人的影響亦或是詩歌創作質量都明顯處于下風,同時亦不如晚清閩派“同光體”在全國的地位。但是順、康半個多世紀卻正是晉安詩壇由終明之世獨尊唐詩神清俊朗詩風到漸開宗宋瘦硬樸拙之氣的重要轉折期。令人略微遺憾的是,今天治閩詩者往往忽略了這一時期,這對我們完整了解明清兩代閩詩風尚轉變十分不利。因此筆者不揣淺陋,書成此篇,權當拋磚之用。
〔1〕謝章鋌撰,陳慶元、陳昌強、陳煒點校.謝章鋌集〔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2〕郭柏蒼.竹間十日話〔M〕.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3〕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藏弆集〔M〕.周亮工全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4〕鄭方坤.全閩詩話〔M〕.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02 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尺牘新鈔二集〔M〕.周亮工全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6〕郭柏蒼.烏石山志〔M〕.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7〕計東.改亭文集〔M〕.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08 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許珌.鐵堂詩草〔M〕.四庫未收書輯刊本〔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9〕陳世镕編撰.福州西湖宛在堂詩龕征錄〔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0〕徐景熹等修.乾隆福州府志〔M〕.上海:上海書店,2000.
〔11〕朱彝尊.靜志居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12〕福建通志局總篡.福建通志〔M〕.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
〔13〕錢謙益.吾炙集〔M〕.虞山叢刻本.
〔14〕顧雪梁.中外花語花趣辭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5〕賀國強、魏中林.論清初閩派宗宋詩風的衍生〔J〕.江西社會科學,2006(03):88.
〔16〕徐世昌.晚晴簃詩匯〔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7〕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M〕.清代傳記叢刊本〔M〕.臺北:明文書局,1985.
〔18〕張遠.無悶堂集〔M〕.康熙刻本.
〔19〕紀昀.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0〕陳衍.石遺室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1〕黎士弘.托素齋文集〔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3 冊)〔M〕.濟南:齊魯書社,1997.
〔22〕陳慶元.清初閩詩人之冠——張遠〔J〕.古典文學知識,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