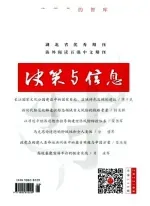理順城市管理執法體制的決策思考
文/王孝兵
提起城管執法,可謂是家喻戶曉,當問及何為城管執法,恐怕鮮有人能準確回答,即使是從事城管執法者,也難以說清道明。究其原因,主要是城管執法職責不明,機構設置混亂,執法隊伍五花八門,歸根到底,就是城管執法體制存在重大缺陷,此種狀況終究導致城管執法備受責難,飽受詬病,嚴重影響黨和政府形象。城管執法也因此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均提出要“理順城管執法體制”,把理順城管執法體制作為深化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納入最高決策層面,中國城管即將迎來新的曙光。然而究竟如何才能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學者、專家乃至城管人也是眾說紛云,筆者結合從事城管執法工作二十多年的實踐體會,通過深入調研,提出理順城市管理執法體制的幾點決策思考。
一、城市管理執法的職責
城市管理執法包括城市管理范圍內的行政檢查權、行政處罰權和行政強制權的行使,不包括行使行政決策權、行政許可權和行政征收權等。在現實中,城管執法任務主要是由專門的城管執法隊伍來承擔的,這支執法隊伍就是社會上所稱的“城管”。城市管理作為一個獨立的管理門類,產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脫胎于城市建設領域,至今經歷四十年左右的時間。
就目前而言,全國大多數城市的“城管”不僅履行著城市管理領域的執法職責,而且承擔著環境保護、城市規劃、工商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執法職責,也就是通常所說的“7+1”城管執法職能模式,也是所謂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即:城管執法部門集中行使市容環境衛生管理、城市綠化管理、市政管理方面的全部行政處罰權和城市規劃管理方面關于違法建設、環境保護方面關于社會生活噪聲污染、建筑施工噪聲污染和飲食油煙污染、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無照商販、公安交通管理方面關于侵占道路行為的行政處罰權和相應行政強制權,以及省市人民政府規定的其他職責。采取這種模式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17條。現實依據是充分利用這支隊伍的力量,集中管理很多部門不愿管也很難管的與城市管理相關聯的事項,以解決推諉執法和執法難的問題。
首先,它應當有排它的管理對象。這是它作為一個獨立的管理門類而存在的前提條件。城市管理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可以裝,城市管理也不是“靠他人吃飯”,強行將其他管理門類的部分職能據為已有,硬生生地弄出一個獨立的管理門類來,城市管理有其特定對象,即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空間,包括城市地面、地下及地上設施和城市公共空間,主要有城市道路、城市水域、城市綠化、城市建筑物及設施、城市公共空間等,城市管理的對象是物,而非行為,當然,在管理物時,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人及其行為。
其次,它有其獨特的職責范圍。城市管理的主要職責就是保護其特定對象形態的完好及特定對象功能的正常,通俗地講,城市管理的職能就是保持已經規劃、建設好的城市基礎設施的外形及其功能。廣義上的城市建設應當包括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三個重要的環節,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以及城市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管理被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以適應城市發展突飛猛進這一客觀現實的需要。由此可見,城市管理是一種事后的、被動的管理,其實質就是“城市看守”、“城市守護”。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城市管理是完全被動的,城市管理應當參與到城市規劃之中,在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中加入有利于城市管理的因素。
再者,它有其特有屬性。城市學認為城市具有流動性和差異性,城市因為有流動性,而有生機,而有城市氛圍,城市因為有差異性而有自由性和創造性。城市管理應當具有包容性,尊重其流動性與差異性,因而城市管理的本質屬性就是以保護城市基礎設施為目的,合理配置空間資源,兼顧城市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城市道路、公共空地、公共空間是可以有限的、合理的利用的資源,城市管理就是充分利用這一資源,一方面緩解城市流動性給城市管理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服務民生,烘托城市氛圍。從中國現行法律法規來看,城市管理就是以維護城市基礎設施外部形態不被破壞和污染為主要內容的市容環境衛生管理、以維護市政設施和園林綠化功能完好為主要內容的市政管理和園林綠化管理,以及以合理利用公共空間為主要內容的戶外廣告設置管理等。
二、城市管理執法的創新探索
城市管理執法就是城市管理,因為城市管理活動就是一種行政執法活動。經過十多年的實踐,城市管理執法模式的弊端日益顯現:行政許可與行政處罰分離后,協調難度增大,管理難度增加;不相關聯或關聯性不強的行政處罰權集中后,并未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一些涉及專業性較強、行業特征明顯的行政處罰權被集中后,因“隔行如隔山”使之難以實現;伴隨著行政處罰權的集中,相關知識也集中,矛盾也集中,執法者難以承受。因此,該執法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機構設置形式急需創新。
第一,解決城市管理部門與城市管理執法部門是否分設的問題。目前,全國分設與并設這二個機構的城市,幾乎是平分秋色。筆者認為城市管理部門與城市管理執法部門并設較為科學,理由是:一則二者并設,使城市管理的行政權統一,有利于突出城市管理執法的中心任務,提升其履職能力,提高管理效率。二則可以減少行政機構和人員,降低行政成本。三則可以增強合力,更好地發揮城市管理協調能力,產生1+1>2的效果。例如湖北省宜昌市城市管理局與宜昌市城市管理執法局并設,采取“二塊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使管理與執法相結合,目前運行狀態良好,成為湖北省推行的一種典型的機構設置模式。
第二,解決設區的市和不設區的市城管機構層級問題。按照減少執法層次的要求,一個城市可以只有一個執法層級,設區的市市級城管部門(執法部門)不直接從事執法工作,其主要職責是組織、指導、協調和監督,區級城管執法部門承擔城管執法任務。在業務上市對區實行垂直領導,區級城管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任免要報上級城管部門批準,區和不設區的市、縣城管執法部門行使執法權并向各街辦、鄉、鎮派出執法機構。例如宜昌市城區就是實行市區二級機構分設,各司其職,并行不悖的機構設置形式。而宜昌市的當陽、枝江等不設區的市就是采取的一級執法形式,這二種形式分別與其城市規模和管理層級相對應,其實施效果正處于最佳狀態。
第三,解決執法隊伍與執法機關之間的關系問題。目前,全國幾乎所有城市,囿于機構編制的要求,均將城管(執法)機關與城管執法隊伍分設,這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17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應當由行政機關具備資格的行政執法人員實施,其他人不得實施。而城管執法需要依法采取大量的行政強制措施,因此,不設區的市和縣設立的城管執法隊伍必須是城管執法機關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一支執法隊伍。目前宜昌市正在研究和探討之中。
第四,解決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范圍的問題。推行相行集中行政處罰權執法形式應當遵循以下幾項原則:其一,所集中的行政處罰權應當以屬于一個大行政管理的系統為基礎,然后作適當的拓展,除了某些特殊的區域,比如開發區、自貿區以外,不宜跨太多的系統和太多的部門。其二,所集中的行政處罰權所指向的行為應當相近或者有較強的關聯性,并且圍繞著一個管理中心而展開。其三,集中行政處罰權時,要排除跨部門的技術性較強和管理權不易分割的事項。
因此,城管執法的范圍除其固有的城管方面的執法權外可集中行使住建系統和國土資源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和相應行政強制權。因為它們沒有脫離“維護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空間”這個中心,原已加于其身的有關環保、工商、公安、交通方面的職權,因為違背上述三個方面的原則應“物歸原主”。
三、完善“城管執法體制”的建議
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根據不同層級政府的事權和職能,按照減少層次,整合隊伍,提高效率的原則,合理配置執法力量”、“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加強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機構建設,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這是指導城管執法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是理順城管執法體制的指導思想。因為城管執法是自下而上產生的,全國各地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城管執法體制不可避免地帶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種狀況亟待自上而下的予以解決,依據上述精神,要理順城管執法體制。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城管執法領域必須從中央到地方設立統一的管理部門。城管執法雖然是城市人民政府的事務,但由于其管理隊伍龐大,管理事項涉及民生,管理范圍尤為廣泛,管理內容極其復雜,國家層面應當有一個主管部門統一指導全國的城管執法工作,省級政府設立與之對應的管理機構,因其它各級地方政府具體組織實施城市管理工作,因此各級地方政府主要是城市人民政府如何設立這一機構應與之有別,它首先必須具備執法主體資格。
2、應當賦予城管執法部門最大限度的協調權。因為城市基礎設施和空間的管理涉及到城市范圍內的每個組織和每個自然人,只有全民參與,全社會參與,各職能部門聯動,才能真正管理好城市,才能創造出美好的城市環境,城管部門只有具備了強有力的協調權,才能調動各方力量形成共管共建的良好局面。其中,就各部門間的橫向協作而言,建立城管與公安之間的緊密聯系是至關重要的。由于整個社會處于改革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城管執法屬典型的街頭執法,處于執法最前沿,矛盾聚焦點,如果沒有適當的強制力作保障,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量的執法實踐表明,只有公安機關向城管部門設立派出機構,才能確保城管執法正常運行。
3、構建大城管格局。通過創新組織體系、建立督查體系、市場作業體系、城市治理體系,建立健全“屬地管理、條塊互動、部門協作、群眾參與”的“大城管”新格局。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穩步把違建查處、市容執法、“門前三包”、污水外溢處置、群眾動員等工作下放至街道或社區,強化城市網格化管理。建立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城管委督查室聯合辦案機制,形成“大督查”格局;強化追責機制,形成各級紀委監察部門齊抓共管的責任追究機制。完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試行“職責外部歸并、權力內部集中”的綜合執法新模式。積極培育市場主體,建立健全市場主體準入招投標制度;全面推進生活垃圾中轉、處置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工作。研究道路維護市場化操作方式,加快市政設施維護轉型步伐。組建市容環境監督員隊伍,創建省級市容環境美好示范社區,在媒體上開辟“不文明行為”曝光臺,推動城市由“管”向“治”轉變。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