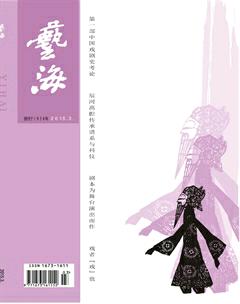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五)
鄭懷興
創作手法(上)
我寫戲,通常都是憑興趣、憑沖動匆匆而就,從來沒有想過我該在這兒用什么手法,要在那兒用什么機巧。現在所要談的這些所謂創作手法,都是為了講課方便,不得不回顧自己的劇作,或分析別人的作品,從中梳理出來的。
一、臉譜化與個性化
傳統戲曲里的人物,通常都是臉譜化的,觀眾一看就清楚哪個是忠臣,
哪個是奸臣,哪個是壞人,哪個是好人。可是《新亭淚》一上演,許多觀眾跑來問我,你的戲怎么把我們弄糊涂了,辨別不出晉元帝是明主或是昏君?王敦是奸臣還是忠臣?你的是非標準在哪里?
我看的傳統劇目不多,所見到的戲中皇帝似乎只有兩種,不是明主,就是昏君。對于開國君王的評價,似乎也都是以其是否殺戳功臣作為好歹的標準。若按這種習慣的衡量法,晉元帝應該屬于昏君之列。但是根據史書所述,他并不昏庸,他也想當一個中興明君,有番作為。站在司馬睿的立場上,疏遠王導,重用劉隗,不過是為了鞏固政權,若是由此而定他為排斥忠良、寵任奸佞的昏君,未免冤屈了人家。我對這個皇帝還是抱有一點同情的。他本想白展雄圖,誰知適得其反,引起王敦兵變,政局更加動蕩,寶座搖搖欲墜,一片雄心,付諸流水。權力至高無上的皇帝,也落了個事與愿違、一籌莫展的下場,豈不可憐?更為可悲的是,“圣明天子”卻永遠無法明白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他的悲劇。對這個皇帝予以一點同情,可以把專制主義鞭撻得更無情些。因此,我不給晉元帝畫上明主或昏君的臉譜,而是從人性出發,讓他以本來的面目出現在舞臺上。
關于那個以清君側為名起兵脅主、造成社會動亂的王敦,我也不作簡單化的處理。據《世說新語》所載,王敦好誦曹孟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詩。因此,《新亭淚》第八場一開始,我就給王敦安排一個橫槊賦詩的場面。王敦白比曹公,不僅是逞顯英雄氣概,而且也微露他對司馬氏政權存有覬覦之心——曹氏天下為司馬氏所篡,吾當為曹公雪恨!因此,我為王敦添此一筆,不但可以刻畫其個性,而且又可以直誅其心:豪情壯志,非為外御,只在內爭;貌似一代英雄,實懷狼子野心。欲貶而褒,似褒實貶,用曲筆刻面人物之復雜性格。
對于周伯仁這個我要正面歌頌的人物,也不是一出場就正氣凜然,豪情滿懷。我花了不少筆墨,寫他嗜酒,這也是史書所載。沉溺醉鄉,玩世不恭,是魏晉時期士大夫的一種風尚。但是周伯仁的終日酩酊,又有別于劉伶。他曾飲宴新亭,常有“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異色”之嘆,可見他醉中飽含憂憤。他縱觀時局,既反對王敦發動內亂,也反對元帝誅殺王導,可見他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因此,我把他寫成一個似醉猶醒、外醉內醒的士大夫。渲染其醉,反襯其醒。不過,周伯仁之清醒,是與那些不顧民族存亡、只知爭權奪利的東晉君臣比較而言的。旁觀者清,事隔一千六百多年,我們俯覽東晉小王朝,覺得周伯仁還是一個醉者。因為他認為天下動亂的根源在于同室操戈,而不知道也決不可能知道君臣之間互相猜忌、權臣之間互相傾軋的根源在于專制主義。因此,縱然有他挺身而出顧全大局,但也只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天下還是動亂不已。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也是他最大的歷史局限性。
關于王導其人。王導是東晉王朝的棟梁,江東士族唯他馬首是瞻。但是,威高震主,晉元帝對他有戒備之心,故重用劉隗以抑制王氏。他的堂兄王敦又借此之機發動兵變。因此王導處境變得復雜微妙起來。他對王敦之反,態度似乎有些曖昧,既想借王敦之力消除異已,重操政柄,又怕與王敦牽連而有損名節。由于他誤會周伯仁,才默許王敦殺死周伯仁。但可貴的是,作為權傾朝野、名揚天下的王導一旦真相大白后,卻悔恨不已,痛心疾首地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負伯仁!”古今政治家錯殺、屈殺不知多少無辜,但幾個能有王導這樣的襟懷,肯向冤魂謝罪?
《新亭淚》之后的劇本創作,我大體上都是走這一條路子的,人物刻畫少些臉譜化,多些個性化。即使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如《葉李娘》中的賈似道,我也不簡單地丑化他。他聽到葉李上書彈劾自己,雖然憤怒,但不立即下令逮捕,而是請葉李赴宴,想籠絡拉攏軟化葉李,軟硬兼施,逼其就范,為己所用;在刑場之上他還假惺惺表示,只要葉李肯下跪認錯求饒,就免葉李娘一死。這樣寫,并不是美化賈似道,而是讓這個奸臣形象顯得更陰險狡詐,也使劇情更跌宕起伏,引人人勝。
個性化并不等于人物性格復雜化。人物性格也并非刻劃得越復雜其形象就越生動。莫里哀的喜劇作品的人物,幾乎性格都是單一的,但無不栩栩如生。文學創作上有扁形人物與圓形人物之說,把性格單一的人物稱為扁形人物,把性格復雜的人物稱為圓形人物。傳統戲曲里的人物,大量是扁形人物,但許多都是不朽的藝術形象,不能說圓形人物的藝術價值一定高于扁形人物。我的戲曲作品中,既有性格復雜如《晉宮寒月》中的驪姬、《青蛙記》中的魏斯仁,也有性格單純如《鴨子丑小傳》中的阿丑、《阿桂相親記》中的阿桂、《蓬山雪》中的王珠、《葉李娘》中的葉李娘。阿丑樂天知命,淳樸可愛,觀眾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性格一點都不復雜,舞臺形象十分鮮明,完全屬于“扁形人物”。但觀眾喜愛他。評論家仍然可以從他身上挖掘出一些意蘊來。
現實生活中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性格有的復雜,有的單純。我們寫戲,也應該源于生活,該復雜的就復雜,該單純的就單純。如《新亭淚》中的晉元帝、周顗、王導、王敦,《晉宮寒月》中的驪姬、獻公、申生,《要離與慶忌》中的要離、慶忌、伍員,《紅豆祭》里的柳如是與錢謙益,《軒亭血》里的李鐘岳與秋瑾,《上官婉兒》中的婉兒與武則天,《乾佑山天書》里的寇準,《傅山進京》中的傅山與康熙,《青藤狂士》中的徐渭與張元忭,《海瑞》里的海瑞與胡宗憲,就是沒有史料根據的古裝戲如《造橋記》中的喬少爺與老管家,《寄印傳奇》中的侯縣令與冷老板,我都是予以設身處地推想,就構思出來,并不刻意將之個性復雜化或簡單化。樂天知命、樂于助人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比較少,出于我立意的需要,我把這種人加以藝術夸張,就塑造出鴨子丑形象。多年的藝術實踐告訴我,不管是網形人物或是扁形人物,只要塑造得好,就會富有個性,不會雷同化、臉譜化。
二、渲染與鋪墊
渲染,我指的是氛圍的營造;鋪墊,我指的是情節的設置。這兩種手法有時單獨運用,有時合起來運用,以制造出一種特定的情境,讓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在這兒變得可能發生,使觀眾本來不會相信的事情到這個時候卻完全相信了。如臺灣電影《稻草人》(1987年,王童導演),一方面花了大量的篇幅來渲染日本占領時期臺灣農村的貧困和愚昧,一方面通過小學生撿彈片獻給學校,受到老師的獎勵,以及美軍投到紅薯地中的那顆炸彈怎么擺弄都不會爆炸等一系列情節的鋪墊,最終才引出兄弟倆抬著那顆炸彈,長途跋涉到鎮上去領賞的荒誕情節。這個情節,本來是非常荒誕,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在這部電影中,通過充分的渲染和鋪墊,觀眾被引進了那特定的電影情境中,雖然覺得這兩兄弟的舉動無知可笑,又一直為他們提心吊膽,但對這個情節的出現,并不覺得突兀,認為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藝術氛圍的營造,跟寺廟里那種宗教氛圍的營造,十分相似。深山古剎,容易使人們產生宗教的虔誠,一踏入深山老林,山嵐、清泉、鳥語、花香,已讓我們覺得脫離了喧囂的塵世,再仰望那些高大莊嚴、金碧輝煌的菩薩,讓縷縷香煙繚繞身畔,陣陣鐘磬輕叩心扉,更覺得自己恍惚進入了西天佛國,心情一下子變得肅穆,即使平時并不信佛,此刻也禁不住要跟信男信女一道焚香禮拜……
《青蛙記》、《神馬賦》這兩個戲,我都是花了不少筆墨來渲染、營造那種如夢如幻的神秘氛圍,然后引出那貌似荒誕不經的故事來。在《青蛙記》里,我通過對荷塘月色蛙聲來營造氛圍,尤其是對蛙聲的渲染,幾乎達到極致。從第一場的一聲蛙鳴引起蛙聲大作,到最后一場幕后歌聲:“且聽青蛙論是非……”場場都有蛙聲,使劇中人物擺脫不掉,躲避不了。蛙聲那么神秘、詭譎、強烈,不斷叩擊劇中人物的心弦,在向他們追問秦景仙的死因,在審問秦景仙的死是不是你造成的?蛙聲引起了恐懼、悔恨、猜疑、迷亂,以致產生幻覺,終于釀成一場家庭悲劇。在《神馬賦》中,我通過對古樹、圍墻、木魚聲、神情呆滯的仆人的渲染,營造朱家莊封閉、保守、寂靜、僵死的氛圍。然后又著力渲染銅馬生前戰功赫赫,死后的塑像又會顯靈,挾帶風雨,擾得山莊古樹倒、圍墻塌,一片恐慌。對銅馬這樣渲染之后,才使李芳娘產生強烈的好奇心,到后園去仰望銅馬的英姿,才會引出她夢中與馬神炊會的奇異的一幕。
《寄印傳奇》中侯縣令寄印于當鋪的情節也是近乎荒唐。自古到今,哪有一個當官的把印信寄存到當鋪里或民宅中?令人不可思議。我通過渲染子虛縣匪盜猖獗,侯縣令勇于闖虎穴、擒拿盜魁,得罪盜匪,縣衙多年失修,破爛不堪,然后又通過一系列情節鋪墊冷老板對侯縣令的懷疑到信任、感激到敬重再到萌發愛情。再聰明能十的女人,一旦愛上了一個男人,就會讓感情淹沒了理智,甘愿為他承擔任何風險。這樣,渲染與鋪墊足夠了,侯縣令寄印于當鋪的情節就順理成章,沒有人再追究。《造橋記》里康知縣知道喬少爺是光棍后,不敢追究,反而與他們主仆倆繼續假戲真做,也是靠一系列情節的渲染與鋪墊來實現的。《軒亭血》中的李鐘岳與秋瑾的關系,本來是監斬官與死岡的關系,是勢不兩立的關系,我也是通過這種手法使李鐘岳慢慢了解真相而同情秋瑾,深深愧疚而白責、痛恨顢頇腐朽的清廷,最后寧舍自己的官位與性命,決不肯與知府同流合污,決不肯誣陷被自己屈斬的秋瑾而懸梁白盡。
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要運用渲染的手法。如《新亭淚》中的周伯仁,我一開始就濃墨重彩地渲染他的醉態。酒,幾乎始終伴隨著周伯仁。上朝時,他醉意未消,烏紗戴歪了,是書童幫他扶正;玉帶快掉下了,是書童幫他系上;奏章找不到,是書童替他保管。在朝門外,他醉眼朦朧,嘲弄了王導丞相;在金殿上,他醉態可掬,諷諫了晉元帝。月夜,他讓書童挑著酒上新亭,放懷痛飲,醉里殺敵;在刑場上,他還要飲酒食蟹,書童撫尸慟哭,還要說:“黃泉漫漫無酒店,爺今夜三魂到誰家?”這樣,既把“藥、酒、談玄”的魏晉風度展現出來,又把周伯仁外醉內醒的個性充分刻畫出來。
如果說渲染是為了淋漓盡致地營造戲劇的情境和刻畫人物的性格,那么鋪墊則是給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行動提供足夠的條件和依據。例如《春草闖堂》中,春草為什么會到公堂上去聽胡知府審訊薛玫庭呢?因為第一場已經寫了薛玫庭在華山進香的路上救了李半月和春草。有了這個情節的鋪墊,春草關心薛玫庭的案情就顯得合情合理。《鴨子丑小傳》中,阿丑為什么會制造出包山狀元鐘振華投河自殺的假象呢?因為他發現流言蜚語逼得振華走投無路了,只能通過假死來澄清事實,化解矛盾。為什么觀眾能認可阿丑制造這個假象呢?因為通過前面情節的鋪墊,使觀眾覺得眾口爍金、謠言殺人,鐘振華已陷入流言蜚語的包圍中難以解脫,倘若一時想不開,極有尋短見的可能。阿丑念祭文的情節之所以可信,因為前面已對阿丑的詼諧、幽默的個性作了充分的渲染和鋪墊,所以他做出這種行動就不足為奇。
鋪墊,猶如鋪路筑渠一樣,路鋪到哪里,車就通到那里;渠筑到哪里,水就引到那里。戲總是一環扣一環,上一場為下一場作鋪墊,前面各場都是全劇最后高潮的鋪墊。渲染和鋪墊,總的來說是為了情節的產生和發展顯得有其內在的邏輯,合情合理。也有一些戲,并不如此渲染、鋪墊,而讓情節發生突變,以產生強烈的戲劇效果。但我從來還沒有這樣試過,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體會,就不敢談及。如果說我在《晉宮寒月》中也寫了驪姬幾次“突變”,但這些“突變”都基于驪姬復雜善變的個性,而她的個性和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個性,我都作了大量的渲染和鋪墊,她的每次變化,都有充分的心理依據,并不突兀。即使在第六場中她突然栽贓申生投毒,也是在她派優施暗贈青絲給申生遭到拒絕之后,處于羞愧絕望之際,又中了獻公的離間計,才激起她對申生的無比痛恨,要置之死地而后快。這個內心的復雜而微妙的變化,我相信觀眾可以感覺到,所以就不必再用道白或唱詞加以剖示。
三、懸念的制造
電影懸念大師希區柯克說過:“如果你要表現一群人圍著一張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聲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個十分呆板的炸后一驚的場面。另一方面,雖然你是表現這同一場面,但是在打牌開始之前,先表現桌子下面的定時炸彈,那么你就造成了懸念,并牽動觀眾的心。”希區柯克這個異常生動的例子,被人們奉為懸念的“最高范例”。
懸念,顧名思義是把觀眾的心提起來,也就是說,讓觀眾關注劇情發展和人物命運而心情緊張。制造懸念的手法多種多樣,因戲而異。我下面所談的是自己在幾個戲中如何制造懸念。
在《戲巫記》中,阿梅一上場,就說自己今天要去桃花村探訪年青漂亮的小寡婦阿秀。探訪的目的是什么呢?原來阿秀自稱仙姑附體,能夠通靈,名氣很大,阿梅要去一試真假,看她到底有什么法力。這樣,懸念就產生了,觀眾等著瞧阿梅要用什么辦法去測試阿秀,阿秀到底有沒有法力?等到兩人見面后,阿梅要請阿秀為他招亡妻之靈,又通過阿梅的旁白,讓觀眾知道阿梅從來就沒有娶過老婆,亡妻之說,純屬子虛烏有。觀眾興趣更濃了,阿秀會不會上阿梅的當?阿梅此行的目的能不能達到?而阿秀也讓觀眾明白,她的仙姑附體是假的,裝神弄鬼純粹是為了戲弄世人。那么兩人到底誰在戲弄誰?到頭來誰被誰戲弄了?這樣,懸念更強烈了。這個小戲可以說懸念不斷,情趣甚濃,所以能步步吸引觀眾看下去。
這個折子戲的懸念跟《鴨子丑小傳》中第五場《審妻》相似,都是來自沖突雙方所產生的濃厚的生活情趣。觀眾知道的信息比劇中人要多,就會饒有興趣地看劇中人是如何被設套,又是如何去解套。《魂斷鰲頭》制造懸念也是運用了這種手法。劇中的王長卿,完全不知道他能獨占鰲頭是他表妹——戀人用青春和生命交換得來的,所以他得志之后,能洋洋得意,指責表妹嫌貧愛富,而觀眾心里卻是明白的。所以當狀元越白鳴得意,觀眾越替他感到難受,他越嘲弄表妹,觀眾越盼望他趕快知道真相,但又擔心他弄明白了會受不了……這個時候,把狀元蒙在鼓里的時間拖得越長,懸念就越強烈。
在《新亭淚》的第七場中,王敦派他的部將錢鳳來征詢王導的意見,該如何處置周伯仁?周伯仁的處境非常危急。觀眾都已知道是周伯仁在危急關頭救了王導一家,也盼望王導能于危急關頭救下周伯仁。但這個時候的王導,卻顯得非常悠閑、從容、鎮靜。這樣情勢的動,與人物的靜,形成巨大的反差,這個反差產生了強烈的懸念,讓觀眾猜不透王導的下一步動作。
在《遺珠記》的第五場中,我設置了一個局,即剽竊者在剽竊別人的技術成果時,是被剽竊者為他把門站崗。而叫被剽竊者為剽竊者站崗的是誰呢?是一位一心想當發現人才的伯樂的廠長,而這位廠長,又是被剽竊者的姑父。設置這樣貌似荒謬的情節就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懸念。
《寄印傳奇》中侯縣令設下圈套,把官印寄存在冷記當鋪里。當他有一天晚上突然造訪當鋪,欲說還休,冷老板還以他是要來向自己求婚的。當他向冷老板謊稱官印被人偷蓋,正被有司追查時,觀眾知道這是侯縣令在耍花招,要詐騙冷老板的百萬家資。只有冷老板被愛情蒙住了雙眼,喪失了理智,信以為真。侯縣令又假惺惺地表示,寧愿自己丟官殺身,也不愿連累冷記當鋪。侯縣令越狡詐,冷月芳越動情,觀眾也越加提心吊膽,為冷月芳捏著一把汗。這樣強烈的戲劇懸念就產生了。
將觀眾蒙在鼓里,引發他們的重重疑問,也是一種懸念制造的手法。在《青蛙記》中,秦景仙究竟如何死去,二十年來一直是個謎。這個謎劇中人物急于想解開,觀眾也急于想了解謎底,但是越想解開,越顯得撲朔迷離。于是這個謎就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懸念。又如《蕭關道》這個劇本。李充醫師為什么不敢向阿塔說出他父親當年不治身亡的事情呢?因為他擔心阿塔向他討父親的遺物——鎏金銀壺。而前面我渲染了有司正在奉晉王之命在蕭關搜尋此壺,使得此壺身價猛漲,這樣讓李充更加不敢吐實,內心愧疚更加重了。這個懸念一直到最后,山大王說你若不交出鎏金銀壺,我就要把玉兒留在這兒做壓寨夫人。事關他唯一的愛女的生命安危,他才不得不交出阿提夫的遺書,向阿塔傾吐埋在心底二十年的隱衷,懸念才解開。真相大白了,李充的人物形象也完全展現出來。觀眾本來對他充滿了疑問,這個李充是不是貌似儒醫,實是陰險毒辣的小人?是不是他謀財害命,置番客于死地,而奪走鎏金銀壺?謎底揭開之后,觀眾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充太重信譽了,才遲遲不敢道出真相!
但真正好的懸念,不是編劇在情節設置時所刻意安排的疑問,而是對劇本中人物命運的密切注視和關懷。在《晉宮寒月》中,申生一班師回朝,就被晉獻公奪去兵權,晉獻公又命他到后宮去赴驪姬特意為他設下的酒宴。申生明知驪姬懷有奪嫡陰謀,遣他遠征霍國,又被斷絕后援,都是驪姬在背后搗的鬼。但忠厚孝順的申生又不敢違抗父王的命令,明知赴宴兇多吉少,還是不得不去。第二場一開始,驪姬又巧設機關,暗藏殺機。情勢非常危急,觀眾誰不為申生捏一把汗?能不關心他的命運?這個戲可以說是對立雙方的命運引起觀眾的極大關注而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懸念。
在《要離與慶忌》中,如果寫慶忌對要離暗中防備,使要離一直下不了手,一直在尋找機會,以謀刺殺成功。這樣雙方的對立,可以產生懸念,但比較落俗套。我將這個故事改成了隨著要離對慶忌了解越來越深,越不忍于下手;慶忌對吳國政治形勢的了解越來越深,卻越來越渴望要離來刺殺他。但他們兩人都在互相窺察對方的內心,互相等待……觀眾被他們復雜微妙的內心沖突所吸引,擔心他們的命運,既急切期待要離下手,又非常害怕要離行刺,這也是一種懸念。
在《乾佑山天書》中,一向反對天書的寇準為了東山再起、重整朝綱而不得不上表賀天書。這是出乎觀眾意料之外的。觀眾認為寇準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了,那么,他的愿望能實現嗎?寇準第三度拜相的目的達到了,但他以為重掌大權之后,就可以匡扶正氣、挽住頹勢的良好愿望還能不能實現?觀眾在急切地期盼、等待,這就產生了懸念。觀眾同情寇準,關心寇準的政治命運,希望他的復出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然而,客觀環境卻使寇準陷入了一個怪圈,他越努力,越難實現自己的愿望,越掙脫越不能自拔。這一困境的形成,又是因為他附和天書,被政敵抓住了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他陷入被動;也因為他附和了天書,地方官們紛紛上行下效,致使造假之風更盛,使他無力匡正……于是觀眾一次次地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希望、失望不斷交替,形成緊張、焦慮的心情,不知寇準將如何走出這個怪圈。觀眾的希望和寇準所處的客觀政治環境早已預定下來的必然失敗的結局之間形成了張力,這種張力產生了懸念。
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是如何根據劇情的需要制造懸念的。前人與別的編劇都有許許多多更好的經驗,可以通過看劇本看戲去領悟、去總結,我就不贅述。
四、沖突的運作
大家都知道,沖突是構成情節的基礎,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沒有沖突就構不成戲劇。也有的人認為,戲曲并不那么重視沖突,只要重視情境就行了。我讀過幾個名家的戲曲文學本,詩情畫意甚濃,詞句雍容典雅,但是很難卒讀,想像不出將如何搬上舞臺,如何吸引觀眾。或許,他們故意不要沖突,只重情境。但我理解的戲曲情境,如《休丁香》那樣,貌似沒有沖突,其實丁香的主觀生活領域與客觀生活領域已構成了沖突,已經知道丁香越盡心繡羅衣后果越不堪設想的觀眾與丁香的行為也構成了沖突。如《虎牢關》中張飛臨戰前夕磨矛洗馬那出折子戲,好象沒有什么沖突,戲卻吸引人。我以為,這里面也隱含著一種沖突。因為一般觀眾只知道張飛是個莽漢,想不到他的心思也會這么細,跟矛說話,與馬談心,更是新奇。這樣,舊的印象跟新的發現形成了反差,構成了沖突,產生了懸念,戲自然就好看。
又如《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十八相送”,梁山伯的傻乎乎跟觀眾急欲讓他知道祝英臺的種種比喻的含義的愿望之間也構成了沖突,這種沖突隨著相送的路程越來越遠、分手的時間越來越近而越來越強。戲曲情境來自設局,設局就是以沖突作基礎,局設得巧妙,其情境貌似平淡清靜,實則暗流洶涌澎湃,內在的漩渦把觀眾的心都挾卷進去。
剛學習寫戲的時候,我把沖突理解為對立的人物在舞臺上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斗爭越激烈,戲劇沖突就越強烈。學戲一久,才知道此乃膚淺之見。舞臺上的兩軍交戰,雙方開打,那只是讓觀眾欣賞演技而已,算不上戲劇沖突。在戲曲中,看一臺戲或一出戲的沖突強烈不強烈,可以拿懸念來衡量。懸念是戲劇沖突的標志,產生不了懸念的戲,就是沒有沖突。現在我結合自己的幾個戲,來淡沖突的幾種類型。
人物內心沖突。通常的寫法,是通過人物的道白、唱詞,或是幕后的伴唱,來刻畫人物的內心。在電影中,還可以運用字幕。比如伍迪·艾倫的名片《安妮·霍爾》(1977年)有一個情節片段,兩位初識的青年男女為了給對方留下美好的印象,都急于表現白己,結果言不由衷地聊起藝術、哲學。而他們真實的想法卻是考慮如何進一步交往。導演通過字幕的方式直接呈現兩人的心口不一,這種對人物內心矛盾沖突的表現方式,就營造了一種幽默效果。在戲曲中,其實也是可以靈活運用一些技巧的。《新亭淚》中的第四場,是寫周伯仁面對動蕩不安的時局,內心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是要急流勇退,獨善其身,還是要挺身而出,力挽狂瀾?這是古代中國士大夫常常面臨的一個人生課題。如果這種內心沖突只讓周伯仁用唱詞或道白來表達,我應該如何,不應該如何,就顯得單調無味。我在這場戲里加了一個神秘的漁父,讓他出來跟周伯仁對答,就把周伯仁的內心沖突外化了。有些人對我這種寫法不理解,提出批評,認為漁父來無蹤去無影,不合情理。1990年底,我看了鯉聲劇團排演的《目連戲》,發現在劉四真在要不要開葷這個問題猶豫不決,內心矛盾沖突非常激烈的時候,她的左右突然出現了兩個神將,一個是素神,一個是葷神,兩人在對打,最后素神被打敗了,倉皇逃下,劉四真就決定開葷。古人早就懂得運用內心沖突外化的手法,可惜我們把這個傳統丟掉了,戲曲的表現力衰退了。
我在寫《青藤狂士》時,就借鑒素神與葷神的寫法,在徐渭身邊設置了兩個豎子,以表現他的激烈的內心沖突與精神錯亂。
對立雙方的正面沖突。正面沖突的戲很難寫,弄不好會變成雙方在據理力爭,只有理充耳,沒有趣娛目。因此,在寫正面沖突時,得花些心思,用些機巧。《鴨子丑小傳》的第五場《審妻》,阿丑要追問阿花有沒有收起金桃。如果單刀直入,曉之以理,則會成為一出說教的戲,索然無味。我寫阿丑緊緊抓住阿花愛打扮的心理,通過勸酒、贊美、照鏡、試裝而步步深入,慢慢誘之,最后水到渠成,教阿花情不白禁地出示金桃。審妻實為騙妻也。然而阿丑騙妻,是寄狡黠于厚意,不用花言巧語,而動真情實感,他贊美阿花勤勞漂亮,后悔自己體貼不夠,都是出于肺腑之言。唯有相敬如賓的真摯之情,才使阿花深受感動,毫無忌諱地向丈夫披露隱秘。審妻,是夸妻貶已,卻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樣寓機于情,使機趣情趣渾然一體,戲才有味,才不會“硬”。
《乾佑山天書》中的第三場,寫寇準與丁謂在玉清昭應宮的面對面斗爭。根據寇準的剛直的個性,我一開始就讓寇準主動出擊,義正詞嚴,窮追猛打,有非取丁謂頭顱不可之勢。丁謂處于被動地位,然而他并不驚慌,并不極力為自己爭辯,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問寇準“你這回上的賀乾佑山天書表中,不也是說上天賜福,祥瑞頻呈,一片升平景象嗎?”一句話,問得寇準目瞪口呆,使形勢急轉直下,寇準處于劣勢,丁謂反占上JxL。陰險的丁謂這時卻顯得寬宏大量,豪爽的寇準倒顯得心胸狹窄。這樣寫正面沖突,既符合人物個性,又起伏跌宕,頗能引人人勝。
《葉李娘》中的第二場,葉李往半閑堂赴宴。賈似道之流想通過威脅引誘,逼使葉李屈膝,與他們同流合污。葉李卻是書生意氣,決不低頭。如果寫雙方你一言我一句反復較量,也許很熱鬧,演出來卻可能沉悶。我沒有這樣寫,而是以“把酒行令”的方式,展開這場針鋒相對的沖突。雙方各借酒令,諷喻針砭,斗智斗狠,機趣橫生。葉李反對賈似道的公田法,也不是大發議論,而是借用了無名氏的詩句:“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刺到了賈似道的痛處。
在《王昭君》這個戲里,漢元帝知道王昭君貌美,卻因受毛延壽的蒙騙,以為她長了一顆白虎痣,而不敢召幸。王昭君知道自己的美貌曾被皇帝所賞識,但不知毛延壽在她的畫圖上加了一顆痣,所以埋怨皇上為何不召幸她。如果分別寫這兩人的心理活動,則沒有對比,戲不好看。我以琵琶洞簫為媒介,讓他們同時出現在兩個表演空間里,各自唱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這個場面就與觀眾之間產生了沖突——觀眾越看會對造成隔離漢元帝和王昭君的毛延壽越痛恨,對王昭君越同情,也越替漢元帝感到遺憾。
《傅山進京》中傅山與康熙論字于雪天古剎,也是一種沖突。歷史上康熙喜歡書法,師法董其呂與趙孟頫,所書“福”字,天下視為至寶,而傅山又是當時的書法大家,曾被黃道周稱為“晉唐以下第一家”。作為書法愛好者的康熙,聽到傅山投宿京郊古剎,惺惺相惜,有可能盼望與之相會,當面請教。于是,我就設置了他雪天微服,私訪古剎,與傅山品茗論書法的一場戲來。在這場戲里,傅山一見不速之客所書的“福”字和不凡的談吐舉止,就猜出面對的是清廷少年天子——康熙。兩人心照不宣,以賓主之禮相待,一起切磋書法,評點人物。表面彬彬有禮,實則立場迥異,時而談笑風生,時而唇槍舌劍,明在論字,暗在對弈。康熙借機示懷柔,傅山論字表氣節;情境雖為虛構,而他們的觀點,卻是字字有根據,句句有來歷。傅山與康熙觀點不同,因厭惡董、趙的人品而嫌他們的作品帶奴貌、含俗態,不是書法正脈,他主張寫字應當“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如老實漢走路,步步踏實,不左右顧,不跳躍趨。”這些我都是照搬他的原話,并無半點修飾。這樣寓沖突于論字,無刀光劍影,有詩情畫意。論者都稱譽我構思巧妙,孰知此與《新亭淚》中周伯仁遇漁翁于新亭一樣,也非我刻意為之,苦思冥想得來的,而是得之于偶然,可謂鬼神啟我,非我筆力之所能逮!
五、伏線與蓄勢
伏線,也稱伏筆,它與鋪墊不同,鋪墊是情節的安排,伏線是為了密針線,通常是通過一個細節,或者幾句話,或者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預先作了埋伏、交代,乍看起來,是漫不經心,等到與后面的情節相呼應時,你才感到其作用很大,缺之不可。《團網之后》的第一場中,葉慶丁說的那句:“舍妹入門遇喜,八月便生甥兒。”乍聽起來,沒有什么,猶如萬里晴空飄來一縷云絲,誰知道這微不足道的云絲引來了驚雷閃電、狂風暴雨。作者就是用這句話預埋下了一條導火線,導出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悲劇。
在《晉宮寒月》中,驪姬讓優施往她頭發上抹蜂蜜,這個細節是伏線,觀眾與優施一樣都不知道驪姬為什么會有這樣奇怪的行為。等到后來蜜蜂飛到驪姬頭上,申生急忙為驪姬驅趕蜜蜂,而令躲在一邊窺視的晉獻公勃然大怒時,大家才明白這個伏線的作用。
在《王昭君》中,宮女拜托王昭君到了邊關,替她尋找一下戍邊多年的父親張老三,乍看起來,與劇情并無什么關聯,似是贅筆。可是等到王昭君到了邊關,上了烽火臺,向老戍卒打聽張老三時,觀眾才明白我預伏張老三這個人物的用意何在。王昭君在烽火臺上的思想升華就是由跪祭張老三所引發出來的。
《海瑞》中,我設置了一對小人物——衛立秋與他的老婆吳春花。這對小人物,除了在第一場在胡公子大鬧驛站里必須出現外,我又安排他們擔心得罪了胡宗憲而遭到報復,就連夜逃跑,設計衛立秋到了京城在刑部監獄里當了獄吏,胡宗憲入獄后就在他看守的牢房里,這又為海瑞悄悄探獄預設了一個伏線。沒有熟人衛立秋當獄吏,海瑞怎能私訪監獄?
蓄勢,則猶如射箭一樣,要把箭往前射出,先要把弦往后拉,弓與弦之間的張力越大,箭才飛得越快,射得越遠,穿透力也才越強大。箭要往前射,弦要往后拉,這就造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反差,就造成了“勢”。在《新亭淚》中,我極力渲染周伯仁的醉,目的就是蓄勢,大書醉以反襯他的醒。在《鴨子丑小傳》中,極力夸張阿丑怕老婆,夸張阿花管老公,也是一種蓄勢,能反襯了阿丑審妻時的機智。
我的老家仙游有個著名旅游景點九鯉湖,以瀑布雄偉壯觀聞名于世。但是瀑布的源頭,卻是一條蜿蜒在平野上的小溪,水流十分平靜。待流到第一漈時,如徐霞客所寫的:“……平流至此,忽下墜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漈之奇也。”他這里所說的雷霆之勢,是平流至此,忽下墜而造成的。他寫到第二漈是:“……水初出湖,為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沖激,水石各極雄觀。”這個勢是水為石所扼不得出而造成的。戲曲中的蓄勢,與徐霞客所說形成九鯉湖瀑布這兩種勢,極其相似,一是劇情先平緩安靜后突然急轉直下,二要在劇情發展中設置障礙,障礙越巨,所蓄積的勢能也就越大。第一種手法如《新亭淚》中的第七場,戲一開始我寫王導丞相閉門謝客,在后園除雜草,剪枯枝,整花畦,家事不問,政事不聞。百官前來請安,他都不予理睬;王敦派錢鳳來征詢如何處置周伯仁,他唯“哦”了一聲;晉元帝請他設法令王敦撤兵,他只勸皇上寬懷,不要操之過急;周伯仁的女兒前來向他求救,他也無動于衷……王導的平靜到此已推到了極限,勢已蓄足了,一待到他讀到周伯仁的奏章,劇情急轉直下,鎮靜白若的王導頓時急得木屐脫落而跌倒,他連呼兩句:“老夫負伯仁,老夫負伯仁!”這臺詞才能如雷霆乍起,撼人魂魄。
第二種手法如《晉宮寒月》中的第六場。驪姬一廂情愿,愛上了申生,托優施暗贈青絲于申生,誰知遭到拒絕,她羞憤難忍,陷入極度痛苦、絕望之中,這時晉獻公又來挑撥說,申生向他告密,逼驪姬向他吐實情。驪姬覺得白己的一腔癡情一再遭到申生的褻瀆,忍無可忍,便狂怒起來,把積在胸中的痛苦、憤恨、陰毒頃刻間都發泄出來,像瀑布一樣傾泄到申生的頭上——誣告申生投毒!在《王昭君》中,王昭君一出場,就非常自信,認為自己天生麗質,用不著賄賂畫工;果然毛延壽給她畫的畫像,是宮女中最美的,王昭君更是勝券在握,認為自己必定會被皇帝選上的。小黃門來報喜訊,說皇帝一看昭君的畫像,驚喜萬分,又把昭君喜悅的心情推向了高潮。等到老黃門來宣旨時,所有的宮女都認為,必定是昭君要被召幸了!誰知,被召幸的不是王昭君,而是李玉瑩。如果把王昭君的情感比作一條溪流的話,以前一直是平直而歡快地向前流淌,此刻突遭巨石遏阻,立即墜入深谷,能不飛噴沖激,化成瀑布?
在沖突與蓄勢中,我多次提到反襯的手法,以周伯仁的醉反襯其醒,以阿丑的外憨反襯其內秀,這都是從人物個性不同的側面來進行反襯。人物之間也可以運用反襯手法。如寫陰險毒辣的夷吾以反襯申生的忠厚誠實,寫喜歡嫉妒、散布流言蜚語的群眾以襯托心地善良、樂于為人排憂的阿丑,寫元士會的動搖與絕望以反襯王珠對愛情的堅貞。反襯對比可以造成反差,而產生強烈的戲劇效果。
在寫《青藤狂士》時,我讓徐渭一出場,就為吊唁慘遭權奸嚴嵩殺害的好友沈煉而撰雜劇《狂鼓吏》,借古諷今,以抒孤憤。緊接著,就讓他面臨著一種艱難的選擇:要為浙江總督胡宗憲撰寫《賀嚴公生辰啟》。這樣反差太大了,簡直是從九霄云外落進萬丈深淵。怎么辦呢?胡總督這樣奉承嚴嵩,為的是能得到他撥下軍餉,倭患未平,東南未靖,沒有軍餉,一籌莫展呀!可是,自己怎么能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為不共戴天的仇人歌功頌德祝賀辰呢?不寫,對不起最器重自己的胡大人還是小事,關鍵的是倭寇未滅,東南百姓的倒懸未解……開場時寫徐渭罵嚴嵩越狠,他后來的抉擇越艱難,這樣的前后巨大落差所積蓄的勢能也就非常巨大,人物的內心沖突必然非常激烈。徐渭的發瘋也就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