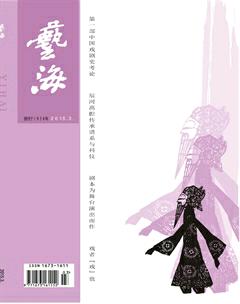黑暗中的一絲燭光
李沛霖
[摘要]20世紀上半葉是一群意氣風發的熱血青年追求浪漫理想、放聲吶喊的激越時代。而作家蕭紅卻在難以想象的孤立環境和冷漠情感中成長,在冷漠的親情和曲折的愛情中歷經創傷性體驗,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下具有作家的本位理性思考,對自由的向往讓她萌生漂泊情結和逆向性創作意識,女性主義意識和對故土的苦戀成為她一生的信念,蕭紅一生都在追逐和反抗,在悲劇性沖突中向往著自己的黃金時代。
[關鍵詞]平靜 安穩 自由 信念 創傷性體驗
蕭紅的一生短暫而不平凡,在有限的歲月中散發出金子的光芒。身處一群熱血青年揮擺鋤頭鋤金的激越時代,她卻有著自己眼中追求和向往的黃金時代。影片《黃金時代》被眾多觀影者理解為一個“夢想、愛情和自由”十分闊氣的年代,又或是“一群精氣十足的青年,一段放任自流的時代”、“一個充滿自由理想、海闊天空的時代”。但將目光放在以人生經歷為主線貫穿全片的女作家蕭紅身上,以她的視角思考,被蕭紅定義為“黃金時代”的時代究竟是什么樣子?
《黃金時代》的片名取白蕭紅于日本寫給蕭軍的信中。1936年11月19日,蕭紅在信中寫道“窗上灑滿著白月的當兒,我愿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于是我摸著桌布,回身摸著藤椅的邊沿,而后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這信與其說是在和蕭軍告知生活情況,更像是蕭紅自我的述說。可以清楚地看出,蕭紅對黃金時代的定義很簡單,自由而舒適、平靜而安閑、經濟不壓迫。她用過人的敏銳,在物質條件十分艱難,內心無比痛苦的時刻,體悟出這樣一個黃金時代,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洞見。但此時蕭紅仍有不甘,盡管是在日本如此靜謐的夜晚,精神上仍經受著如同‘籠子的桎梏,這桎梏如影隨形,歷經一生歲月在反復中不斷加重和變形。因而對于蕭紅來說這般簡單美好的時代,卻是追求了一生也難得,所以才稱之為“黃金”般的時代。
蕭紅眼中的黃金時代和后人眼中的黃金時代大不相同,后人看到的是一群人生活在廣闊天地中自由放任的生活,而蕭紅眼中殷盼的是個人生活環境的平靜和安穩,以及在此基礎對自由和信念的追求。蕭紅和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有很大不同,比較男性作家已是在性別上有了極大的先天條件的不平衡,對比同年齡的女性作家更是在后天成長環境方面差異過大。蕭紅經歷著太多人不曾經歷和難以想象的孤立環境和冷漠情感,但卻又在黑暗中看到一絲燭光,感受一股火焰,生而倔強的她開始追求平靜和安穩,堅持自由與信念。
一、平靜和安穩
張乃瑩生于呼蘭的鄉紳家庭,在正式開啟寫作生涯前她經歷了三大痛苦——喪母、逼婚、墮胎。但卻也得到得到過三份溫暖又青春的回憶——祖父口授《千家詩》的啟蒙教育、和表哥為愛私奔、北平女師大附中半年求學。直到1932年,困境中的蕭紅和蕭軍,開啟了文學創作一路,其后接近十年創作達到高峰。在這樣的困苦動蕩環境中蕭紅脆弱卻倔強,對“愛”與“溫暖”有著深切的憧憬和追求,極端渴望能在平靜和安穩的環境中自持自立,專心寫作。
每一種文學都根植于無意識中,這種無意識是在從小創傷的環境中衍生出來的認知和感觸,這是蕭紅文學作品的源泉。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引論》中提到的創傷性體驗,精神創傷是一種長久、深刻的痛苦,這種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的心理現象在蕭紅身上得以充分體現。
首先是冷漠親情中的最初溫暖和美好記憶。童年的經歷,早期家庭環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氣質和性格的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對蕭紅童年影響最大的四個人,父親、母親、繼母和祖父。蕭紅眼中的父親是無情的,幼年的她能感受到的近乎全是冰冷和摒棄。對于母親,依賴卻陌生,母親的早逝也沒能給蕭紅帶來應有的關愛。接下來便是受著繼母的不盡折磨,客氣中帶著冷淡,冷淡中含著疏遠。因而在直系親人的影響下,蕭紅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反復的冷酷折磨下形成長期性的創傷。但卻有一個人,蕭紅的祖父,帶給了小蕭紅最初的愛與溫暖,這是蕭紅日后仍保持對愛與溫暖追求和對平靜安穩生活向往的最初動力。“每每在大雪中的黃昏里,圍著暖爐,圍著祖父,聽著祖父瀆著詩篇時微紅的嘴唇”,可以說祖父是蕭紅在正面情感上的第一啟蒙老師,讓蕭紅“向著這‘溫暖與‘愛的方面,懷著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因而年幼的蕭紅是品嘗過愛和溫暖帶來的甜滋味的,這就為她在日后的生活中對愛和溫暖的極度渴望心理埋下了伏筆。
其次是坎坷愛情中的深刻悸動和心如止水。在親情上飽經創傷的蕭紅對愛情是有強烈欲望的。蕭紅一生中有四個男人,歷經四次不同程度的受挫。盡管愛情之路坎坷曲折使得蕭紅胸口丟滿沙石,但蕭紅熾熱的心還是感受到了強烈的悸動以及輾轉后對平靜安穩的尋求。陸振舜,第一次嘗試為愛情奮不顧身的蕭紅,與青梅竹馬的表哥逃婚北京。但正如魯迅所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在被斷絕經濟來源的情況下陸振舜屈服了,蕭紅只得帶著羞辱破碎的心回到呼蘭。汪恩甲,蕭紅被包辦婚嫻下的未婚夫。在蕭紅饑寒交迫時,兩人同居于旅館半年,她漂泊勞累的心暫得安定。不久后蕭紅懷孕,汪恩甲棄她而去,留下蕭紅欠債百元,食無求飽,居無所安。蕭軍,蕭紅真正的愛人,他用愛情把蕭紅人生中窮困、苦澀的日子編織成了“春暖花開”的模樣,相逢結合都變得格外傳奇。在遇見蕭軍之前,蕭紅可以說是帶著僅有的生存意識和強烈的生命意識在黑暗中穿行,這份愛情最終使得蕭紅的心千瘡百孔但也帶給過蕭紅真切的愛與溫暖,如用臉盆喝水、分吃一個窩窩頭、穿同一件大棉襖。但最終由于性格的悲劇,新時代女性自由解放意識與民族男性霸權潛意識的矛盾使得蕭紅與三郎永遠地分開。端木蕻良,蕭紅一生都渴望在愛情中尋找愛和溫暖,想個安身立命之所,直到最終選擇了端木蕻良。但此刻的蕭紅已經是“在胸中積滿了沙石”,因而端木蕻良帶給蕭紅的正是默默陪伴下的心如止水。從前的每一次愛情都讓蕭紅傷痕累累,已是不堪重負。蕭紅用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明確自己所需要和追求的,正常的老百姓式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打鬧、不忠、譏笑,有的只是黃金時代下的充滿諒解、愛護、體貼的生活。
再者是動亂社會下的作者本位思考。蕭紅認為“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段,作家是屬于人類的”。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許多知識分子都搖身為“戰士形象”或“投筆從軍”。但蕭紅卻對戰爭有獨特認識,她感同于民族的生死命運、經歷抗戰的水生火熱,卻傾向于留在戰線后方寫作。蕭紅曾對“不聽別人的勸告”的蕭軍說明“你知道我別無所求,我只想有個安靜的環境寫寫東西”,蕭紅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擔負的責任就安心寫作,反對“形式主義”和“抗戰口號”一類的東西,不論身處前線與否,都是可以跨越空間對抗戰進行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導。由此可見蕭紅認為平靜和安穩的環境是作家創作的必要條件之一。
二、自由和信念
“我不能選擇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選擇怎么愛、怎么活,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黃金時代”,蕭紅從小受教于呼蘭的一所設立女生部的小學,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婦女解放思潮的影響。直到從十九歲的離家出走,蕭紅開啟了屬于白己的真正人生。在《國際協報》眾多熱血青年的幫助下走出生活困境,獨立自主的邁向了社會活動的廣闊天地,精神方面也更加具有自由意識和獨立自主的女性意識。
蕭紅的女性意識在通過和同時代思想先進的優秀女知識份子白朗、丁玲、許廣平等接觸后得到快速發展。典型的女性意識使得蕭紅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始終抱有積極態度,意識到白己是獨立自主的社會個體,存著對生的向往,大膽追求愛情企圖得到幸福,也試圖通過個人努力取得各方面的獨立,在此基礎上去實現自我價值,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我只愿生活在此時此刻,無所謂去哪,無所謂見誰。那些我將要去的地方,都是我未謀面的故鄉。那些我將要見的人,都會成為我的朋友”,蕭紅是一個極具漂泊情結的人,因為她一生都在跋涉,從哈爾濱到北平、日本回上海、武漢到西安、重慶飛香港,從一個男人懷中到另一個男人身邊。漂泊中的蕭紅擁有一種“積極的靈魂的情緒”,她把漂泊路上對人生、愛與溫暖的理解全都訴諸于文字,如《呼蘭河傳》、《小城三月》、《馬伯樂》等。蕭紅不愿被束縛的天性使得她在對自由追求的路上富有浪漫感性的漂泊情結。
而最引人關注的,是在抗日救亡文學如火如荼之時,蕭紅始終用逆向性的主觀創作意識,區別于其他作家對于戰爭宏大場面的描寫,寂寞地轉身面向那座叫做呼蘭河的小城。茅盾在作《呼蘭河傳序》中,由首至尾提及二十七個“寂寞”來表現蕭紅創作時無處不在的寂寞。作家在寂寞心理下構筑出具有獨特東北氣息的精神文化空間,文字犀利有力,蠻荒卻又豪邁,凸顯出蕭紅卓越的批判諷刺才能,繼承老師魯迅,將中國人的愚昧揭露于紙上。漂泊于戰亂,輾轉于大江南北的蕭紅產生了一種逆向性創作之寂寞論。
回到電影,女性導演下的《黃金時代》體現了女性立場和女性意識,夢想與現實、期望和失落、堅強與無奈、掙扎和妥協,可以說是為更自由地表達蕭紅提供了多樣化的可能和途徑。現實中的蕭紅一生和一身不容忽視的一個閃光點即是具有女性主義的信念。蕭紅喜歡用女性的經驗來洞察歷史,追問女性生存的價值與意義。蕭紅從小到大的艱難抗爭都不斷澆灌著她女性主義的意識,如反對傳統包辦婚嫻對女性的壓迫而離家出走,為得到學習機會而大膽地付出身體,不愿為男人變成奴隸而離開最愛,這種種的“女性的抉擇”,都讓她“以生命為代價窮盡了歷史給女性留下的最后一份可能性”。
作為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和很多作家一樣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她是一名“憑天才和感覺在創作”的才女,而她敏感的文學細胞來自于生她養她的黑土地上的人和事。錫金說:“蕭紅一直在抒情,對鄉土的思念是那樣的深切,對生活的品味是那樣的細膩。情意悲涼,好似寫不盡的。”作家從創作開始到終結,思考并表達的故鄉土地上的生死人生,她對故鄉小城的印象十分深刻,“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而除了對從小生活地的自然而然的熟悉感指引她外,更是因為“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住著我的祖父”,還有蕭紅眼中“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什么都新鮮漂亮”的后花園。這些給蕭紅帶來的美好體驗和難得的情感愉悅,成為她故土苦戀情結的構成因素之一。而記錄于《呼蘭河傳》中這“后花園生命的童年世界”——是她“失樂園”后“精神的返鄉”。
蕭紅是一個追求者又是一個反抗者,她所希冀的黃金時代在過去的生活中掙扎過來卻又等待在永恒的未來,她用信仰與靈魂一生追求和向往著。擁有平靜的生活環境和安穩的心態,不為物質生活發愁,不必害怕生命的終結,身心既是自由又能執著信念,這就是蕭紅眼中的黃金時代,是蕭紅用半生閱覽體悟出來的所需要所適合的生活,卻也是蕭紅清醒認知難以實現的黃金時代。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最終或許蕭紅想要的黃金時代僅僅是和童年時的一樣,簡單、安靜、平穩的不必多想明天,只是自由地過好現在就好。而“長夜漫漫,我等待著”詩人戴望舒在蕭紅墓前刻下這八個字,仿佛在替蕭紅發出長夜里的嘆息聲,我一生所愿的黃金時代,我追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