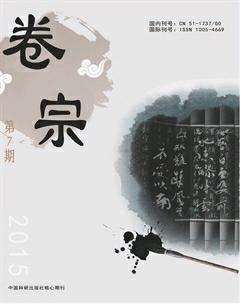簡論陳柱對清代以來墨學研究的評論
梁超前 劉宇龍 劉小云
摘 要:清代以來,墨學研究成果豐碩,而紕漏亦多。陳柱重點對畢沅、蘇時學、梁啟超三位墨學大家的研究疏漏提出批評和質疑,既體現學術求真的精神,又為后來學者樹立典范。
關鍵詞:陳柱;墨學;批判
本文是2014年“大創項目”創新訓練項目“無錫國專與近代廣西”(201410606064)研究成果。
陳柱(柱尊,1889—1944),廣西北流蘿村人。著名國學家。清代以來墨學研究繁盛,“清畢秋帆張皋文之徒,始稍稍補綴,至孫仲頌為墨子間詁,集當時墨學之大成,而墨之書始可讀,墨學始盛。五十年間,治墨學者無慮數百家。”[1]“至于清末,文網已馳,言論自由,學者遂一反而詆孔孟,尊孔子;梁啟超等箸書且稱為大圣人;學者向風慕義,而墨子之學遂如日沖天矣。”[2]陳柱對畢沅、蘇時學、梁啟超的墨學研究提出質疑。
1 陳柱對畢沅《墨子注》紕漏的批判
畢沅(纕蘅,1730—1797),江蘇太倉人。精通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其所作《墨子注》可視為研讀《墨子》的基本工具書,其疏漏亦不可輕忽。
清乾隆年間,畢沅開啟治墨的先導,他校注《墨子》。孫星衍為該書作序言“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3]梁啟超認為“畢注前無所承,其功蓋等于茂堂之《說文》。”[4]杜國慶肯定畢沅所校注的《墨子》,“在許多方面創辟路徑,作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推動了墨學研究的發展。”又認為“因其所依據之書頗為有限,可供借鑒的學術成果也不多,所以書中漏校、錯校、不應校之處非常多,還有許多地方需要作進一步的校勘。”[5]
陳柱認為,畢沅注墨價值重要,但疏漏不少。首先,陳柱認為畢沅“好以儒言傅會。”[6]《親士篇》中,有“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畢沅認為古書中省“不”字,所以增添“不”字;“疚”與“究”相同,所以可說“內省不疚”。陳柱指出畢沅不明古文的用法,古文中“退”用作“彳內 ”,與“內”聲相同,“內”即為“彳內”的通假。所以又可以理解為“進不敗其志,而退究其情。”[7]這也符合墨子的進退之道,而不是畢沅認為的“非內省不疚”的消極主義。又如,《親士篇》云:“雖雜庸民,終無怨心。”[8]畢沅作注為:“言逸佚不怨。”[9]陳柱從墨子所提倡的救世觀出發,認為應解釋為“與庸民雜居,亦無怨也。”[10]故陳柱認為畢沅上述所云“皆傅會儒言之失。”[11]
其次,陳柱認為,畢沅所引據的類書漏略很多。畢沅認為《法儀篇》中的“昔之圣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簡脫“愛”字,可根據原文的意思增添“愛”字。但是,陳柱提出在《群書治要》的引證中已經有了“愛”字。在《七患篇》中,畢沅認為“大臣不足以事之”中之舊版簡脫“以”字。但在《群書治要》中,也有“以”字。[12]
再次,畢沅論證不完備。《耕耘篇》中有“古者周公非關叔”句,畢沅注“關”即“管”的假音。有的版本改作“管”,畢沅認為不應如此。但《左傳》所云“掌其北門之管,即為關也。”畢沅認為,此“管”可作“關”。[13]陳柱引用《說文.木部》中的“棺,關也,從木,官聲。”由此可知管可從官聲,而官聲又有關義。所以“關”“管”是相通的。所以畢沅論證不夠完備。
2 陳柱對蘇時學《墨子刊誤》的糾偏
蘇時學(爻山,1814—1874),廣西藤縣人。清代學者。他對墨學的研究主要有《墨子刊誤》,其偏失亦存,陳柱同樣予以指陳。
孫詒讓稱贊《墨子刊誤》為“專門之學”[14]。“蘇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誤》見示,正訛字,改錯簡,煥然冰釋,怡然理解。”[15]足見蘇時學所著《墨子刊誤》的創獲。
陳柱認為,蘇時學該書的紕漏之處有三。首先,篤信《偽尚書》,誤解《墨子》。在《非命》篇中,“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蘇時學認為,“殷”應改為“夏”[16]。而《泰誓》中“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泰誓》引用《偽書》要將“殷”改為“夏”。但作《偽書》沿用《墨子》。[17]《泰誓》是伐紂王之后的告誡言辭,簡朝亮在《尚書集注述疏》中作過考證。[18]作《偽書》者誤以為《泰誓》是伐紂時之言,所以將“殷”改為“夏”。
其次,蘇時學不擅長于小學。《尚閑篇》“是在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證也。”蘇時學在為此句作注時,稱:“事當為使,二字形近而訛。”[19]陳柱指出,蘇時學不知古字中“事”與“使”為同一個字。[20]
再次,蘇時學刊書不夠嚴謹。蘇時學將《所染篇》的“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也。”錄入《法儀篇》。《修身篇》“身勞不圖”中的“圖”寫成“啚”。[21]
3 陳柱對梁啟超《墨子學案》的質疑
梁啟超(卓如,1873—1929),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的墨學著作有《墨學微》、《墨子學案》等。畢沅治墨以來,治墨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梁啟超。他的研究同樣存在謬訛之處,成為陳柱質疑的口實。
梁啟超在其《墨學微》、《墨子學案》中,論述墨子社會組織法,認為天子的選立由人民的選擇而立。陳柱批評說:“此乃大謬特謬。”[22]如《墨子.天志上篇》云:
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證政,有士正之;士竭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于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于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23]
墨子所認為的理想的社會組織關系應是由“天”、“天子”、“三公諸侯”、“將軍大夫”、“士”、“庶人”組成的等級組織,墨子是在維護等級制度。陳柱認為,“有天政之”、“天之為政于天子”是墨子所謂天子是天之所選,而非民之所選。所以,陳柱批評說:“梁氏于此等處,均未闡發,不免多阿所好之言。”[24]陳柱的論述,也得到楊俊光的認可。楊氏認為,陳柱在《闡墨》中所言“秦政焚書坑儒偶語者棄之厲害階”,“頗為正確”。[25]
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論述墨子之實利主義經濟學說認為:
我想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經濟組織,很有幾分實行墨子的理想......雖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比諸從前工黨專想減少工作時刻,卻是強多了。墨子說:“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勞農政府居然能夠實現,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26]
梁啟超把“以自苦為極”作為“墨子消費”的“公例”。甘乃光認為,“‘自苦不是他消費的原則”,因為他還談到“宮室衣服飲食之安”,“他引用的‘自苦,乃處變時之所為”。[27]對于梁啟超所言,陳柱用墨子《節用篇》“圣王制為節用之法”、“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加以反駁。陳柱認為,《節用篇》所言“圣王弗為”不是圣王禁民不為。梁啟超所言“都由政府干涉”欠妥。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存在不少牽強附會之處。陳柱言:“近人之學,頗似商賈趨時,好以外國學說,皮傅古書;往時人喜談盧梭說傅會之;今人喜談勞農政府等,故又以勞農政府等傅會之。此乃近世學者之長技也。其學術之能聳動聽聞者在此,其短處亦正在于此。”[28]
陳柱作為20世紀前半期墨學研究有成的學者之一,他既肯定已往學者所取得的成績,又有敢于挑戰權威和勇于求真的學術品質,迄今仍是學者治學的標桿。
參考文獻
[1]蔣庭曜.墨子間詁補正跋[J].交大季刊.1934(17)
[2][3][6][7][8][9][10][11][12][13][16][17][19][21][22][23][24][26][28]陳柱.墨學十論 [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181-144-144-144-144-144-144-144-144-145-151-151-151-151-159-
160-161-161-162.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255.
[5]杜國慶.畢沅與孫治讓《墨子》校勘比較研究[D].溫州大學.2010.
[14]許嘉璐.籀庼述林[M].北京:中華書局,2010:382.
[15]蘇時學.墨子刊誤[M].北京:中華書局,1928:1.
[18]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18.
[20]吳大澂.說文古籀補[M].北京:中華書局,1988.
[25]楊俊光.墨子新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71.
[27]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