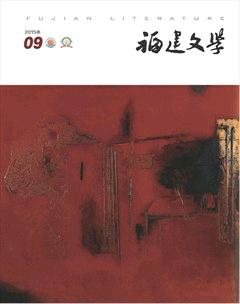灘聲已遠
徐錦斌
這個秋天的早晨,空氣似乎含著透明的力量,我從抗冠嶺上俯瞰斜灘古鎮的一角。四面環山,一水中流。斜灘大橋橫擱著。古龍江兩岸的樓廈沐浴在朝陽里鱗次櫛比顏色艷麗,水中的倒影,依稀可見。斜灘嶄新的姿容,在此敞開。
“你必須說出新的東西,但它肯定全是舊的。”
目光深入的追尋受阻于如此這般的視野,心頭不禁疑念暗起——
古鎮之“古”,存乎何處?
1
“嶺勢從天下,灘流委地斜。”(清·宋際春《詠斜灘》)斜灘形勝之地,刪繁就簡地加以描述,其來龍去脈,大致由洞宮山支脈在鎮域內分開兩支,從西山頂和南山頂逶迤而來,并聚斜灘,形成雙龍搶珠之勢,遂有郭家龍崗、張家龍崗。壽寧境內第一大河流長溪,流經斜灘,自古稱“龍江”。龍江,河面寬闊,既有淺流,亦見深潭,至斜灘水尾,緩緩分流,形成江心島(即馬瀨潯),隨即環合,以近乎直角的急彎,轉向直下,奔流而去。如此,“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勾勒了斜灘地理的基本格局。
斜灘的肇基,據說始于一只狗的選擇,因為主人與狗的默契,過路客變為定居者,掀開拓土開山的第一頁,多少帶著靈異的色彩。這是明萬歷年間的事兒。傳說已遠,卻依然代代傳說。只是,傳說大體相似,版本各有不同。據考,斜灘的開化史,可溯及宋代,其時即有游、程、毛、虞、梁先民定居,越數百年,竟絕沒于洪水災害。明代,才是斜灘基業真正的開始。總之,那時,一家一姓,立定腳跟之后,構成如今斜灘幾大家族的盧、何、周、郭諸姓,他們的先人,相率而至,繁衍生息。唯有原初的斜灘,那渚清沙白蘆蕩茫茫的純粹的自然存在,已永不復現。不斷疊加和延續的,是人文的步履,亦耕亦讀,亦宦亦商。一步步走來,風流輩出,歌哭相隨。沉積至今,眼下,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古鎮,是否越來越模糊了遠處的光景?
2
斜灘,水陸兩通,山道多險阻,水路卻順暢。古鎮昔日的物資集散,商貿繁榮,商號昌盛,在很大程度上是拜龍江所賜。
龍江上行走的木船,俗稱“斜灘槽”、“溪溜”,或順水,或逆流,來來往往,一時盛況,早已淡退,終究歇息了長篙短槳,直至坂尾、坂頭大橋先后建成,斜灘古渡口(上渡,巡檢司前、文昌閣下;下渡,關橋頭)最后的渡船也銷聲匿跡,龍江作為水路通道的意義已蕩然無存。偶見竹排撐出,那不過是捕魚者的休閑遣興或討些小生活。何況,一道道水庫大壩的攔腰橫截,一個個工廠的肆意污染,龍江河床日淺,河道日窄,水流時多時少,其自然生態,已不復當年。
不知何時,龍江上的古木橋拆除了,斜灘、樓下間的“π”型石橋埻,還站立在溪流淺瀨中,孤獨地,年復一年。
世易時移。公路開通,水道閑置,山道荒蕪。
斜灘連接各方,有五大陸路古道——跨省與浙江相通的:越平溪、南溪,抵政和;循車嶺、岱陽、托溪,至慶元;沿竹管垅、南陽、犀溪,到泰順。跨縣界的:過武曲,達福安;經鳳陽,與周寧相連。
國慶期間,我赴斜灘同學聚會,很想棄車徒步,取古道,從鳳陽基德村啟程,直下馬座頭陡嶺,擦過獎祿,再下徐家池,奔渡船頭,重溫當年的求學路途。同學一聽,驚訝道:走不了,好多年沒人走,荒了。以草木的瘋狂,侵吞人跡已渺的山道,只在秋去春來之間。這么多年,其難以措足,實可預見。其他幾條古道的情形,想必也大抵如此,都一一埋沒于榛莽了吧?
3
要說古鎮,直接呈現于視覺的是它的建筑。那些深宅大院的木質年輪,黯淡的檐角,破落的門楣,青幽的墻垛,是歷史敘述,歷史例證,既指涉時間的流逝,也暗喻人事的變遷。小巷深處,門口廳堂,一聯一匾,無不寫照著各自的門庭家風世業榮耀。今日,或還有斑駁的字跡幸存;或已被鏟除于無形。
“一經舊業承科第,兩世家風宦晉陽。”(盧家里曾設立“一經樓”,寓意“通一經者為博士”,以激勵子孫。盧家有先后兩代人在山西晉陽當過知縣。)盧家里,“進士第”,走出的是進士、舉人、詩人、文士,盧金綺,林則徐的姐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舉,嘉慶十三年(1808年)出任山西岳陽縣知縣;盧贊虞,道光十三年(1833年)汪鳴相榜進士,欽授山西浮山縣知縣;盧雁秋,清末壬寅科舉人,民國元年(1911年)出任福建省長樂縣知縣;盧少洲,畢業于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土木科,歷任交通部主事、三沙海關關長……
“西江宦跡曾盟水,東閣家風喜詠梅。”何家巷,“大夫第”,此間出落的人物,都有各自精彩的“民國演義”。何雋義釋鮑羅廷夫人,何宜武歷任臺灣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常委,何宜慈擔任臺灣“國防”科委副主任……
“豹隱南山霧,鵬摶北海風。”坂頭,郭家宅第,“家學淵源”,郭公木歷任泰寧縣縣長、龍巖縣縣長、福建學院(福建師大前身)院長,其后人亦多薪火相傳于教育一途,成就的是杏壇佳話。
“窮巷高士轍,柴門將相家。”周家里,“朝議第”,雖是素樸人家,卻不失寒門風骨。由此邁步遠走的周孝培,投身軍旅,先后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日本陸軍學校,歷任東北軍旅參謀長、代旅長、重慶軍訓部騎兵副監、代兵監等職,人謂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位“騎兵少將”……
4
古鎮的“古”是前人和時間共同留下來的,任誰也賴不掉,只是,在這每個毛孔都滴著功利的時代,有誰,真正對古鎮之“古”持存居敬之心和珍惜之情?
“時間中虛假的門,你的街道朝向更輕柔的往昔。”讀博爾赫斯的詩句,腦海里會出現斜灘古鎮的街道。可是,那條不大不小的陳年的鵝卵石長街,沒了。1999年9月26日的那場火災,沿街鋪面吊腳樓化為灰燼,百年長在的鵝卵石長街,經受了火光映烤的最后時光,隨著家園重建,被徹底掀翻,埋葬于水泥。
古鎮其實是有脈絡的。除了街道,還有那些大大小小的青石巷道。它們,也幾乎無一幸免,被水泥抹殺。如今,只有周家里,一截短短的巷道,舊貌猶存;盧家里,某座老宅門前,方寸老路,由于主人的挺身堅守、負隅頑抗,才得以殘留。
古鎮街尾的小廣場,被鎮政府的新建大樓耍橫一擠,變得如此逼仄,狹窄。本來就是小廣場,如今,“場”沒了,只剩下“小”。“做十三”(農歷每月十三趕墟)的人流匯集此地,豈還有當年的場面?
郭家大宅后的菜園里,那座黃土墻炮樓,飽經風霜,煢煢獨立。只要還在,便是大幸。否則,像文昌閣,“門迎云路三千客,地據龍灘第一峰。”終于,不見了廢墟,也沒了遺址。同此命運的,還有觀音閣、媽祖廟……
那座小小的石板橋呢?發源于下坪坑那條小澗,從原紙廠舊址流出,與龍江交匯,這座石板橋就跨澗坐落在交匯口附近,頂端圓弧形的條狀青石一層突出一層往上疊加,共四層,形成拱形基座,橋面鋪搭著石板條。造型簡約,不失風致。我在斜灘求學時,曾居此橋附近,晨讀,或晚間散步,踏橋而過,常來常往。那時和我的同學還偶爾在此橋不遠處耕種一畦菜園,自給自足,澆水施肥,來去必經。二十多年后,據諳于掌故的當地人士說,此橋很可能建于宋朝。但它的粉身碎骨,毀于一旦,卻在前年,2011年,因為鎮政府的防洪堤工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年,正值《人文斜灘》付梓,文字圖片不遑記錄,一處古跡已被悍然滅除。
江心島,龍江環抱的一片沙洲,當地俗稱“馬瀨潯”(此名稱,暫從現有資料所載,本地土話如何落實到合乎情理的漢字,還值得考證),在我的印象中,它一直被挖石采砂,傷痕不斷,自愈能力怎么也趕不上新添的創傷,但它的美仿佛是永遠的。近年,馬瀨潯被興建為江心公園,楔入水泥操場,人工作意十足,自然之趣永失。當地士人稱譽它 “儼然不沉航母”,用意固然在于強調其不沉,而這恰恰是可虞之處。何況航母作為武器,充斥的是戰爭的威懾和陰影,豈可比擬于馬瀨潯的天然?
5
三十年前我與盧少洲先生擦肩而過,失之交臂。我來,他走,飄然而去。那天晚上,在斜灘,沿街面江的那爿吊腳樓,表姑將我迎進家門,我看見一位老先生扶杖下樓,道別,出門。回過頭,表姑告訴我:“這位老人會寫詩……”這是我第一次聽聞盧少洲,少不更事,也沒太在意。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重回斜灘,謁見盧先生,他已長臥病榻。寸步不離,陪伺床前的,是他年近古稀的公子盧紅伽。一對父子,兩位老人,形影相吊。晚境若此,令人唏噓。特殊的政治年代,盧氏一門,悲劇上演,血淚相和,生死交織。他們的人生起落,已非幸或不幸所能道盡。還記得,1990年10月26日,盧少洲去世。我遵囑為《閩東鄉訊》寫作通訊:“深秋的陽光,無聲地照著靈前的白花,照著執紼者悲傷的淚水。”同期鄉訊刊出悼念專版,配發盧紅伽的《哭父》長文,其劈頭的一句獨立成段:“人世光陰如過隙,滿城風雨近重陽。”接著一段:“數十載相依為命之嚴親,即于重陽佳節這一天,棄兒而長逝矣。”撕心裂肺,一發不可收拾,滿紙悲聲,無以自禁。時任寧德地區行署副專員林思翔特意交代,要多給些稿費。
盧少洲去世,對盧紅伽而言,“如同林鳥失群,天拋異色”(盧紅伽《哭父》)。其失落無依、求告無門之狀,殆難形容,于是念經,事佛,凡古鎮之內,粉墻石壁,面路沿街,有空白處,每每題寫“阿彌陀佛”。如此行跡,不免招來鄉黨物議。
那兩年,我任教古鎮,與盧家父子多所過從。盧少洲不以書法名家,我看他晚年的墨跡,一把老骨,浸徹蘇味。書卷氣,在他筆墨里是自然而然的。反觀當下,以“書法家”招牌招搖過市的,除了叫囂之氣,還真不知道書卷氣何在。書法與舊學,已脫節啦,你裝,裝得像嗎?
古鎮人士的翰墨,我偶然珍藏了一幀何宜武的手跡,是他致臺灣“國防部”少將高級參謀邱耀東八十華誕的祝壽詩:“師干統馭著殊功,國會尤欽獻替隆。今慶杖朝益碩健,將軍未老更豪雄。”穩健、沉著的行楷,頗有顏魯公、蘇東坡的筆意,透著民國那一代人的余緒、風范,雖非書家,卻見儒雅。我曾記錄道:“今日幸遇其手跡,正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拜觀這一紙翰墨,斯人如在,可親可感,且油然地牽連著關于壽寧的、斜灘的鄉情,其間自有別樣的況味。倘若,和它就此別過,則江湖之大,何處問訊?”
盧紅伽先生的片紙只言,我也留存一二,寫的只是隨意的劣質的紙張,筆不精良,墨則尤次。字跡透著被壓迫下的倔強,人謂他學何紹基,我看倒有些顏真卿、康有為的痕跡,而終究是慌不擇路,難言來歷了吧。盧紅伽在《哭父》中哀嘆:“不孝生而多難,涉世甚苦。”實則,到他這里,事勢盡去,除了早年的意氣風發,他后來幾乎沒有直起腰來的時刻,至于寫詩“謾罵”江青并投寄馬來西亞,被偵察部門巧施手段,不動聲色,按圖索驥,逮個正著,投入大牢,則是嚼食黑暗,夫復何言!而在乃翁身影的遮蔽下,人們對他多少不怎么看重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盧紅伽的遭遇殃及了后人。據說,盧少洲與陳子奮私交甚篤。曾有約,盧作詩,陳據詩作畫。后來,不了了之。盧紅伽的兒子,曾拜師陳子奮,學習國畫。后因家庭變故迭起,遂告中斷。世道弄人,真堪扼腕。
盧少洲死,盧紅伽再死,斜灘古典的人文時代,收斂了最后的一抹余光,戛然終結。就舊學而言,自此而后,古鎮上,有誰能達到他們的腳步呢?
現在回到古鎮,你一不小心可能遇到更大的官員,更有錢的老板,更壯觀的題字,但你再難遇見年近古稀不經意間還能背誦高吟“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老頭。那滿腹經綸的,在古鎮上押韻的,用典的,寫詩做對子的,迂腐的老頭。這個,可以有。但,真的沒有了。
6
人事凋零。
古跡日損。
古龍江,灘聲已遠。
一聲一聲喊著古鎮古鎮,有誰,覺得不安心嗎?
歷史與現實,古典與現代,審美與實用,在它們的相互角力中,一座古鎮是極易被絞殺的。
我想,古鎮的“古”,當是,留住了時光。雖遠,猶在,包括,人心和感情。
但愿,這樣的想法,不至于太愚蠢。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