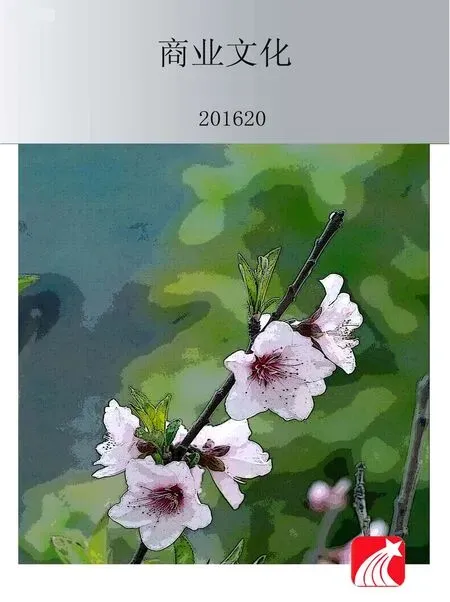新商業文明的核心理念依然是“誠信”
文/ 王日根
新商業文明的核心理念依然是“誠信”
文/ 王日根
一 誠信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倫?理
在中國古代,人言為信,即講誠信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基本要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 為政》),為人誠信成為人生信條和行為守則,盂子甚至提出:“夫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孟子正義 離婁下》) 這種“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信用觀也成為商業活動的重要倫理準則。司馬遷(《史記 貨殖列傳》)記載,楚人范蠡因經商而擁有萬貫家財,但其樂善好施,仗義疏財,被時人譽為“富好行其德者”。在缺乏法治、契約精神的傳統社會里,獲取利益的手段和途徑必須符合社會道德規范,否則便很難長久維持下去。在當時的社會里,君子人格受到社會普遍的推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樸素倫理深入人心,商人是最多受到利益誘惑的人群,社會道德要求他們應該“見利思義”(《論語 述而》)、“見得思義”(《論語 季氏》)。《論語 學而》篇中,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因不失親,亦可宗也”。《漢書 公孫弘傳》指出:“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孟子 盡心上》也說:“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矣,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由此可見, 儒家思想中論及的“義”主要從“ 治人” 層面立論,是君子應該具備的人格和道德品質。同時,荀子、墨子從另一方面也把“義”的道德標準從“治人”層面上升到了社會制度的層面。如《荀子 王制》言:“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載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論語 里仁》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大學》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以此在倫理導向方面將“義”作為首要價值。另一方面,當義與利產生沖突時,強調利須服從于義,見利思義,獲取利益要符合道德規范,如《荀子 榮辱》言:“先義而后利者榮,先而后義者恥”,“義勝利為治世,利勝義為亂世”。《論語 述而》也指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主張一切以“義”為準繩,他甚至認為,義不僅重于利,而且重于生命,假如義利不能兼得,則應“舍生取義”。這種義利觀深刻地影響了國人的價值觀,成為我國商業倫理的重要價值訴求。
“新商業文明”的基本理念:(一) 商人階層的使命是為消費者提供適銷對路的產品,而不是見利就上,或在金融領域過度地制造泡沫,乃至沖垮實體經濟。(二) 商人的社會責任不在于賺取了若干不義之財后,少施其惠給社會,而在于在生產、經營環節走“以義為先,義利兼顧”的道路。(三) 如今的商業越來越成為智者的事業,每一個入行者除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外,更應該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四) 慈善和公益是人類社會的高尚事業,是商人人格提升的理想渠道,是商人人生價值實現的至高殿堂,商界精英理當如此要求自己。
總之,在人類社會中,自從有了商業活動之后,便有了商業倫理,像誠信、公平就衍為商人的職業道德。
或許初期的商業活動就屬于以貨易貨的零星之舉,交易雙方各自實現了自己的交易目的,交易本身便叫公平;或許初期的商業活動能從可見的勞動量的衡量中得到裁斷,因為交易雙方掌握了完全信息,于是交易中便不能存在欺詐。追求誠信的商業倫理本身就能對商業活動產生約束和規范作用。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產品的豐富,人們的交易活動也變得更加復雜。作為交易手段的貨幣產生了,且不說貨幣的種類很多,貝殼、金、銀、銅等均曾經擔任過貨幣的角色,單論銅、銀等,還存在成色高低的區別。人們在經營活動中不僅需要防備成色不足,還時常要防備假幣的坑害。
商業活動增多之后,作為中介的牙人形成了,牙人往往分為官牙、私牙,起初,牙人設置的目的是提供中介服務,但慢慢地有些牙人以朘削商人為目的,則制約了商業的正常發展,商人們往往與牙行玩起了貓躲避老鼠的把戲。商人將成功地逃稅作為獲利的一種手段,這其中,有些或許是背離誠信原則的,有些也可視作是躲避不適當雜稅而作的消極之舉。
隨著商業活動的增多,作為交易地點的市場出現了。無論是來自官方的管理,還是來自民間的自我管理,本來的目的都是無論建立良好的商業秩序,保證商業活動的正常開展,環節的增多意味著公平精神之維持的必要,亦要求各環節能堅守公平的尺度。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維持著“ 士農工商”的四民價值觀,四民秩序既作了社會地位的高低排列,亦給予不同階層不同的責任要求。“重農抑商”體現了對農民職業的尊崇與對商業的貶抑,其中實包含了對商業活動中極易滋長的市儈習氣的抑制。于是士者恥為商,他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甘于“君子固窮”、“恥言利”,憂天下而樂萬民是全社會尊崇士人的基本理由。
二 近世商業活動言制而不背信
亞當.斯密在從一個倫理學家轉變為一個經濟學鼻祖的時候,提出了人的雙重本質的判斷,即“利己”與“利他”,實現了二者的統一時,現在稱為“雙贏”,有時甚至是“多贏”,倘若只是為“利己”而無視“利他”甚至侵害了他人,這樣的交易便較難持續,市場規則乃至上升為法律的條文均可能對之施以懲罰。在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那里,“經濟人”與“道德人”二者并行不悖,彼此支持。
應該說: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進步奠基于兩個良好旳基礎之上,一是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努力謀求經濟利益的巨大化, 二是克勤克儉、誠實守信的商業倫理。各國法律對于背離這種倫理的行為有相應的嚴厲懲罰,但每個人內心所秉持的“公平”、“正義”、“誠信”觀依然是市場經濟走向規范化的最基本前提。這被人們概括為“ 新教倫理”。
一方面強調合理地追逐財富,另一方面更強調合理地限制消費,推動資本積累或將財富適度地分給窮人,從而使經濟獲得發展,也使社會保持和諧。
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更是一種道德經濟。我國傳統商業倫理的核心之辯并非斥“利”,而是恥以不當手段獲取的利。傳統商箴中就有“欲富先仁,富商不忘其德,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寓利于義”的思想,這也是我國商業倫理的核心思想。中國傳統商人又何嘗沒有崇高的追求?近世以來,自從他們的身份意識被彰顯之后,他們亦致意于樹立自己的誠信守義形象。國家的法律制度固然是維護商業秩序的重要手段,商人通過同鄉組織—會館或同業組織—公所而實現的自我約束,對于商業發展的推動和商業文明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商人們在會館中“祀神、合樂、義舉、公約”,既通過祭祀鄉土神、食家鄉味、講家鄉話、聽家鄉戲而尋找到心靈的歸屬,還可以通過義舉、公約樹立“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回饋社會、提升誠信水準的整體形象。會館實際上具備了自治的效果。傳統的里甲、保甲、鄉黨式管理模式都難以管理這龐大的流動人群。
會館卻可以獨展其長,會館往往能融合寓居客地同鄉中的官、紳、商等各個階層,彼此動用各自的資源,形成互補的局面,經濟而有效地實現內部的自我整合、與外部世界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可以說會館組織使民間智慧在復雜的社會變遷面前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流寓社會建立起“熟人網絡”,彼此樹立誠信的形象,其對社會管理的積極意義是顯著的。
既然會館對社會管理的效果是積極的, 因而便逐漸由民間自發產生發展到獲得政府的默許、認可乃至保護,會館由此成為地域文化的展示物,甚或發射器,由會館認識地方文化已不失為一可取之徑。會館的社會功能還有所延伸,到近代,其社會治安功能進一步彰顯,會館在消除黃賭毒、杜絕民間私藏槍支、禁止罪犯藏匿等方面都有所作為。有的會館還匯集資金,為政府的應急軍需提供實質性的幫助。這些都反映了會館順應時勢的內在品格。
會館較之由西方引入的商會更多些人文關懷,更多些對人際關系、人生價值乃至社會價值的追問,因而它不僅像商會那樣旨在制定商業規范,而且樹立家鄉的文化精神,彰顯地方文化建設業績,濟助貧困的同鄉人,參與乃至主持客居地的社會事業,給同鄉人以自豪感、榮譽感和歸屬感,他們將家鄉的英烈奉祀為神,無疑成了最強有力的黏合劑和凝聚器,同時為主流、優秀的價值觀延存提供了基地。因此,即使是在商會移植進中國并大行其道之時,會館的生命力并未消減。有一位著名學者說:“進入21世紀以來,各大城市中的近代商會組織紛紛建立,但舊式的會館、公所仍然是城市工商業中的重要經濟組織,它能把傳統的地緣關系與現實的行業紐帶融為一體,把舊式的人際關系與職業行規與近代的社會契約和民主意識結合起來, 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國城市經濟功能結構的近代化過程,既有新舊事物間的矛盾沖突,也有它們之間互補共進的發展。傳統因素直到1949年仍在城市經濟中起著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文化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人性中的“求利”、“縱欲”思潮被極端伸張,好在有契約觀念、法制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將“求利”、“縱欲”、欺詐等等惡行加以限制,但是契約、法律從根本上依然屬于“他律”,無法限制個人內心或不公開場合的背離可能,若干僥幸之舉仍常有出現,“誠信”記錄往往并不代表真正的誠信。
不過,不誠信的行為歷久勢必遭遇被揭露的命運, 宗教的力量一定程度上讓不誠信的人付出代價,因而, 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還是會堅守誠信的道德底線。
三、誠信依然是新商業文明的核心理念
當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大門之后, 我們過多強調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卻過少地關注到“誠信”與“利他”觀的樹立。殊不知這本來就屬于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卻由于“文革”等政治運動被陵夷殆盡。由于新技術背景下信息不對稱的日益嚴重,有悖“誠信”和“利他”的行為又沒有得到政府部門和行業組織的有效制止,于是,誠信、公平的市場秩序便無法完整地建立起來,乃至“三聚氰胺”、“化學火鍋”等現象層出不窮,通過媒體輿論放大的商業競爭、雇傭網絡水軍爭奪客戶的營銷方式等等,幾乎無所不用其極。由此,商業道德淪喪,商業運行的良好生態便無法建立。
我們在高喊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時,不應忘卻市場經濟照樣是“道德經濟”,以“誠信”為根本要素的道德約束是走向成熟市場經濟的前提。當建立“新商業文明”的呼聲愈加強烈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確信如下基本理念:
(一) 商人階層的使命是為消費者提供適銷對路的產品,而不是見利就上,或在金融領域過度地制造泡沫,乃至沖垮實體經濟。
(二) 商人的社會責任不在于賺取了若干不義之財后,少施其惠給社會,而在于在生產、經營環節走“以義為先,義利兼顧”的道路。
(三) 如今的商業越來越成為智者的事業,每一個入行者除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外,更應該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四) 慈善和公益是人類社會的高尚事業,并不是將黑錢漂白,或所謂“承擔社會責任”乃至謀取福祿的場所。慈善和公益是商人人格提升的理想渠道,是商人人生價值實現的至高殿堂,商界精英理當如此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