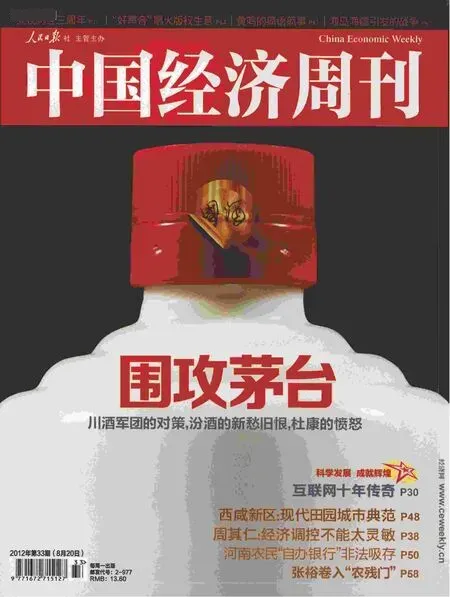“后文人時代”的文化守望與精神重塑
潘呈杰 關天舜


《水墨人物》

左:《墨象-馬勒交響樂+墨》右:《明清山水》
“文人”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曾在中國的歷史上活躍了2500年。它是一個群體的代稱,也是中國文化符號中的一種“情懷”隱喻。而當代,“文人”的稱呼大大被弱化了,這個傳統文化中的主力軍以西化了的“作家”、“學者”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中。面對洶涌的文化侵襲,傳統文化又何以依托“文人”自居?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從未停止探索步伐,他們在考慮這個民族該如何審美。
用時代的眼光守望文人的故土情懷
李庚作為李可染先生最小的子女,自幼在李可染身邊長大,李家深厚的家學淵源為李庚在成長階段鋪就了堅實的文化積淀。青年時期的李庚已在繪畫上頗有建樹,對中西方文化差異和如何繼承傳統文化有自己的思考。1980年,李庚來到了當時與美國東西呼應的世界藝術中心——日本求學。80年代日本的美術思潮受到“包豪斯”的影響,當代藝術遍地開花,眾多的藝術形式被細化,李庚正在這時帶著中國的傳統藝術融入了洶涌澎湃的藝術大潮中。京都市立藝術學院畢業后,李庚先后在日本、德國從事水墨研究、教學。
幾十年的海外經歷讓李庚洞悉了世界藝術潮流與民族文化交融,也發現很多西方人以片面的眼光看待中國文化。他說:“中國近現代史上,中國和世界互通的地方很多。有時候融合的口徑大,有時候融合的口徑小,而我正是在融合小的時候出的國。在日本的早些年,國外對當代中國持否定態度的比較多,那是因為外國評論家沒有能力評論中國當代藝術。”對此他直言不諱:“你們還是坐飛機到北京看看再說話吧。”李庚這種引領西方站在立體的、多層面的角度去看待東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西方藝術家的廣泛認可。
李庚熱愛祖國,熱愛傳統文化,這是他把中國藝術思想傳播海外的動力,也是李可染大師畢生的追求。關于兒時對父親的記憶,李庚回憶說:“他對子女的教育是身教多于言教,他是一個學者型,說的話很少,總是看他在寫字臺前畫畫、讀書,在用功。他的出身窮苦,但不妨礙精神富有;他一生簡樸,但在美院的教授里藏書最多。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父親每周都至少兩次去故宮,無論雨雪;在故宮在每張畫前都要站十分鐘,沒人比他站的久,看得出對那些畫他是懷有敬意的,出了故宮就要去榮寶齋,看民間的藏品,不到關門不會走。”李可染對視覺文化有自己獨有的理解,并融合進他對傳統的繼承一并帶入了教學中,培養了大批“李家山水”的繼承人。
在李可染畫院的展覽館里,李老的雕塑靜靜地佇立著,他用目光守望著遠方,守望著家鄉的山川風貌,守望著中國大地,那里有他在紙上永遠也畫不夠的故土情懷。
以教育的手法重塑當代的審美精神
作為李可染畫院院長,李庚延續著李可染先生的心愿,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傳承開拓并立足于當代文化藝術。對于當代中國的藝術教育,李庚闡述了自己的見解:“我國藝術大學的學科分類過細,藝術大學的價值觀是好與不好的問題。藝術家的思維要跨領域,不能培養白開水一樣的藝術家,藝術家需要經常研討,藝術沒有對與錯,科學領域里才是用對錯的標準來衡量的。”
關于傳統藝術在當代的傳承,李庚談道:過去是審美的時代,什么都有標準;現在是傳媒時代,有很多藝術理念的混亂、價值觀念的混淆,最重要的是參與的人多了,這時候就需要一批高水平的藝術家來傳道授業,來解惑。以教育的方法來提升全體國民的審美,而李可染畫院正是一個這樣的機構。
對于李可染畫院承擔的任務,李庚說:“李可染畫院集畫院與高級研究所為一體,以研究的精神立足當代。集合百名以上的教授以單項研討會的形式從事專項研究,同時培養青年藝術家,給青年人提供廣闊的平臺。將100年來中國文人做了什么和當代青年人應該干什么做一個接軌,并以免費演講等形式給普通老百姓普及文化,有教無類,這也是李可染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全體中國文人的心愿。”
因李可染善畫山水,弟子眾多,且風格鮮明,技法獨到,曾經有人提出,將李可染及其門下弟子統稱為“李家山”。對此,李可染先生說,還是叫“中國派”吧。相比于個人名利,李可染更愿意以民族審美為出發點,做一個為中國藝術而奮斗的人。時至今日,三代“中國派”已經成為了中國藝術的號角,他們以水墨為基石,把河山做畫卷,引領著我們在壯美的自然中體味生命,在絢爛的色彩里審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