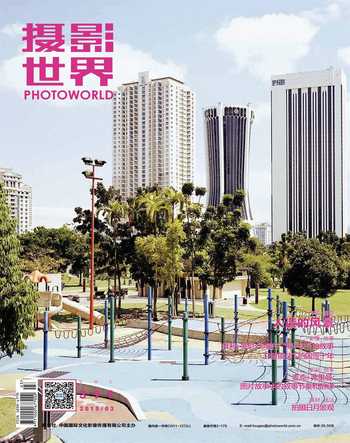楊圓圓:在克拉科夫的十日
朱一南

2013年夏天,楊圓圓來到波蘭的克拉科夫。十天的旅行結(jié)束后, 她并未像一個旅行者,留下一疊明信片一般的風景照片;而是用影像提出疑問:在陌生之地,當旅行者只能停留很短的時間時,自身是否能與該地的歷史時空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一座城市又如何通過遺留下的細節(jié)來告知到訪者彼時此地的故事?
于是,楊圓圓試圖把自己拍攝的照片、在當?shù)囟质袌鍪占睦险掌鸵恍┯幸馕兜碾娪爱嬅娼貓D放在同一場域內(nèi)發(fā)酵。在影像的相襯中,觀者可以隱隱被一條線索——關(guān)于城市,關(guān)于歷史,也關(guān)于她自身的情感認知——引領(lǐng)入一個開放而模糊的故事中。這種挪用圖像的創(chuàng)作手法,讓她的作品集《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增加了觀者思考的層次。同時,這次創(chuàng)作也很好地展示出,攝影師如何通過編輯一本有節(jié)奏感的攝影書,出色地展示一個項目。
楊圓圓,出生于1989年,目前工作居住于北京。她于2013年獲得倫敦傳媒學(xué)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即以前的倫敦印刷學(xué)院,是倫敦藝術(shù)大學(xué)6所學(xué)院之一)的攝影本科學(xué)位。她的藝術(shù)實踐包含多樣的形式,以攝影為主。
自述: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以一種介于旅行筆記和手札之間的形式呈現(xiàn)。盡管這本書沒有目錄,但是書的整體結(jié)構(gòu)實際包含了三個隱形的章節(jié),它們被構(gòu)架在看似零散的排版形式之上:1.戰(zhàn)爭;2.城市;3.聯(lián)結(jié)(從彼處到此處/從我到你)。書中所出現(xiàn)的素材包括我在克拉科夫逗留的10天之內(nèi)留下的快照、手記和收集的老照片,以及對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電影截圖以及文字摘錄)。這三件作品包括:《空中殺手》(2008年,導(dǎo)演:押井守)、《看不見的城市》(作者:卡爾維諾)以及《我略知她一二》(1967,導(dǎo)演:戈達爾)。對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劃分出了這三個隱形章節(jié)的框架。來自三個不同年代與背景的既存作品與我在克拉科夫10天內(nèi)所搜集的素材交織在一起,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時而緊密交織,時而又相對松散。通過排版與排列的節(jié)奏調(diào)和,這些素材逐漸在書中編織出一條模糊而開放的敘事。
一直以來,我都對于旅行者的狀態(tài)很感興趣。當我們前往陌生的城市并只能停留很短的時間時,個人的經(jīng)驗與知識是否能與城市龐大的時間網(wǎng)絡(luò)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我們此時在此地所遭遇的事物,是否能與彼時在此地發(fā)生的事件產(chǎn)生聯(lián)結(jié)?這本書呈現(xiàn)的僅僅是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倘若我并沒有在2013年7月16日去Hala Targowa購買舊照片,沒有在7月15日前往波蘭航空博物館參觀,或者沒有在2011年就看過戈達爾的電影《我略知她一二》,也許這本書依然會誕生,但它最終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形式可能完全會是另一種樣子。
物理學(xué)家Julian Barbour曾假設(shè)過一個全部由“此刻(Nows)”組成的無時間的宇宙。他這樣說道:“隱秘的時間之河是不存在的,卻存在可被稱為時間點(instants of time),或者‘此刻’的東西。”在生命過程中,我們就像是穿過一段連續(xù)的“此刻”,問題在于,它們是什么呢?它們是宇宙中一切在任何時刻彼此關(guān)聯(lián)的排列,比如,“現(xiàn)在”從另一個角度去假設(shè),或許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不存在真正的間隔,每一個“此刻”都是由無數(shù)條時間軸匯集而成,也因此,沒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一切都是彼此關(guān)聯(lián)的。事實上,這種假設(shè)或許就被投射在我們的日常周遭中,譬如在充滿繁復(fù)印記的墻面上,或者我們時刻都被多重信號所充斥的頭腦里。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好像是一本旅行筆記,但又好像不止于此,你怎么定位這本書?
書的呈現(xiàn)形式像是一本旅行筆記,大部分基礎(chǔ)素材也是我在克拉科夫的十天里搜集的。然而,這件作品的結(jié)構(gòu)與理念遠不僅僅關(guān)于一次旅行。我本人在這座城市中的經(jīng)歷僅僅是書中的線索之一,其他兩條主要線索則是書中引用的兩部影片——《空中殺手》以及《我對她略知一二》,這兩條線索源于我過往的觀影經(jīng)驗。我試圖將三條本無關(guān)聯(lián)的線索交織在一起。同時,這兩條線索也劃分出書中開頭結(jié)尾的兩個章節(jié)“戰(zhàn)爭”與“聯(lián)結(jié)”,兩個章節(jié)被中間的章節(jié)“城市”串聯(lián)為一體。
就像我在作品陳述中引用的卡爾維諾的文章所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無數(shù)經(jīng)驗與信息的集合體,此時此刻的我們,由我們的記憶、體驗、看過的電影和讀過的書匯聚而成,而這些過往的認知與我們在當下的體驗又能發(fā)生怎樣的聯(lián)系?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于周遭的理解與判斷,并如何影響下一個事件的發(fā)生?
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nèi),一個人與某個地點可能產(chǎn)生何種關(guān)聯(lián)?《在克拉科夫的十日》以及我的近期其他幾件作品,都是在這個提問語境中展開的。旅行僅僅是與地點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的一種形式,其他的形式也可能是一次短暫散步,或者長達幾年時間里多次重返的某個特定地點。
在我的作品中,城市通常被作為一個起始點,但作品并不僅僅是對城市表面化的描繪。發(fā)生于不同時代的事件交織成一張張錯綜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覆蓋于每個城市、甚至每一個街角。面對這些龐雜的結(jié)構(gòu),我試圖梳理出多條討論的線索,歷史的線索、戰(zhàn)爭的線索、特定人物的線索等等。
在一次對話中,你提到采用了圖像挪用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式,在這本書中你是如何使用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挪用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手法,在藝術(shù)史中很常見。在這本書中,我挪用的素材主要包括了兩部電影的截圖以及我搜集的舊照片,無論素材是由我拍攝還是搜集,它們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而對于書的編輯就如同電影的剪輯,它是真正將這些素材串聯(lián)的語言。
說到挪用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手法,我想說在當下這樣一個信息平鋪的時代,世界上已經(jīng)有太多的圖像。我并不是說我們已經(jīng)不該再去制造新的圖像了,只是面對一個如此龐大的資料庫,我們是否應(yīng)該在創(chuàng)造新圖像時更為謹慎?并且,攝影自發(fā)明之時,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記錄,而在當下,大量的既有圖像就是我們的現(xiàn)實;無時無刻將我們包圍的廣告與熒幕上的圖像就是我們的現(xiàn)實。因而我認為,在創(chuàng)作中對既有圖像進行挪用,是當代視覺藝術(shù)家對現(xiàn)實周遭的本能反應(yīng)。
你是如何找到這些老照片的,會涉及到版權(quán)問題嗎?
老照片全部尋自于跳蚤市場,攝影師和舊照片的擁有者都已不可尋。在作品中運用老照片作為素材的藝術(shù)家很多,通常來講不會涉及版權(quán)問題。
為何選擇了“攝影書”這樣的影像呈現(xiàn)方式,而不是展覽或者其它?
在我看來,書是呈現(xiàn)這件作品最理想的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這件作品也可以通過展覽的形式呈現(xiàn),只不過素材之間彼此關(guān)聯(lián)的邏輯,以及作品被呈現(xiàn)的形式將會不同。
有人認為,攝影書本身才是攝影師最終完成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你同意嗎?比如說,單張照片不是很強的時候,如果經(jīng)過再編輯,并加之一些書籍的裝幀手段,能加強整體作品的表現(xiàn)力。
我不同意。攝影書僅僅是作品最終呈現(xiàn)形式的一種。而制作一本攝影書之前,創(chuàng)作者需要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這件作品為什么要以書的形式呈現(xiàn)。這本書究竟僅僅是一本作為攝影作品載體的畫冊,還是說書本身就是一件作品?然后是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問題,書的結(jié)構(gòu)會是怎樣的?這樣的結(jié)構(gòu)與作品的觀點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等等。
在我看來,僅通過強調(diào)“單張照片的視覺強度”來閱讀攝影的年代已經(jīng)過去,單張照片僅僅是作為完整作品中的一部分,而作品本身是否“強烈”,則關(guān)于創(chuàng)作者的構(gòu)思,關(guān)于如何將照片進行編輯與組織。
而所謂的“裝幀手段”,即書的設(shè)計,首先要與作品的理念緊密關(guān)聯(lián)。不是說所有人都適合穿同一款好看的衣服。
在你看來,什么是一本好的攝影書?你看到過哪些?
在我看來,一本好的攝影書遠不僅僅是作為攝影作品的載體,而應(yīng)該是一件獨立的作品,具備自己獨特的語言,具備與作品節(jié)奏契合的編輯與組織。近期比較喜歡的畫冊包括Cristina De Middel的The Afronauts,藝術(shù)家通過自己的想象再現(xiàn)了1960年代發(fā)生在非洲的贊比亞太空計劃。一直都非常喜歡的攝影書包括Collier Schorr的Jens F.以及Daniel Blaufuks的Terezin。
作為年輕攝影師,在制作完攝影書之后,你是否還需要參與到推廣環(huán)節(jié)?你是如何做的?
需要啊。首發(fā)式,在藝術(shù)機構(gòu)做講座,聯(lián)絡(luò)展覽事宜,報名參加比賽,這些工作,任何藝術(shù)家都需要做吧。
制作攝影書的成本大致要多少?在沒有資金注入的小眾藝術(shù)書籍出版上,很多創(chuàng)作者都面臨無法回收成本的問題,你如何看?
成本根據(jù)作品來定吧,選擇的紙張與作品的開本以及印量都會讓成本有很大差異。我認為,創(chuàng)作者對于自己的定位要準,在書發(fā)行之前,要對自己的受眾群以及范圍有大致的預(yù)測。這些都是非常不確定的,譬如我剛才提到的畫冊The Afronauts,藝術(shù)家獨立出版,印了1000本,而在發(fā)行后兩個月內(nèi)就全部售光并獲得大量獎項提名,這是藝術(shù)家本人也根本沒有預(yù)測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