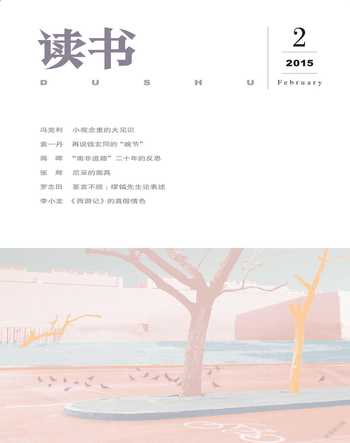有什么關系?
熊秉元
關于華人社會的人際關系,很多學科(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國學,等等)都有探討。其中最廣為人知,也經常被中外學者引用的,無疑是社會學者費孝通的著作。在《鄉土中國》這本書里,費孝通(一九四八年)由田野調查歸納出他的心得:華人社會里的人際關系,符合“差序格局”的結構。
要體會差序格局的意義,不妨用圖形來比擬。以棋盤的交錯縱貫來描繪,并不很恰當。用同心圓來刻畫,庶幾近之:把一個石子丟進池塘,水波由中心向外擴散,形成許許多多距離不等的同心圓。人際關系,約略如此。而且,如果再加上一維變成立體,就更貼切生動:同樣的人,在不同的領域里,分布在距離不等的同心圓上。
以“差序格局”來總結華人社會的人際關系,有提綱挈領、畫龍點睛的精妙。然而,問題在于,費孝通點出了華人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什么”,卻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什么”,是哪些因素讓人際關系形成差序般的格局?因此,探討華人文化這個極其重要的環節,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只能算是起點。
費孝通的著作,廣為人知。可是,真正提出理論上解釋的,是近半個世紀之后的戴珍妮教授(Janet T.Landa)。她研究東南亞華僑的經商模式,發現一個有趣、想來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現象:華僑們會依自己的背景(漳州、泉州等),形成自己的人際網絡。買賣時,也就分成圈內人和圈外人。無論是賒欠、價格等等,圈內人和圈外人條件不同,圈內人要優渥一些。
戴教授的解釋,現在看來平凡無奇,幾乎只是常識。然而,在理論的發展上,卻有承先啟后的作用。她認為:在東南亞國家,華僑在當地經商,和圈內人買賣,萬一有糾紛,可以依恃鄉親故舊這種人際網絡,因此,風險較低,條件自然可以寬松一些。相形之下,和圈外人交易,萬一有了麻煩,沒有人際網絡,因此,風險大,當然要比較嚴格(苛刻)的條件自保。也就是,圈內人圈外人之分,隱含著不同程度的成本效益。換句話說,人際關系的性質和結構,可以由成本效益來解讀。
戴教授的個人經歷,也可以稍微插播一下。她出生在上海,于香港成長,美國留學后,結婚冠夫姓,在加拿大工作。近退休時回到上海,故國家園情懷,像打翻了的醋瓶子。她作英詩自遣:在外多年,現在和故國相連的,似乎就剩下名字里和熊貓的聯想( Landa,panda)!
由成本效益的角度,解釋華僑經商的模式,合于情理,順理成章。然而,畢竟這只是針對海外華僑,這種解讀能不能普遍適用于華人社會的人際網絡,并不十分清楚。眾所周知,華人社會里,“關系”重要無比。關系衍生出英文單字(guanxi),可見一斑。對于關系的討論,國際期刊里更是汗牛充棟,俯首可拾。華人普遍重視關系,大家耳熟能詳,是你知我知、無所不在的潛規則。可是,為什么在華人社會里,關系特別重要? 對于這個小哉問,卻少有探討。
幾千年的華人文化,經過早期的摸索之后,走上儒家文化的軌跡,從此一以貫之、路徑相依,為什么?
對于這個問題,簡單的答案,是和其他幾種主要思想比較。稍稍琢磨,答案自然浮現:法家,不容易成為主流,兩個明顯的理由。第一,地理幅員人口如此遼闊的帝國,操作一套嚴謹明確的法律,并不容易。第二,真的就法論法,皇室與庶民一致,不能持久,因為不符合統治者的利益。道家,強調順其自然,返璞歸真。可是,帝國的治理、特權的維護,都要靠源源不斷的稅收;無為而治,是自找麻煩,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墨家,強調非攻兼愛,愛人如己。這種游戲規則,在小范圍里也許行得通;對治理一個帝國而言,操作性不高,因為太不實際。
道家、法家和墨家,都各有明顯的弱點。相形之下,儒家以“仁”和“禮”為核心的思維,剛好有比較優勢。追根究底,“仁”和“禮”就是人際相處的游戲規則,強調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等等。這些道德上的戒律,合于人情世故,說服力強;而且,雖然性質上是觀念,也可以具體成為規定或戒律—落實為政府措施,就是公共政策;落實為行為規范,就是法令規章。在運用和解釋上,很有彈性。可以因地制宜,適合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大地。因此,儒家成為中華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是經過嘗試錯誤,慢慢形塑而成。環境條件使然,一旦走上這個軌跡,就是路經相依、長此以往。想起來似乎是偶然,其實幾乎是必然。
無論如何,儒家成為華人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可是,以儒家為脊梁的傳統華人社會,有幾點特質卻很少受到關注。一方面,傳統華人社會的政治結構,行政和司法合而為一。縣老爺既是父母官,又是青天大人。司法并沒有獨立運作的空間,而律令的解釋又有相當的彈性。另一方面,幾千年來,華人社會一直以農業為主,安土重遷,人口的流動性很低。在這兩種條件直接間接影響之下,華人的老祖宗們,就慢慢發展出自求多福的生存機制:家庭里靠倫常(孝道),家庭外靠關系(門道),也就是形成“倫常關系”的雙元軸線(filial piety-guanxi nexus)。換種描述方式:倫常,是家庭內的關系;關系,是家庭外的倫常。借著塑造和經營“倫常-關系”,進可以興利,退可以除弊。倫常(孝道)和關系(交情),表面上看起來是道德教化,其實不折不扣是工具性的安排(tool-like arrangement),具有功能性的內涵。
儒家,是傳統文化的主流;倫常和關系,是華人社會的特色。這些都是事實,爭議不大。然而,由哪些主要因素,塑造出這些文化上的特色,涉及千百年的歷史。對于歷史,可以揣測,可以試著解讀,但是離“事實”畢竟還有一段距離。相形之下,在現實社會中,也許反而能夠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來提供間接的證據,反映華人文化的特質。
因緣際會,我曾設計問卷,希望借著一些具體的事實,以小見大,勾勒出這三個華人社會的當代面貌。借著二十到三十個問題,針對有社會經驗的成年人,直接間接地測試關系在生活里的意義。測試問卷的內容,可以包含下列問題:
* 如果親人生病,必須住院,找醫院和病床時會不會通過人際關系?
* 開車違反交通規則,被開罰單,會不會通過關系,取消罰單?
* 去年春節時,自己有沒有送禮物給上司?
* 自己求學過程中,在高中階段,關于入學和就讀班級等事項,是否曾經通過請托、幫忙安排?
* 最近一個月內,在公共場所(例如: 地鐵上、馬路、商店內)有沒有看過陌生人吵架對罵?
人際關系很重要,對三個地區都成立。雖然沒有其他地區作為對照,但是由問卷的作答里,可望反映出這點特質。這是華人社會共同的特色,即使三地之間有諸多差異。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在內地、臺灣、香港三個地區之間,依次遞減。這個排序,和所得(經濟發展)的排序,剛好顛倒。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程度愈高,傳統關系的重要性愈逐漸下降。臺灣和內地比較相近,香港和兩者距離都遠。重視關系,是華人社會的特質。也許有區域性的差異,但是在各個區域里,重視關系、運用關系的程度相近,并沒有明顯的差距。
在香港和臺灣的測試結果,總結如下。由問卷的回答里,可以看出幾點共同性:
對于親人住院要找醫院和病床,“會”和“可能會”通過關系的比例,都超過60%(香港60%,臺灣73%)。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認為“關系”非常重要(香港58%,臺灣70%)。把“有點重要”和“非常重要”加在一起,都超過90%(香港97%,臺灣96%)。對于升遷,無論是公家單位或民間企業,也都認為“關系”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在香港和臺灣,關系在公家單位的重要性,都高過民間企業(香港67%>64%,臺灣70%>61%)。
差異部分。根據樣本,對香港和臺灣而言,關系都很重要。可是,兩地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
開車違規被開罰單,臺灣還有近1/3的人(26%)可能會托關系取消罰單,香港想這么做的人絕無僅有(0%)。到銀行申請貸款時,不會托人幫忙的比例,香港明顯高于臺灣(香港67%,臺灣48%)。春節時去探望師長的比例,香港明顯低于臺灣(香港27%,臺灣50%)。和五年前相比,認為“關系”重要性上升的,香港要遠低于臺灣(香港44%,臺灣91%)。預期五年后“關系”重要性上升的比例,兩地都很高(香港42%,臺灣52%)。但是,認為五年后和現在差不多的,香港要遠高于臺灣(香港45%,臺灣22%)。一般而言,香港的法治和專業水平都超過臺灣;依賴關系的程度,也因而低于臺灣。可是,公開場所吵架的現象,香港卻遠高于臺灣(香港61%,臺灣26%)。這個現象,巧妙地反映了“關系”的另一種內涵。香港有很多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也有很多外籍傭工,因此社會成員的異質性較高。在“非我族類”之間,就比較可能沖突摩擦。相形之下,臺灣社會的成員之間同構性較高,即使有沖突摩擦,通常也不會劍拔弩張地公開叫罵。
簡單總結一下,由香港和臺灣的測試里,可以發現:對這兩個華人社會而言,關系都很重要;但是,在程度上,臺灣重視關系的程度,要超過香港。這種結果,和文章里所做的推測,大致相符。
這篇文章的題目《有什么關系?》當然是有點文字游戲的雙關語。第一層意思最曉白:華人社會里,人際網絡有什么樣的特色?這是指關系“是什么”。第二層意義,稍微深刻一些: 華人社會的關系,重要性(relevance)如何?性質上,這還是在解釋關系“是什么”。第三層意義,要更幽微隱晦一些,但卻是本文的旨趣所在:在華人社會里,關系無所不在,是彼此心知肚明的潛規則,為什么?而且,希望追根溯源,由演化的角度提出解釋。
探索的軌跡,可以稍微回顧:以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為引子,聯結到戴珍妮的華商網絡。而后,由關系追溯到儒家思想,解釋儒家成為主流文化的可能原因。最后,再以儒家思想為參考坐標,指明這種主流文化落實到一般人的生活起居,會引發出哪些反應。“倫常—關系”的雙元結構,總結了這趟智識之旅的心得。當然,值得再次強調,引領帶路的,不是想當然爾的道德哲學,而是“拿證據來”的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