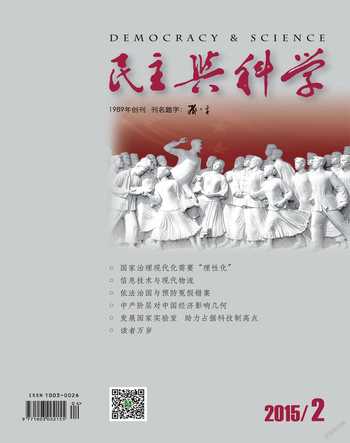吳大猷談通才教育
智效民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鴻溝由來已久,不僅制約了科學發展,也影響到社會進步。我原以為這是內地教育的一大失誤,最近讀《吳大猷文錄》(《大科學家文叢》之一,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才知道這個問題在臺灣和其他地區也出現過。所不同的是,由于吳大猷等人及時發現,才沒有釀成大錯。吳大猷是楊振寧、李政道的老師,他在海外工作多年,在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他的話也許有較大說服力。
在這本書中,吳大猷主要從三個方面談論這個問題。
一是針對人們對科學的錯誤理解,他說科學的要義是追求真理,科學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還包括智慧,“是‘知識和智慧’不可分的一體”。可見對于一個人來說,假如所受教育太狹窄太專門,那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斷個別的知識”,而不會通過了解科學全貌來增長智慧。這種人很可能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書簏,或者是一臺只會工作不會思考的機器。
二是針對人們過分看重實用的傾向,他告訴人們,科學家投身科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有用”,而是為了尋求真理。人類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都來源于純粹的求知,而不是為了實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臺灣社會,曾被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籠罩,許多人上大學不是為了求知,而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對這種傾向,吳大猷告誡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識的傳授”,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教育學生思考”。這一觀點對于糾正我們過于重視知識傳授的偏向非常重要。
三是隨著科技發展和經濟繁榮,人們的欲望也越來越高,這就使人類陷入一個貪婪的欲壑難填的漩渦之中。其中最明顯的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犯罪率不斷增高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有一個人文與科學合一的文明”來發展人類智慧,控制人類貪欲。他指出,要想讓人文與科技“融合起來,成為更高層次的一個文化,著重的是需要改變人類的教育,使習科技的不成為‘機器人’,習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質”。也就是說,當我們通過通才教育,兼備人文與科學的更高智慧時,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
說到通才教育,吳大猷和余英時在1983年的對話值得注意。在這次對話中,吳先生介紹了哈佛大學在1946年成立的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認為,科學發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術進步,而是一種根本性改革。要使人們對科學有基本了解,最好的辦法是借助通才教育。吳大猷說:“通才教育可使學生未來發展時,能有一種寬廣的基礎,使得念科學的人,也能了解、欣賞人文知識。同樣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對科學有清楚的了解,將來如果進入政府機構,在從事政府決定時,就可避免發生偏差。”
我注意到,早在1945年,哈佛大學的教授們就以《一個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為題,提出一個報告。這份報告是在反思戰爭、反思人類歷史教訓基礎上形成的。他們發現,多年來過分強調社會分工和專業教育,有抵消人類合作、增加社會沖突的可能,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乃至法西斯戰爭都由此而產生。這不僅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也對民主自由構成極大威脅。他們認為,自由社會必須由自由的人組成,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自動的個體,唯有充分尊重這個事實,人們才能獲得自由。基于這一認識,他們提出自由人格的產生有賴于普通教育的努力。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普通教育強調“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達。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會大大增加;不“通”,就無法獲得真正自由。因此通才教育又稱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在這次對話中,余英時也談到在臺灣和世界各地出現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與如今大陸面臨的困境極其相似。他說:“傳統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專業。現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會趨于專業化,個人必須有一技之長,職業才有保障。因此,哪些專長易于找到職業,大家便一擁而上。這種情形當然不限于臺灣,美國、蘇聯等地,亦復如此。例如,目前各國都有許多男女,紛紛學醫、法律與計算機。這純粹是一種以職業為主導的教育取向。這種取向,有予以自覺改變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不正常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見是:無論你學什么專業,都應該對專業以外學科具備必要常識。只有這樣,你“才有資格做一個完整的現代人,并具備綜合判斷的能力”。他認為,這些問題涉及到考試與教育制度,要徹底解決雖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應該做些努力和嘗試,“否則就會產生一種流弊,亦即造成一種所謂‘對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對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專家’。這種專家只有很狹隘的專業或純技術觀點,卻無法妥善處理專業以外的重要問題,甚至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些話對于那些過分迷信專家的人們,無異于當頭棒喝。
1984年,吳大猷還在臺灣《民生報》發表文章指出:臺灣初中生畢業后就必須作職業教育或考高中的選擇,這就不可能讓學生養成求知的興趣和習慣;至于大學的專業設置,也有過于狹窄的毛病。另外,整個社會對教育也有誤解,以為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工作,或以為大學應該對學生進行專才訓練,“這些皆是偏狹之見”。他說:大學的“學者和學生都有自由從事所選擇的學術”研究的權力,凡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應該擁有基礎知識和科學訓練。他認為通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養成廣泛的求知興趣和不斷學習的習慣。
不久,吳大猷還以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身份,在臺灣“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強調:由于“大學聯招”(類似大陸高考)存在的問題,使中學教育出現三大偏差:一是課程設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學業負擔太重。這就使大多數中學生在學習中只能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識的奧秘和科學的真諦,從而對科學喪失興趣。為了糾正這些偏差,吳大猷成立了“人文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組織相關教師培訓,以便進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7年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就準備成立一個原子能研究所,并提出吳大猷等9人是最佳人選。另外,吳的恩師饒毓泰是胡適的學生,胡適在臨終前給人們講過一個故事。他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這個故事告訴人們:中國曾經有一個相對自由的學統,它依靠通才教育培養出許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倘若不能恢復這個學統,不注重通才教育,我們就很難改變目前的落后狀況。
(作者為山西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