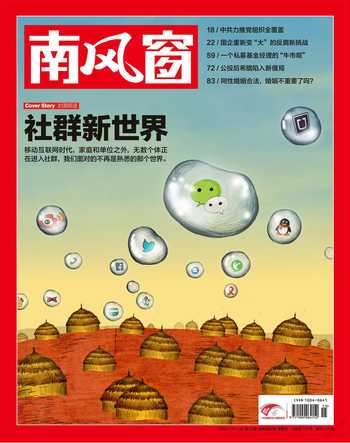當大危機來臨時
李桂文
過去兩周,正當中國火線救市力挽狂瀾的時候,另一個國家—希臘卻走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被搶購一空的超市、大門緊閉的銀行、缺醫少藥的醫院,一半的加油站已經“無油可加”。老百姓為了60歐元而在自動取款機前排長龍,而銀行的高管們正在商討是否將每日取款限額從60歐元降至20歐元……
7月5日,背負3200多億歐元巨額債務的希臘通過全民公決,否決了歐盟提出的金融拯救方案。這也意味著希臘老百姓生活的煎熬,還將繼續。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稱:“人民作了勇敢的決定,公決結果證明民主不會受到恐嚇。”
的確,過去數年希臘為換取國際援助而不斷勒緊褲腰帶,老百姓日子很難過,齊普拉斯領導的左派和進步聯盟黨一直反對財政緊縮,甚至揚言退出歐元區,民意支持率不斷攀升。2015年1月齊普拉斯贏得大選,取代“對外軟弱”的薩馬拉斯出任總理,誓言“首要任務是恢復希臘的尊嚴”。6月27日,大家正等著看希臘如何才能償還數天后到期的15.5億歐元IMF貸款時,齊普拉斯突然宣布就債權人所提的救助方案條款舉行全民公決,稱“債權人意在羞辱希臘人民,希臘必須作出民主的回應”。別忘了,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就是發軔于希臘。
看起來,公決結果確實是一場“民主的勝利”。沒錯,也可以讓希臘在與歐洲債主們的談判中增加談判籌碼。不過,無論希臘與歐盟最終達成什么樣的方案,這次公決充其量只能說是齊普拉斯個人的勝利。我們需要反思,當大危機來臨,領導者以民主的名義,把危機決策的權力交給民眾,是緩解了危機,還是加劇了危機?是民主的勝利,還是民主的悲劇?
容易被忽略的是,這次希臘全民公決的內容是“要不要接受歐盟的金融拯救方案”,并非“要不要退出歐元區”。雖然拒絕歐盟的方案會大大提高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但兩者顯然有著根本的不同。前者屬于政府應對危機的緊急決策,而后者則涉及希臘主權的范疇。從法理上講,全民公決的適用范圍應該是涉及國家主權的憲制安排,而不是應急的決策。可見,齊普拉斯本來也沒準備讓希臘人民來決定什么,他只是希望他們成為談判桌上的籌碼。
希臘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學者劉鶴的一項研究成果可以提供一種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在研究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后得出結論: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對決策者來說,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解決起來既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往往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
政客們既不愿意下臺,也不愿意承擔責任,改變來得更加艱難。
所以,這不是什么“民主的勝利”,而是一場民主的危機。政治學者趙鼎新研究發現,民主體制會強化原有分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次希臘公決中,雖然反對票高達61%,但別忘了還有近四成的支持者。顯然,中上層社會傾向于接受,而底層社會傾向于說不。對歐盟方案的態度迥異反映了希臘階層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公決結果加劇了他們的分裂和對抗。
直接民主對社會的撕裂可能會引發更深的災難。現代社會不再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在這個脆弱、復雜、多元的世界里,物質技術發達的表象潛伏著更多不確定性。一個角落里的小事件,都可能會成為蝴蝶的翅膀,引發巨大的嚴重后果。而當大危機來臨時,個體的公民根本無法從容作出選擇,每個人都是一種應急反應,更多是一種情感的宣泄。用哈佛大學丹尼·羅德里克教授的話來說,這時候人們的“原始沖動和憤怒壓倒了理性的經濟成本收益分析”。趙鼎新也認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由于國家對社會輿論和政治議題的控制,選民在對外政策上根本沒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的選擇。把危機決策付諸公決,放大了民主體制的缺陷,驅使整個社會走向極端。對社會的撕裂,會使大危機的解決變得不可能,甚至造成秩序的混亂、顛覆。因為對于底層民眾而言,現在已經如此艱難,最壞的后果不過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正在本文收尾的時候,經過半個月暴跌的中國股市迎來了站穩翻紅的時刻,政府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的措施效果開始顯現。盡管之前市場監管問題備受詬病,但當危機來臨,中國政府的果斷應對給市場以信心,讓人印象深刻。
當大危機來臨時,一個可問責、敢擔當的強政府,才是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