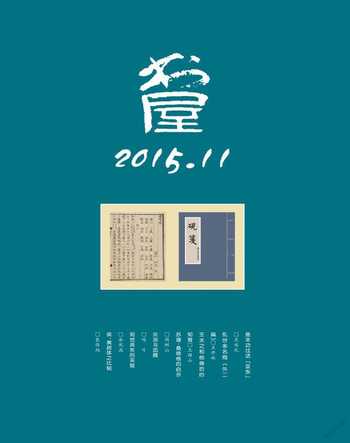哲學的慰藉
張祚臣
世界上的書籍如恒河沙數,拋去那些爛書不說,好書也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讓讀者狂喜,讓作者沮喪,讓人狂喜是因為讀者可以說,我終于等到一本好書了,讓人沮喪是因為對于打算寫書的人來說,一本經典之作,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企及;還有一類書讓讀者狂喜,也讓作者狂喜,前者的理由如前所述,后者則讓寫作的人松了一口氣,哦,原來書還可以這樣寫。
《哲學的慰藉》就屬于后一類書。再看作者阿蘭·德波頓,英國人,生于1969年,原來并非花白胡子的老學究,而是同屬六十年代的“我輩中人”,這些因素均指向一個恰當的心理暗示:或許我也可以試試。
當然,《哲學的慰藉》一書吸引我的首先是譯者資中筠,這位大學里主修英美文學、以國際政治等宏大主題研究為業的前輩大姐,也常常為公共事務發言,這次能為這種生活哲學類“小書”附身翻譯,想必該書一定有不同凡響之處。
阿蘭·德波頓在《哲學的慰藉》中選取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六位哲學家作為敘述的主體。誠然,正如書名所言,作者選取的哲學家和他們的哲學意在對生活的慰藉作用,其實哲學的作用不僅僅在于慰藉,更大的作用可能是智慧,是看待世界及其人生的總體目光。
在希臘語的詞根中,哲學正是由愛和智慧組合而成。
一
蘇格拉底一章的標題是:“對與世不合的慰藉”。或許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蘇格拉底飲鳩事件對世人有警示和慰藉作用。但是作者卻沒有觸及蘇格拉底哲學的核心,在我看來,蘇格拉底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對智慧和知識不可抑止的追求,在日復一日、無禮冒失地與雅典人的談話中,蘇格拉底發展出了一種叫做辯證法的東西,他在各種習以為常的流行觀念中,發現了它們的可笑和錯誤之處,以至于當時的人看見蘇格拉底走來就趕緊躲開,甚至有些人恨不得殺了他。
德行與知識的關系也一直貫穿于蘇格拉底的倫理之中。蘇格拉底認為智慧是最大的善。他并不認為知識是不可企及的,關鍵的恰恰在于我們應當努力尋求知識。善就是知識,一個人之所以愚蠢只是在于他缺乏知識。只要他去認識,就不會愚蠢。惡的一個壓倒一切的原因是無知。因此,要達到善,我們必須具有知識。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只有二十四萬人,從城市的一頭皮雷埃夫斯步行到另一頭埃基厄斯城門大約一小時。全城有投票權的男性公民大約三萬人,這就是雅典直接民主制的背景。在三萬男性公民中又選出五百公民組成陪審團,就是這五百人決定了蘇格拉底的生死,投票結果是二百八十人認定蘇格拉底有罪,二百二十人認為無罪。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尚處于多神崇拜階段,還沒有建立嚴密的宗教體系,蘇格拉底圣徒般的行為從何而來?只能來自于哲學,來自于理性與邏輯的推理力量,事實上,哲學正是智者的宗教。
蘇格拉底最后的演講曲終奏雅,他說:“如果你們處死我,將很難再找到我這樣的人。”事實上,他把自己看做是雅典古城這匹良馬身上的牛虻,他甚至預言,雅典人最終會同他一樣看問題,那些主張處死他的人很快就會后悔。
事實確實如此,哲學家死后不久,公眾的情緒就開始轉變,歐里庇得斯的戲劇《帕拉米德》上演時,蘇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現,觀眾就哭了。雅典人對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絕與他們共浴,在社交場合排擠他們,最后他們在絕望中自縊身亡。
二
發生在公元65年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加死亡事件頗有點像464年前蘇格拉底之死的情景再現。割破手腕,血流并不通暢,又割破了腳腕和膝蓋,塞內加要求醫生給他一碗毒藥,事實上,他長久以來一直以蘇格拉底為榜樣,毒藥還是沒有起多大作用,他最后要求把他放進蒸汽浴室,在那里慢慢窒息至死。
然而,蘇格拉底之死和塞內加之死卻有不同的含義,前者源于哲學的信仰,后者卻仿佛命運之神打了個盹又突然醒來。在塞內加看來,死亡是偶然中的必然,不能因為命運女神長時期的發慈悲而麻痹我們的危險,他要求我們每天花一點時間想她,“汝生而終有一死,汝所生者亦終有一死,一切都應在考慮之內,一切都應在預料之中”。
當羅馬皇帝尼祿處死老師塞內加的命令傳來,親友們都大驚失色,哭了起來。由于斯多葛派的哲學態度,哲學家不動聲色,努力勸他們止淚,并從容地問道:“你們的哲學哪里去了?”
塞內加恰當地說出了哲學的慰藉作用,所以這一章叫做“對受挫折的慰藉”。塞內加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他曾是羅馬朝廷的重臣,曾經貴為皇帝尼祿的老師,作為斯多葛派哲學家,盡管他鄙視財富,可是塞內加卻積累了巨量財富,據羅素說有三億塞斯特斯之多,約合美元一千二百萬,據說他大部分財富都是在不列顛放貸而來。
然而當他進入政界想要大顯身手的時候,卻被梅薩利女王流放科西嘉島八年,當他被召回羅馬朝廷的時候,不得不接受一個險惡的任務——當阿格麗品娜十二歲的兒子的導師,此人就是后來的羅馬暴帝尼祿,就是他在十五年后下令塞內加在他的妻子和全家面前自殺。
據說最初聽到皇帝的決定時,塞內加準備寫一篇遺囑,人們告訴他已經沒有時間容許他寫長篇大論了,這時候他轉身向他憂傷的家人說:“你們不必難過,我給你們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財富更有價值得多的東西,我留下了一個有德的生活的典范。”
古代的哲學家總是思考德行與善這類倫理問題,斯多葛派認為德行才是唯一的善,像健康、幸福、財產這些東西甚至都是微不足道的。
三
出生于公元前341年的伊壁鳩魯則聲稱:“如果我把口腹之樂、性愛之歡、悅耳之娛、見窈窕倩影而柔情蕩漾,一概擯棄,那我將無法設想善為何物。”
在伊壁鳩魯看來,最大的善是快樂,沒有快樂,善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伊壁鳩魯在后世賺得了一個享樂主義的名聲,其實這可能是一個極大的誤解。
伊壁鳩魯的快樂既包括肉體的快樂,也包括精神的快樂,肉體的快樂大部分是強加于我們的,而心靈的快樂在于對身體快樂的沉思,按照這個觀點,有德性的人在追求快樂的時候應該是小心謹慎的。
伊壁鳩魯的快樂觀是審慎的,更多的是一種消極的快樂。積極的快樂是在對匱乏事物的追求中體驗到的,而消極的快樂能在沒有任何欲求的情況下達到。伊壁鳩魯的快樂觀恰恰是說明真正的快樂可能對于物質的依賴十分有限,當財富超過了一定限度,快樂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這一章的標題是“對缺少錢財的慰藉”。
在伊壁鳩魯的快樂清單中,根本沒有錢財的一席之地。在他開列的清單中,第一是朋友,然后緊跟著的是自由和思想。事實上,伊壁鳩魯在離雅典市中心的幾公里處,在集市與港口之間找到了一所大房子,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搬了進去。據后來的史料記載,同他住在一起的有作家梅特多魯斯和他的妹妹,數學家波利埃努、埃馬爾庫斯、雷奧修及及其妻子泰米斯塔,還有一名商人,名叫伊多門紐。這所大宅子有足夠的房間,朋友們有各自的住房,還有共同就餐、集會和談話的廳堂。
他說,除非有人看見我們存在,我們就是不存在的;在有人能懂得我們的話之前,我們說什么都沒有意義;經常有朋友圍繞身旁,我們才能確認自我;朋友知我、關心我,構成一種力量,讓我們不至陷入麻木之中。
他們在住宅旁又買了一座大園子,種了卷心菜、洋蔥還有某種古老的菊宇之類的蔬菜。他們的食譜既不奢侈,也不豐盛,但是有味道、有營養。他們開始一種公社之類的生活,以簡單換取獨立,以儉樸換取自由。
在園中思考受到鼓舞,據說梅特多魯斯一個人就寫了十二本書。可以想見,在那所大宅的廳堂和菜園里,有著不受干擾的機會同既有智慧又善解人意的人們研究問題,他們常常分析金錢、疾病、死亡和鬼神帶給人們的焦慮。伊壁鳩魯的理論是,如果能合乎理性地思考生命有限的問題,就會意識到人終有一死:“對于真正懂得不活著沒有什么可怕的人來說,生命中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事了。”
四
蒙田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性情古怪的老頭,總是穿著馬褲,圍著文藝復興時期特有的褶皺領。實際上蒙田從三十五歲繼承了家族的產業——一座莊園,一些仆從和牲畜,當然更重要的是城堡一角那座塔樓的三層樓上的圓形圖書館——他便一頭扎進那座書齋,過起了隱居生活。他把隱居生活看作是暮年的開始。
書齋有三扇窗,毫無遮攔地把法蘭西的美景盡收眼底,此外還有桌一張,椅一把,書千卷。就是在這里,蒙田穿越中世紀的藩籬與古典對接,他通過拉丁文的柏拉圖文本讀到了蘇格拉底向雅典陪審團所作的堅定不移的講話;通過拉爾修的《生平》和盧克萊修的《自然頌》讀到了伊壁鳩魯的快樂觀;也讀到了1557年新版的塞內加的作品。
他也閱讀同時代人關于美洲新大陸的記敘。在蒙田出生前的四十一年,哥倫布達到了佛羅里達灣的巴哈馬群島中的一個小島。這些歷史書、旅行日記、傳教士和船長的報告、異域文學,穿著奇裝異服的部族吃著不知名的魚的圖畫集,幫助他克服偏見,獲得深刻而寬容的思想體驗。
這一章的標題是“對缺陷的慰藉”,其中的一節叫做“文化的缺陷”,在我看來簡直是文化人類學的早期顯現。不知道基督的美洲人跟我們的生活是如此不同:他們喜歡吃蜘蛛、蚱蜢、螞蟻、蜥蜴和蝙蝠;新娘可以在婚禮日縱欲狂歡,男人和男人結婚;把死人煮熟,剁成醬用酒拌了,在祭神的集會上由他們的親屬吃下去;有的國家女人站著小便而男人蹲著。
巴西的圖比族人赤身裸體猶如在伊甸園,當歐洲人送給他們衣服的時候,他們咯咯笑著拒絕了;他們一見到河就跳下去,有時候一天洗十二次澡;他們好客,每當村子里來了陌生人,婦女都要掩面哭喊:“你好嗎?你大老遠來看我們,辛苦了!”;男人可以娶不止一個妻子,而且對每一個都非常鐘愛。
我想,蒙田是信奉蘇格拉底的善惡觀的,善就是知識,如果人類以寬容的態度對待自己所不理解的異族文化,南美殖民者的大部分罪惡是可以避免的。他的博學、睿智以及這些龐雜的知識都寫在他那三卷本的《蒙田隨筆全集》里了。查理·索雷爾稱這部作品是“宮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書”。孟德斯鳩說:“在大多數作品中,我看到了寫書的人;而在這一本書中,我卻看到了一個思想者。”
五
作為英國的隨筆作家,德波頓的敘述除了無可爭議的古典哲學家外,沒有選擇近世的英國哲學家,而是選了兩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和尼采。或許是個人偏好,或許是因為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具有零碎的、試驗的、反體系的性格,用羅素的話說,這一切“使歐洲大陸人極感惱火”。
叔本華和尼采都是悲觀主義哲學的代表。
叔本華說:“我的一生可視為一段無用之插頁,是對我長眠于‘無’之極樂境界的干擾。”“人的存在是一種錯誤,可以說今天很壞,一天比一天壞,直到最壞的事出現。”正如先輩塞內加所說:“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人生都催人淚下!”
看來古今哲學家看待人生的態度都差不多,只不過沒有人像叔本華這樣傷心,一事一景都可能勾起其內心的絕望情緒,所以這一章叫做“對傷心的慰藉”。他把此岸世界看做是魔鬼的作品,它把眾生帶到這個世上就是為看著他們受難而取樂的。所以叔本華求助于東方的神秘主義。
在叔本華的世界里,根本就沒有什么是善的東西,人的意志都是惡的,所以必須像佛陀那樣修行,當意志麻木了,才使我們達到涅槃或虛無,從而獲得解脫。神秘的入定,使我們看穿了代表幻覺的“摩耶”之紗,因而可以視世界為一體,從而戰勝意志。
尼采的哲學卻直面人生的悲苦。他認為大多數的哲學家是“卷心菜頭腦”,“我是第一個像樣的人”,他甚至略帶尷尬的承認“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將被宣布為圣靈”。他認為叔本華的哲學“像膽小的麋鹿一樣躲藏在森林里”,是怯懦、脆弱的和女性化的,實際上尼采一生看不起女性,他號召人們去找女人時,別忘了帶上自己的鞭子。
尼采把悲劇看作是通向“超人”的必由之路,所以這一章的作用在于“困難中的慰藉”。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過避免痛苦,而是通過承認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經的步驟而達到的。在尼采那里,直面痛苦就是善的,強烈的意志是善人的突出特征,而在叔本華那里,意志是萬惡之源。
盡管尼采不能為后來的獨裁者負責,但是他所推崇的健康、強壯、高貴的“超人”性格,卻成為歐陸“英雄的暴行”(羅素語)的思想淵源。在1889年他打算刺殺德國皇帝,策劃一場反猶主義的戰爭,他越來越肯定自己是酒神、耶穌、天主、拿破侖、意大利國王、佛、亞歷山大大帝、凱撒、伏爾泰、亞歷山大·赫爾岑和理查德·瓦格納。他被運到一家瘋人院,在那里呆了十一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