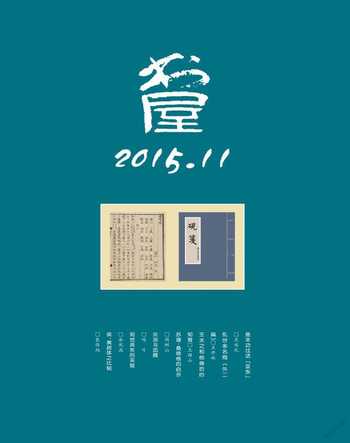1946:胡適辭謝祀孔陪祭官
肖伊緋
孔子是春秋時期的著名教育家,被尊為“至圣先師”,他的誕生日,被稱之為“孔誕”,歷代都有祭祀典禮。但孔子誕生的確切日期,卻歷來都有爭議。崔東壁在《洙泗考信錄》中曾做過考證,據《春秋谷梁傳》定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為今之8月21日;《孔庭纂要》則說是8月27日。此外還有公歷的10月9日、10月3日等等各種說法。
中國古代祭孔,大都以每年農歷八月二十七作為孔子誕辰。民國期間,官方就曾定每年農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誕紀念日,又把這一天定為教師節,祭孔與教師節放假都在同一天。之后又把農歷的孔誕日期換算為公歷的9月28日,固定為這一天進行紀念,也為人們所接受。
抗戰勝利后,北平的首次孔誕祭祀典禮,卻定于1946年8月27日。這是徑直將農歷日期挪到公歷上來用,根本沒有任何換算。為什么會這么草率行事,或者說為什么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誰也說不清楚。時任北平市長的熊斌還自任主祭官,并在當年的8月21日就向公眾發布了孔誕祭典的訊息。北平《世界日報》報道稱:“祀孔典禮定于二十七日上午七時于孔廟舉行,主祭官熊市長熊斌,陪祭官為本市紳耆,該日各機關、學校團體均放假一天。”
到了8月24日,祀孔典禮還進行了預演彩排,媒體記者立即進行了跟蹤采訪與報道。次日,北平《世界日報》在“教育界”欄目頭條發布“重磅消息”,稱新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辭謝了此次祀孔典禮的陪祭官。報道原文如下:
(本報訊)二十七日祀孔典禮,昨下午四時,先在孔廟大成殿舉進演習,到熊斌、張伯鰲、湯永成、汪崇信、左宸綸等數十人。祭樂由國樂團營所全體學生擔任。歷二小時,演習完畢。正式內禮,主祭及陪祭官均將一律著長袍黑馬褂,其中多數系本人臨時制備,每套工料,約有十五萬至二十萬元。陪祭官中,原有北大校長胡適之,但胡昨已婉辭,謂回平未久,校務太忙,不能參加。外間推測,以胡在五四時代,曾以“打倒孔家店”號召青年,此種典禮,就胡氏學術思想立場言,自無參加可能,當局以胡名列入陪祭,或當時偶欠思考。
8月26日,祀孔典禮正式舉行前一天,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又去采訪胡適,想進一步證實他辭謝陪祭官的真實態度。次日,即祀孔典禮正式舉行當天,這篇訪談簡訊被刊登在了該報頭版,足見當時北平公眾對胡適缺席祀孔典禮的關注度。報道摘錄如下:
(本報特訊)本報記者訪北大校長胡適,首詢二十七日祀孔典禮,外傳胡辭陪祀官是否事實。胡謂,確已辭謝,并得熊市長同意。惟胡謂孔子為世界最偉大思想家之一,其誕辰值得紀念,不過宗教儀式,非彼所喜。胡并告記者,去年倫敦世界教育會議,彼曾提議,一九四九年,為孔子二千五百年誕辰,希望下次大會,能在中國召開以紀念此偉大教育家。
看來,胡適確已辭去祀孔陪祭官,當天的祀孔典禮上確實不會出現了。但胡適之所以辭謝,并非記者想象的“打倒孔家店”的立場使然。事實上,“打倒孔家店”這一說法,根本就不是胡適所提出的,它的發明權應歸屬于四川人吳虞(1872—1949)。吳虞是“五四運動”前后涌現出來的反孔急先鋒式的人物,“打倒孔家店”與“禮教吃人”等口號都曾是他的獨家發明。吳虞曾于1919年某日拜訪胡適,當時胡適正在閱讀《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這一章,因此在談話中胡適就隨口說了“打孔家店”這么一句話。此話一經吳虞傳出,胡適原來脫口而出的“打孔家店”就變作了“打倒孔家店”這樣的更鋒芒畢露的口號了。
姑且不論,“打孔家店”與“打倒孔家店”在詞義上有著怎樣的微妙差異,也不論胡適隨口一提、并非深思熟慮的偶然性,只需稍稍讀一下1935年胡適所撰長篇論文《說儒》,他對孔子其人其學的基本態度,就可以一目了然。該文中,他不但考察了“儒家”的歷史,而且提出了“孔子的大貢獻”這一命題。可見,無論從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孔子,還是從人格的眼光來考量孔子,胡適得出的結論,都是正面的、積極的評判。
至于為什么辭謝祀孔陪祭官,胡適也說得相當明白,他認為宗教儀式化的紀念方式,他不喜歡也難以接受。因為他早就宣稱過自己是“無神論者”,任何神化歷史人物的行為,他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實際上,以人格力量、歷史貢獻來看待孔子,是包括胡適、林語堂、梁啟超、魯迅等在內的諸多同時代學者的共同取向,也是民國學者人格獨立、學術自由之自然表現。
此外,胡適被采訪中提到的,他曾于1945年的倫敦世界教育會議上提議,在孔誕二千五百年時,在中國舉辦世界教育會議,以為紀念之事,確有其事。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因為1949年的孔誕二千五百年紀念日,無論是按農歷計算,還是按公歷換算,胡適及國民黨政府都不可能再行操辦任何慶典及會議了。此刻,國民黨政府業已潰逃至臺灣,而胡適則只得飛赴美國暫寓,再也沒能回到祖國大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