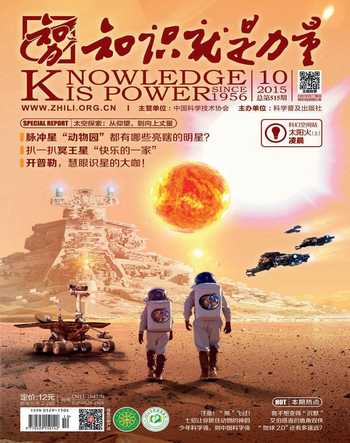科幻名家給孩子們的“悄悄話”
房寧 黃慶 彭婕 劉亞南 胡青梅 薛燕男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與劉慈欣、周文武貝等科普科幻界人士座談。李源潮認真聽取了大家的發言后講,對美好未來的想象是人類進步的精神動力。科學幻想因其源于現實生活、激發新奇發現、放飛自由想象,對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科普科幻創作肩負著展現中國夢的時代責任,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努力點燃青少年科學夢想,激發全民族實現中國夢的想象力創造力。要堅持科學性、藝術性、思想性相統一,既超人超物超史,又合情合理合法,把科學幻想與人類情思、社會理想融為一體,增強全社會實現中國夢的理想信念。
《小靈通漫游未來》
就在今年8月,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斬獲素有“科幻界的諾貝爾”之譽的雨果獎,為中國科幻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科幻是青少年讀者獲取知識、激發興趣的一片重要園地,而讀者年輕化正是中國科幻發展的巨大優勢與空間。為此,《知識就是力量》雜志特別邀請到10位著名科幻人士,與青少年朋友共同分享他們對科幻的感悟。
1. 您是如何走上科幻文學的創作道路的?哪些科幻作品對您影響頗深?如果有孩子想學著寫科幻,您有什么建議?
葉永烈:在寫作《小靈通漫游未來》前,那還是1959年年初,19歲的我正在北京大學化學系上二年級。當時,我剛剛走上科普創作道路,編寫了第一本科普書稿《科學珍聞三百條》,從各大報刊及國外雜志中收集了許多科技新成就,然而羅列科技新聞太枯燥、太乏味,遭到退稿。這本書雖然沒有出版,但是為了寫這本書,使我熟悉了許多當時的科技新成就、新動態。1959年暑假,我寫出了化學小品集《碳的一家》,受到出版社的歡迎,并接著應邀參加《十萬個為什么》的寫作,我的寫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為了克服《科學珍聞三百條》一書的缺點,我決定把它寫成一本科學幻想小說。我設定了一位耳聰目明的小記者——小靈通,到未來市進行一番漫游,報道種種未來的新科學、新技術。通過這樣穿針引線,把一條條孤立的科學珍聞,像一粒粒珍珠串在了一起。講每條科學珍聞時,我不是直接講,而是通過形象化的幻想故事來寫。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小靈通先后再版18次。我總結這本書之所以經久不衰,還是歸功于當時以“大孩子”的童心寫作,貼合孩子的接受程度和興趣點,對各個領域的科學知識進行全景式展現。而且由于科普書稿的編輯經驗以及偏愛童話書的閱讀興趣,使我在講故事的同時知識基底也非常過硬,對這本書的問世非常有幫助。
科幻電影《銀河系漫游指南》
劉慈欣:科幻小說中各種科學設想的構建,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要產生一個設定,然后用某些推理方式,把這種設定向前推導,不斷推翻重來,直到推導出很震撼很有意思的故事,那就能寫出來,這是我創作科幻小說的基本過程。說起來容易,但實際上,這是很艱難很緩慢的過程。并不是說只要努力,就會有寫作的創意和靈感。我喜歡宏大敘事,喜歡像《戰爭與和平》那樣全景式地推進,就像克拉克的經典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游》的最后一章,10億年時間百億光年空間在作家筆下揮就,主流文學所囊括的世界和歷史瞬間變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
要進行科幻創作,就必須要有科幻的思維方式。首先,科幻作家要對宇宙的宏大有一種敬畏感,渴望用有想象力的觸角,來超出有限的生活,觸摸那些我們無法觸及的那些很遙遠、很偉大的存在。在時間上,你可以用想象力去觸摸過去和未來,有這樣強烈的欲望,這種渴望的思維方式,我覺得這種狀態,就是科幻創作的一個精神基礎。有了這樣的精神基礎,才能談得上別的方面。
王晉康:我開始科幻創作大體有三個原因,一是偶然的原因,兒子喜歡聽故事,我就想給兒子講點故事,也因此創作了我的處女作《亞當回歸》,結果獲得了1993年全國科幻征文的首獎,漸漸地,我就走上了科幻文學的創作之路。但任何成功都沒有巧合,這部作品之所以能一擊即中,深層次的原因還是我對科學的深厚情結,從小我就非常注重感受科學的震撼力,感受大自然中蘊含著的非常精巧的秩序,我把這種對科學偉力的領悟融入我的科幻小說創作之中。另外,我對文學比較喜愛,上大學的時候也練過筆,大量閱讀過國內外的文學小說,這對于我的科幻創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夏笳:我生活在理工科氛圍的家庭中,在父母的影響下我從小就愛科學,小時候讀物特別少,而《十萬個為什么》是當時為數不多且寓教于樂的科普讀物,我就抱著反復讀,從而記住了葉永烈這個名字。后來,我知道葉永烈還寫科幻,就慢慢讀起了科幻,從他又讀到鄭文光。打開了科幻這扇大門,我漸漸愛上科幻,能找到的科幻雜志書刊都被我收集來……長大了一些,我也開始嘗試編寫一些故事,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踏上了科幻創作的道路。
我相信,每個孩子天生都有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在我小時候,閱讀就像“吃字”一樣,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娛樂。然而時代不同,現在的孩子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有太多信息需要獲取,這些信息又良莠不齊,因此優秀的兒童科幻作品更顯其可貴。
《校園三劍客》系列之《吃人電視機》
2. 您認為孩子們應該如何學習科學知識,怎樣從科幻中汲取科學養分?科幻對孩子最大的幫助在哪里?
吳巖:科幻對孩子們最主要的貢獻是滿足孩子的夢想。每個孩子都有對未來世界的向往,科幻會告訴你未來是怎么樣的;每個孩子都喜歡夢想,喜歡點石成金的魔術,科幻可以將那些神奇的畫面展現出來。
王晉康:我認為科幻對孩子的影響大體說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一些比較“硬”的科幻會使孩子在閱讀過程中積累大量的科學知識、科學背景,能讓孩子潛移默化地接觸科學。另一方面,經常接觸科幻的孩子,從小就化解了對科學的疏離感,樹立起對科學的愛,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由于這樣的興趣存在,對孩子將來的影響可能很大,比如有學生說過:“我就因為喜歡看《三體》,我才愛上學物理。”
周文武貝:在我所從事的科幻電影事業中,有許多科幻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會使青少年對很多科學現象及其內在原理產生興趣,進而去研究,從這一層面上說,科幻電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促進孩子學習科學的動力。而對于科幻作品的創作,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想象力,孩子們的想象力非常豐富,廣大中小學生可以盡情釋放,結合互聯網時代的新興事物和元素,在這個知識結構下發揮想象,創作出一些嶄新的作品。
張之路:我認為一個人在學習科學的時候,不但要學習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鍛煉一種科學的思維。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好的科幻作品就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想象是有力量的,想象力就是一種創造力!對于想走上科幻創作道路的青少年,我建議要理解和注意科學和文學的關系,科幻作品既要寫科學,也要寫人,要記住科學也是美麗的。
3. 您認為哪些科幻題材較為適合孩子看?怎樣的科幻作品更符合兒童科幻市場的定位?
楊鵬:現在的科幻市場上,適合孩子看的科幻小說還是比較少,家長們還是要根據孩子的興趣點,找一些淺顯易懂、符合孩子心理的兒童科幻書,以此來做啟蒙,我現在就主要在做這件事,針對孩子的口味創作一些易讀易懂的科幻讀物。
神奇的科幻世界
當然,如果不了解兒童科幻市場,就不可能寫出兒童喜歡的讀物,寫出來也不會暢銷,所以有的時候,科幻作家要充分考察、把脈市場走向,有可能比研究科幻的專家還要了解科幻的前沿趨勢。創作《校園三劍客》時,我仔細考察了小學中高年級兒童的閱讀需求:他們渴望主動閱讀,渴望扮演的不再是受教者而是能夠參與和改變社會的主人;渴望他們中間出現英雄,出現他們自己的偶像;渴望超越現實。因此,我的《校園三劍客》和孩子們的這些渴望高度契合。
對于兒童科幻作品,我覺得是有一定的標準的,第一,是孩子喜歡,適合孩子讀,所以我堅持讀者本位的思想;第二,要能激發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不能寫老生常談的東西;第三,還是要堅持科學精神,不要有科學上的硬傷,不要有知識點的馬虎、過時或者錯誤;第四,一定要有文學性,有文學性的東西,才有靈性,才是活著的文字。
近年來,我一直在將自己的科幻作品推向產業化,就以《校園三劍客》系列作品為例。在我寫《校園三劍客》的時候,還是個大學生,沒有想得那么長遠,但那時就已經開始了對科幻產業化的學習研究,隨著《校園三劍客》的影響越來越大,產業化的條件越來越成熟,我的作品就慢慢開始走上了除圖書發行外,兼有動畫片、舞臺劇、廣播劇、微電影、漫畫改編的全方位開發之路。
4. 很多科幻故事最后都變成了現實,您覺得科幻可以預測未來嗎?
夏笳:科幻可以“預測未來”,且特別有志于把故事放在未來視野中敘寫。然而,預測準確并不是它的目標,其本身的思考過程才是最有價值的,不僅是那些被事實驗證的才凸顯其價值,有些被證明特別離譜的預測,也常常包含特別有趣的東西。雖然說現在有許多未來學家在積極地預測未來,然而未來是充滿變數的,不可計算的,預測未來本身是一種思想試驗,獲得一個思考的樂趣是最重要的。比如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他預測的彈道角度、著落地點都和后來的火箭發射非常相似,然而他預測的大炮發射是美中不足的,但他并不是因為犯了錯誤或者知識不夠才預測失誤,而是一方面考慮當時讀者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是對當時軍事俱樂部濫用大炮的諷刺,他用最有趣的載體展現他想要表達的思想內容,這是文學作品與科學論文的不同之處。因此,科幻可以“預測未來”,但并不是預測對了才是好科幻。
劉興詩:我認為真正科學性很強的科幻作品,是具有預見性的。我是學地質學出身的,曾考察過七八百個洞穴,其中涉及很多地下瀑布,我的第一篇科幻作品《地下水電站》(1961年)講的就是利用地下瀑布建設水力發電站的故事。我的另一篇作品《北方的云》(1962年)是國內最早的氣象科幻作品。這篇文章中提到的渾善達克沙漠是離北京最近的沙漠,我當時就預測它的起沙有可能對北京造成影響,會產生霧霾。
楊鵬:我認為科幻作家談不上能預測未來,只不過比別人多了解一點知識,比如我在寫電腦科幻的時候,那時好多人還不知道互聯網,不知道電腦是干什么用的,而科幻作家可能只是掌握了比較前沿的科學資料,這是科幻作家預測未來的一個基本點。由于現代科技比較發達,給我們留出的預測未來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像一百多年前的科幻作家,很多預測都變成了現實,那是因為他們把想象力與科學結合在一起,大膽地運用邏輯思維進行推理,預測出冷凍術、潛艇等五花八門的科學技術。總的來說,我覺得科幻作家“預測”未來主要是基于兩點:一是占有資料、信息,站在別的科學家高瞻遠矚的基礎上預測;二是要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嚴謹的科學態度。
5. 作為一名資深科幻編輯,您怎么篩選適合讀者口味的科幻讀物?
姚海軍:從專業的角度來說,科幻編輯篩選出的讀物要在自己的喜好和讀者的喜好之間盡量找到一個平衡點,更多地以讀者能夠接受的、喜聞樂見的作品為主。科幻讀物的篩選大概有三個標準:第一,一定是一個好故事;第二,要有一些原創的想象成分存在;第三,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讀完科幻作品一定要能引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