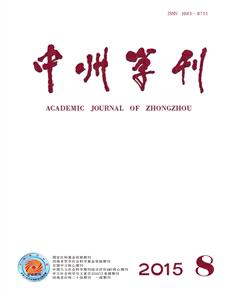古代“孝道”的社會化、政治化對當前道德建設的啟迪*
王四達 孫力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各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派生出一些消極現象,如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滑坡。早在改革初見成效但問題初露時,小平同志就憂心忡忡地指出:“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①為此,中央曾先后推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加強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等重要舉措,但由于所提倡的內容較空泛,與民眾的生活結合不緊密,故多年來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習近平指出:要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②要弘揚傳統美德,就必須使之符合人性、貼近生活、易于普及,而“孝道”就具有這樣的特點。古人所謂“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百善孝為先”等,即精準地揭示了“孝”在道德教化中的優先性與基礎性。甚至可以說,古人的“以德治國”是以“孝治天下”為前提的。因此,以家庭為載體,以孝道為抓手,借鑒古代把孝道文化社會化、政治化的成功經驗,也許可以成為推動道德建設、凈化社會風氣的突破口。
一、古代“孝道”文化及其社會化、政治化
一般而言,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形成的文化系統,必定有一個能使該民族維持內部穩定有序的基本價值,是一種能把社會控制內在化的思想工具。這種價值與工具又必定有它在特定環境中發育的生成邏輯。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宗法-政治型社會,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政治型文化。筆者認為,如果把“仁”作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概念的話,那么“孝”的觀念就是扎根在宗法社會土壤中原初的文化基因。因為與后起的“仁”相比較而言,“孝”畢竟是先在的文化元素,它源于氏族社會中天然的血緣親情,其中已包含著親對子的愛與教育及子對親的敬與依賴。由于“孝”具有內在的凝聚力與外在的輻射力,所以在氏族社會向國家演進的過程中,“孝”就成為從親情倫理走向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的邏輯起點。美國學者赫斯科維茨認為,一個民族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可以視為該民族的文化焦點,也是該文化討論最多的問題。“孝”可以說就是古人討論最多的問題。漢代大儒揚雄在《法言·孝至》中說:“孝至矣夫!一言而該,圣人不加焉。”“孝”被強調到兼該(包容)百行,連圣人對此也無以復加的地步。從這一點上說,它又是傳統中國的文化焦點。
所謂”孝道”,是從“孝弟”(通“悌”)兩種親情倫理發展而來的尊親敬長等善德的通稱。朱熹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親親”即是血緣親情最直接的體現。而在親情中又以父母兄弟最親,因此,孝親順兄就成為社會推崇的美德。從文獻上看,這一親情倫理可上溯至堯舜時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尚書·堯典》稱帝堯“克諧以孝”,帝舜“以孝烝烝”,命司徒“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③。在圣王看來,如果人人皆能做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便能實現家“內平”而國“外成”。可見古人很早就懂得良好的家庭倫理可以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到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成為孝文化最有力的倡導者。《論語》對“孝”的解釋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奉養。“事父母,能竭其力”,且“唯其疾之憂”。二是恭敬。《論語·為政》曰:“今謂之孝,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但“敬”還是有是非的,《孝經·諫諍章》指出,“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三是“慎終”“追遠”。《論語·學而》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與“孝”密切相關的是“弟”(悌)的兄弟倫理,“孝”與“弟”共同構成家庭教育的內容及個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基礎。對“孝弟”在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基礎作用,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孝弟”被置于諸行之先。有子則進一步把“孝弟”強調為“仁之本”,如果一個人從小能行“孝弟”,凡事專注于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孔子之后,孟子對“孝弟”的認識又進一步深化,他敏銳地看到,“孝弟”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之中。《孟子·盡心上》稱:“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由于“孝弟”以人性為基,又是仁義之本,因此它可以推廣到父兄輩及一切年長者身上。《禮記·曲禮上》曰:“年長以輩,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雖說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仁”是比“孝”更根本的核心概念,但由于“仁”的內在精神是“愛人”,《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最初的“愛人”便是“愛親”。《孝經·天子章》引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因此,只要把“愛親”“敬親”之心擴展開來,“愛人”就在其中了。以這種“愛人”精神為基礎,還可以借助社會倫理培育政治倫理,成為國家推行道德教化的重要工具。《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由此,古人構筑了一個以“愛”為起點、“孝”為核心的社會倫理系統,它“孝于父”“慈于子”“尊于師”“敬于長”“順于兄”“友于弟”“恕于友”“慈于幼”“忠于公”(后來漸被扭曲為“忠于君”)。它既貫穿在各種人倫關系之中,又滲透到政治生活之中,所以朝廷有“以孝治天下”之宣示,杜甫亦有“孝理敦國政”之主張。對此,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倫理學史》中有一個總結性的闡述:“人之全德為仁,仁之基本為愛,愛之源泉在于親子之間,而尤以愛親之情發于孩提者為最早。故孔子以孝道統攝諸行……則一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得統攝于其中矣!”④于是家庭倫理就擴張為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這就是“孝道”的社會化和政治化。通過這樣的過程,“孝道”已演變為全民族的集體意識,無形中對其他價值觀起到整合、協調的作用,由此推動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系統發育。可以說孝道是個綱,綱舉目張。
所謂“社會化”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通常是指人從“自然人”轉化為“社會人”的過程,即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通過對社會文化的學習與角色知識的認同逐漸適應社會的過程,也是基本人格的培養過程。從個人的角度說,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社會化”才能使外在的社會規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標準。從社會的角度說,通過對社會成員的文化熏染,既可使主流價值觀獲得認同,又可使文化傳統得以積累和延續,社會結構亦得以維持和發展。應該承認,古人在推廣“孝道”文化的社會化這一點上是有戰略思維的,它以父權為工具,以孝弟為價值,利用從小的家庭教育和上一輩人的示范作用(如孩子天天看到父親孝順爺爺),對孩子進行“潤物細無聲”的孝道教育;孩子讀書知禮進入社會后,又接受圣人之書的熏陶和社會主流文化的影響,會激發他們的道德欲望,使他們自覺進行價值內化,以符合社會的期望;成家立業后他們同樣以自己認同的這套價值觀教育子女。這就實現了文化的代際傳遞,而同時國家也達到了政治穩定的目的。因此,社會化客觀上兼有政治化的作用。
“政治化”也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其實質是“政治的社會化”。就“面”而言,它是某種政治價值、政治秩序、政治制度被社會接受的過程;就“點”而言,它是個人認識所處社會的政治秩序、制度并接受和適應其秩序、制度的過程。通過社會化和政治化過程,個人才能成為被該社會認可的合格社會成員,而“孝道”則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紐帶作用。孟德斯鳩曾敏銳地指出,中華帝國是以治家為基礎的,“中國的立法者們認為帝國的太平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他們看來,服從是維持太平最適宜的方法。從此種思想出發,他們認為應該鼓勵人們孝敬父母,他們并且集中所有力量,讓人們恪遵孝道”,而“尊敬父親就自然包括尊敬所有可以視同父親的人物,如老人、師傅、官吏、皇帝等”,“一個兒媳婦是不是每天早晨為婆婆盡這樣那樣的義務,此事的自身是無關緊要的。可是假如我們想到,這些日常的習慣不斷喚起一種必須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感情,并且正是由于人人均具有此種感情才構成了這一帝國的統治精神”。⑤通過日常生活持久地潛移默化,“孝道”就由社會化發展為政治化,成為古代政治秩序最堅實的社會基礎。而這種社會基礎與政治秩序的一致是超越王朝政治變遷的,不管歷史上如何改朝換代,“孝道”作為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都是不變的。所謂古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并不在于哪個王朝能千秋萬代,而在于數千年倫理秩序的持久穩定。
二、傳統“孝道”文化的現代價值新審視
當然,如果從現代眼光來看,古代“孝道”文化也有其歷史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鼓吹“家無二尊”,導致對宗法家長專制的維護,使子女喪失了個人的獨立性;二是宣揚“移孝于忠”,導致對政治家長制的強化,使臣民成為愚忠的犧牲品。因此,清末民初以來,“孝道”文化與家長制受到啟蒙思想家的猛烈批判。應該說,在當時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這些批判確有進步意義,但也存在矯枉過正之弊。即使如孫文、黃興等革命者,也看到了傳統道德的價值。孫中山曾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道德規范,重新賦予其新時代的新內容。黃興也批評那種以為提倡新道德就必須否定舊道德的謬論,他說:“夫以孝悌忠信為戒,則必不孝不悌不忠不信,自相殘殺而后可。以禮義廉恥為病,則必無禮無義無廉無恥,論為禽獸而后可。循是以往,將見背父棄母,認為自由;逾法蔑紀,視為平等;政令不行,倫理喪盡。家且不齊,國于何有?孟子所謂猛獸洪水之害,實無逾此。”⑥遺憾的是,新中國建立后傳統文化再次被全盤否定,孝文化也被“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的“領袖愛”“階級愛”所取代,結果造成人性的扭曲與虛偽。但“文革”結束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應該說在今天的中國,家長專制的宗法土壤與帝王專制的政治結構均已解體,并不存在這兩種專制復辟的危險,經過揚棄,傳統文化中那些優秀成分完全可以“古為今用”。恩格斯曾批評近代歐洲“對中世紀殘余的斗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沒有看到它的成就,“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⑦其實,中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悠久燦爛,更需要接續古今之間的“偉大歷史聯系”,只有這樣,時代性與民族性才不會脫節,新文化建設才具有民族心理的依托。因此,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號召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而在這一點上,孝文化具有不可否認的現代價值,它可以成為重建傳統道德、形成家庭美德、培育個人品德、推及職業道德、惠及社會公德的最佳起點。
1.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們接受
《詩經·小雅·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覆我,出入腹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中感念父母生養我們的辛勞,他們細心照顧呵護我們,出入都把我們抱在懷中。若沒有父母,我們就沒有依靠。父母之恩如天無窮,不知何以為報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世間最偉大的,兒女對父母的感恩之情也最真誠。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任何政治說教所無法比擬的,只有這種天倫之愛能在所有人心中激起強烈的共鳴。例如,康有為雖然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急先鋒,但他仍非常推崇孝道,他說:“父母之勞,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體由其育也,勤勞顧后,子乃熟也。少喪父母則饑寒困苦,終身賤辱。普天之下,計恩論德,豈有比哉?”⑧所以古人有“孝子愛日”之言,稱孝子最能珍惜與父母共處的日子,只為能及時行孝,以免父母歿后抱憾終生。在社會高度流動的今天,“孝子愛日”更具現實意義。從一曲《常回家看看》風靡全國,到每年的春運返鄉大軍,反映出人們對回家團聚的執著,表明親情與孝心仍存在于出外謀生的人們心中,由此可見,古代的孝道文化在現代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2.孝道是善良的種子,它的生根開花必定會結出道德的果實
由于愛親萌生于幼兒心田,這就把道德教育前置到孩提時代,它會對人一生的品德產生良好影響。一個有孝心的人必定對自己的行為格外慎重。《禮記·祭義》曰:“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一個孝子如能時刻謹記所作所為不能辱沒父母,這既是對自己的警誡,又是對自己的激勵。所以《禮記·祭義》又稱:“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能讓國人對自己有這樣的夸贊,就是對父母生前最大的褒獎。即使父母歿后,“孝親”的自我警誡與激勵仍須始終如一,既要“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又要“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于是,在孝的陶冶下,個人品德和職業道德皆得到淬煉。《禮記·祭義》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這就是由孝生發的道德力量。古人甚至強調連仁、義、禮、信等道德亦由此(孝)而起:“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⑨——順此將得樂,反此可犯刑,這種忠言對治療當前中國社會的“官腐民敗”仍具有警醒之效。
3.孝道是一種永恒的價值,它的升華可成就無私的博愛
孝道雖是一種源于親情的私德,但它卻是公德的源頭活水。蔡元培先生認為,私德不健全,即難有健全之公德。孝道作為“仁之方”,最可貴的就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愛父母可以生發出愛他人、愛自然、愛生我養我的故土故國,愛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的情感。《禮記·祭義》曰:“大孝不匱。”所謂“不匱”就是“博施、備物”,即把這種博愛源源不斷地施于萬物。“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古人對此的注解是:“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由愛親之心而推之,則雖一物之微,有不可不愛者,而況其大焉者乎?”⑩可見愛心可以由小及大,由近及遠:對父母的孝心和對家的責任,可以轉化為對他人的愛和對社會的責任,擴大為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岳母刺字”“精忠報國”,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均表明中華民族的孝道經過升華可以成為一種“民胞物與”、充塞天地的大愛。所以《禮記·祭義》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于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它能否成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準則姑且不論,但它確有能“施于后世”的永恒價值,因為它所包含的博愛精神即使在今天也并不過時。
三、古代“孝治天下”的戰略對當前道德建設的啟示
不可否認,現代中國社會與古代宗法-政治社會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孝弟”的親情倫理比“忠君”的政治倫理更具有超時空的特性,它并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消失。“孝”文化雖然存在若干歷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繼承。這正是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例如,古代帝王推崇孝道當然是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秩序,如果我們撇開這個政治目的不說,把孝道的推廣看作古代的社會道德建設,那么其整體化的戰略思維和人性化的貫徹手法還是非常有效的。今天我們同樣面臨著如何有效地推進思想道德建設的問題,古人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就特別具有啟示意義。
1.社會化與政治化巧妙結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戰略設計
任何一個社會想要穩定并延續下去,都必須力求使它的成員盡可能地在基本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上趨于一致,用主流的信念來引導人們的思想,用統一的規范來約束人們的行動,以便塑造合格的“公民”(古代則為“臣民”)。塑造過程包括價值施化與價值內化兩個方面:價值施化一般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完成的;價值內化一般是通過個人道德修養完成的,因為個人為了有效地適應社會,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用家庭和社會的期待來塑造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升華,所謂“理想人格”就是這樣煉成的。除了在具體內容上有所差別外,上述社會化的過程古今并無不同。
然而,“孝道”的社會化與政治化又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社會化是政治化的基礎。《禮記·哀公問》引孔子言:“愛與敬,其為政之本與?”“愛與敬”雖然是為政之本,但它們卻是借助社會化扎根的。另一方面,政治化又是社會化的目的。所謂“孝治天下”,表明“孝”只是手段,“治天下”才是目的。馬克思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1]所謂主流價值觀,通常就是官方倡導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既體現現實政治的需要,又以家庭、社會為依托。《大學》有言:“其為父母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謂治國在齊家。”《孟子·離婁上》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就是貫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價值,也是社會化與政治化的現實載體。清末維新派思想家文廷式稱:“古代圣帝明王皆以孝為教,而政輔之以孝,故不必假于鬼神之吉兇,而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此中國政教合一之大端也。”[12]把“教”與“政”建立在人性親情的基礎上而不必用鬼神來威懾恐嚇,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性的體現。于是,古人通過這樣的戰略設計實現了孝道的社會化與政治化的無縫對接,也為“以德治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2.“倡”與“導”同時并舉,是古代推廣“孝道”的戰術舉措
“倡”雖偏于宣傳,但它起到樹立價值坐標的作用。《孝經·三才章》引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被提到“天經地義”的高度,這便是官方推崇的價值坐標,故須“導”民力行之。“導”則側重貫徹落實,只有倡導有方才能收到實踐這些價值觀的效果。總的來說,古人倡導孝道的做法主要有三方面:官方制度建設、君子以身作則、民間教化配合。
官方制度建設主要是通過禮樂制度來推廣孝道。《孝經·廣要道》指出:“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記·內則》從“禮”的角度對孝道做了許多具體的規定,如在家里,“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左右佩用”,“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在外頭,“見父之執(“父執”謂父之朋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13]在社會各領域,比如在朝堂上、在行路中、在鄉村里、在狩獵時、在軍旅間當如何尊長敬老,規定得非常細。對此,《禮記》的結論是:“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意為“眾人以孝弟為所宜行,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14]。
君子以身作則要求精英們皆應率民以孝。《孝經·三才》指出:“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所謂“師尹”泛指朝廷官員,他們的所作所為民眾都看著呢。《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這種榜樣作用可產生社會效應,所以古人說“愛敬之道,既立于此,則愛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以感化之也”[15]。《大學》所謂“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民間教化配合則發揮耳濡目染、“習以性成”的作用。古人很早就懂得“習以性成”的道理,認為人之生性會因長期的習慣而養成:它既可以因習善而養成善性,也可能因習惡而助長惡性。《尚書·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以性成。”而政與教就是“習以性成”的決定因素。《荀子·大略》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后行。”據史書記載,為了加強孝弟的教化作用,周時即在朝廷設“三老”“五更”之官。所謂“老”“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16]所以古人有“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說,因為培養尊老敬長之風可以帶動孝弟之道。秦漢以來,朝廷又把“三老”“五更”設到縣與鄉,使之掌鄉民教化。《漢書·高帝紀上》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置為三老,鄉一人。”又設“孝弟”鄉官,其職責是勸導鄉里,以助成風化。由于措施得力,教化有方,民間尊老敬老亦蔚然成風。以“鄉飲酒禮”為例,《禮記·鄉飲酒義》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豆,古代食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白居易《策項》曾曰:“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程頤《四箴》則說:“習與性成,圣賢同歸。”要做到“圣賢同歸”也許不現實,但在民間推行一些切實的教化措施并持之以恒,必定能收到移風易俗的良好效果,其道理即使在現代也不例外。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中國當前已有“壞基”之虞,特別需要以國基養護為務。平心而論,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并非不重視道德建設,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從“五講四美三熱愛”“四有新人”,到“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八榮八恥”,再到最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內容并無不對,但社會道德狀況仍無明顯好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官方的政治“天話”不接民眾的生活“地氣”,難以引起民眾情感上的共鳴;二是道德目標泛泛羅列且不斷變換,既缺乏頭緒也缺乏一個現實的抓手;三是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缺乏相應的同步改良,使健康的社會意識無法在不良的社會存在中順利生長。在這三方面古代“孝道”文化均對我們今天的道德建設有所啟迪。
首先,一種文化價值觀只有貼近人性,源于情感,才能深入人心并成為構建社會道德的基礎。古人看到孝道乃人之天性,天性之理可順而不可逆,如果舍棄基層的親情倫理,忽視中層的社會倫理,上層的政治倫理必然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故歷代帝王皆不遺余力地倡導孝道,并沒有把政治倫理凌駕于親情倫理之上,甚至不惜允許“親親相隱”來維護社會基礎價值,這當然不會引起民眾的暗中抵制或虛偽以對。
其次,道德本質上是一種心靈結構,該結構的道德品質有層次性的邏輯關聯。在古人那里,“孝”就是這個心靈結構中的邏輯起點。孔子以孝道統攝諸行,孟子指出“孝弟”植根于人天賦的“良知良能”,圣賢對各種德行的內在邏輯、主次先后,皆梳理得清清楚楚。古人關于孝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的論斷是很有見識的,其道德教育以孝為抓手,再循序漸進地培育君子人格,也是切實可行的。
最后,一種道德之所以能夠扎根,必須有適宜的社會土壤。古代也曾因惡政而產生周期性的“官逼民反”,但由于孝道扎根于血緣親情的社會土壤中,政治生態變壞并未導致民間“孝弟”之風喪失,所以即使改朝換代,新王朝也無須進行道德價值的重建。而現在由于缺乏扎根于民間的道德基礎,所以當社會存在惡化時,我們應致力于社會生態與社會意識的同步改善,而“孝道”即是一個最適合的突破口。古代以“孝治天下”作為“以德治國”的基礎條件是很富有創見的。
注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頁。②參見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③崔愛芝、宋鵬主編:《世界通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第3頁。④高平叔編:《蔡元培哲學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頁。⑤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中華書局,2006年,第209頁。⑥《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94頁。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頁。⑧康有為:《大同書》,中華書局,2012年,第175頁。⑨[13]《四書五經》,線裝書局,2007年,第160、99頁。⑩[14][16]孫希旦注:《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1227、1227、576頁。[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頁。[12][15]吳楓主編:《中華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2、3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