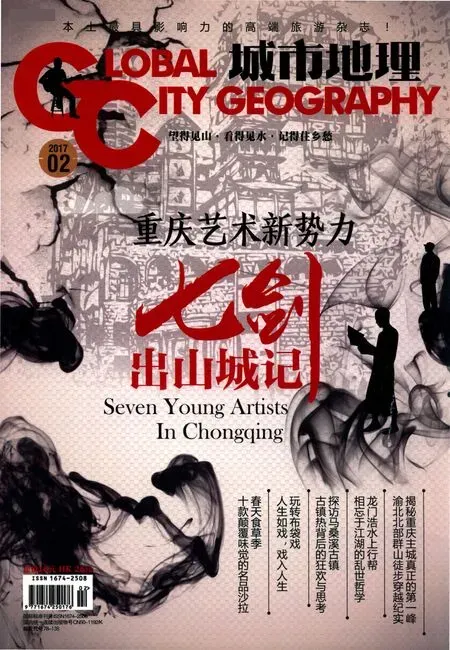歐洲的涂鴉
——對于景觀互動性的一點啟示
王笑石
(北京林業大學,北京 100015)
行走在歐洲,隨處可見涂鴉,城市的大街小巷,墻壁上、燈柱上、扶手上、垃圾桶上、甚至是樹干上,色彩斑斕,水平參差,形式各異。絕對讓國內“辦證人士”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到此一游”的作者也一定會自慚形穢。我不禁對自小被灌輸的歐洲人素質高這樣的定論產生猶疑,原來“亂寫亂畫,損壞公物”不是國人的專利,而是世界人民的“通病”。于是乎,決意研究此“病”根源所在,并試圖提出解決辦法。
1.問題的發現
意大利的龐貝古城,慕尼黑的英國園,杜伊斯堡北部風景公園,阿姆斯特丹的花街,蓬皮杜藝術中心廣場……大小名勝,各種環境,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無論是自然風景園還是工業遺存改造,無論是市民的公園還是后現代藝術廣場,一律平等,滿目皆是。一路走一路看不禁一路思索,游人為什么偏愛在公共場所或名勝古跡涂鴉呢,人們是出于什么心態做這件事的呢,想來此事是一定有共性的,一定有原始訴求的。由于甚是在意,疑竇叢生。于是,每到一個地方定會關注此事。如此,便有了以外的收貨,在魏瑪古城,這個問題特別突出。還有幾個地方:蓋爾森基興的北極星公園,波茨坦的無憂宮,法國的拉維萊特公園,三個風格迥異,毫不相干的地方卻幾乎沒有見到。

圖1 魏瑪古城

圖2 龐貝古城
2.專業角度的人性化分析
思慮至此,我暫時得到了一個僅從景觀建筑學這個專業角度出發尚欠推敲的論斷,此事必和景觀建筑的互動性也就是公眾參與度有關。
以龐貝古城為例,它是歷史遺存古跡,近乎廢墟,斷壁殘垣之屬,游客只能穿梭于破磚亂瓦之中,游客中心及相關服務設施都在古城之外,景區內沒有任何使我們與這幾千年前的場所建立聯系的媒介,也沒有休憩停留的場所。但人是社會性動物,不止要和人本身交流還有要和場所建立聯系的欲望,小狗每到一個地方必撒尿以示領土所有權,連懶到極致的考拉君也會分泌物質用肚臍在桉樹上蹭一下,說“這棵樹我來過是我喜歡的”。人雖是高級靈長類,也不過是“直立的無毛兩足動物”而已,所以與場所建立聯系是必然的,只是手段有所不同。
人類是怎么干的呢,“我在哪哪哪吃了什么,見了什么,遇到了什么,而且我干了什么”這個而且后面的“干了什么”必是深入的交流互動。因此,到了這種無交流媒介的地方,只能勉為其難的“到此一游”,或是摳塊石頭帶片磚,還冒著機場安檢的風險。

圖3 北極星公園手繪墻
柏林墻景區這點做的就很好,一塊殘墻,用透明的有機玻璃做了保護的避雨棚,并配套做了實物、舊照片、舊文件的展覽,有文字和語音講解,有合理流暢的游覽路線,有配合廣場做的可休憩景觀,在旁邊的紀念品商店和小咖啡館有非常豐富的周邊產品,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種可以帶走的一小塊殘墻(仿制)的明信片,這簡直是把互動性做到了極致。
北極星公園是工業遺存改造的公園,結合自身性質,專門預留殘墻給大家涂鴉,涂累了還可以直接躺大草坪上和朋友野餐,真是暢快淋漓。而慕尼黑的英國園除了草坪就是樹,還有一條水渠,讓人怎能不在樹干和點景小建筑的墻壁上做文章呢,同樣是大草坪不見人聚會或休憩遛狗的倒是有幾個。董豫贛先生曾經說過“奶牛才會只對大草坪充滿熱情”。從前不明此句要詣,現在想來“只”字是關鍵。這樣大的一個公
園卻寂寂無人,也不無道理。無憂宮呢,雖是古典園林,但做了非常多很有意思的服務設施,讓人們在了解歷史,游賞園林的同時,感覺仿佛在不斷的變換場景下追逐嬉戲發現探索更美麗的所在,誰還會圍繞著一棵樹冥思苦想要刻什么字好呢?
法國的拉維萊特更是把互動融合發揮到了極致,參數化設計的紅色鋼鐵小房子,在不同的區域依據游人的需要變換著自己的造型與功能。無論老人還是孩子,無論你來自哪里信仰什么宗教,總能找到你游玩的樂趣,休憩的地點,冥想的空間。人與環境就這樣通過服務設施的人性化設計和景觀的互動型設計,自然而然的融合在了一起。
3.啟示
最近幾年,風景區建設如火如荼,各個城市爭做花園城市,古鎮村落不是被嚴重破壞就是過度商業化。這是一個“過”和“不及”之間如何抉擇的問題。想來,可以在保護遺產和環境的的基礎上,在環境行為學的指導下,通過增強景觀的互動性,增強城市景觀和風景區的親和力,來改善和提高游覽者的體驗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