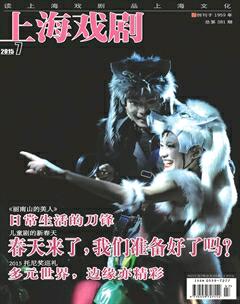春天來了,我們準備好了嗎?
趙瓊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之初,中國兒童劇市場便穩步增長,規模不斷擴大,去年更呈現出明顯的繁榮局面。道略演藝產業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2015中國商業演出票房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兒童劇演出高達10377場,這是國內兒童劇演出首次突破萬場大關;總票房達3.26億元,觀眾數量479.8萬人次,僅次于話劇。至此,一直被認為處于邊緣地帶的兒童劇以強大的市場潛力躍入了人們的視野,加上生育政策的逐漸放開,兒童消費群體將迅速擴大——兒童劇的春天來了,商機帶來了演出市場的繁榮,然而這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深思和反省。
演 出:收獲頗豐,有待拓展
從專業演出來看,整體演出質量良莠不齊,難以一概而論,國立的兒童劇院因人才和資金等諸多原因相對制作精良,且有意識地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從劇目內容來看,仍偏向于故事劇場,以講好故事為準繩。在其他藝術形式的借鑒上更傾向于音樂劇,多媒體的引入也成為賣點,受到青睞。經典童話改編仍然占據很大份額,原創系數較低,大多缺乏形式上的表現力,但自去年以來原創劇目的比重有增長的趨勢,開始關注當代兒童文學作品,從中汲取養分。比如中福會兒童藝術劇院就著力扶持原創劇目:《蝴蝶之舞》試圖拓展兒童劇的深度和內涵,擺脫常人認為兒童劇一味淺顯的偏見;《小八臘子流浪記》展現了老上海的面貌和風情,令人眼前一亮;還有規模宏大的《森林運動會》和簡短靈活的《小魔盒》,都在不同程度上嘗試了新形式的探索。
在劇目引進方面,近年來力度相當大,除了官方交流外,民間力量也迅速崛起。比如引進頂尖兒童“微劇場”的“小不點大視界”,由媽媽和寶寶一起看戲選戲,在演出同時開設工作坊和大師班,建立起了兒童劇引進的良性模式。在引進的劇目中,家長比較偏愛已有一定閱讀基礎的兒童劇,比如根據艾瑞克·卡爾的圖畫書改編的黑光劇《好餓好餓的毛毛蟲》去年10月上演時一票難求,今夏再度來滬,提前三個月便開始搶票。此外,劇目制作中的國際合作也日益頻繁,形式多樣化。比如武漢人民藝術劇院根據著名童話《尼爾斯騎鵝歷險記》改編的兒童音樂劇就屬于中英聯合制作,他們請來《悲慘世界》的編曲,可謂大手筆,曾于今年3月在上海文化廣場演出;又比如易劇場推出的瑞典兒童劇《小屁孩的煩惱》,此劇由上海戲劇學院的博士Maja翻譯和導演,由中國和瑞典演員共同演繹,既做商演也做公益演出。
從發展趨勢看,在劇目內容和形式的拓展上還有很大空間,兒童劇場不必拘泥于故事傳統,其先鋒性有待被認識和深入挖掘;兒童劇場與音樂、舞蹈、肢體、偶和雜技的結合也存在多種可能性,需要不懈探索。除專業兒童劇團外,成熟而優秀的成人劇團也可以嘗試為兒童創作,為兒童劇行業輸入新鮮的觀念,相互激勵和啟發。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市場為導向使得一線城市的演出頻率明顯居多,二線城市緊隨其后,天津戲劇市場的火熱對兒童劇發展也有助益,上海周邊城市如杭州也逐步形成以動漫產業為特色的兒童劇市場,然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則發展非常緩慢,那里的兒童同樣有權力觀看演出,這需要政策的傾斜和扶持以及良性的公益演出模式的建立。
觀 眾:學齡前兒童為主,嬰幼兒和青少年劇場缺乏
過去兒童劇由學校包場組織集體觀摩,進入市場后,大量學齡前兒童成為觀眾主體,為數眾多的8-18歲的青少年看不到兒童劇,審美教育嚴重缺失。這一狀況持續至今,由于觀眾的低齡化影響到創作,為小學生和初中生演出的劇目嚴重缺失,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導致難以吸引青少年進入劇場的狀況。除此之外,0-2歲的寶寶也完全可以觀看演出,不過適合他們的劇場具有特殊性,在國外較為普及,而在國內還鮮為人知。廣義上的兒童劇場應包括0-18歲的兒童,涵蓋嬰幼兒劇場和青少年劇場,這兩者的缺失無論對創作、研究,還是兒童劇場的整體發展都十分不利。
可喜的是這一缺失正開始得到彌補。今年5月來自立陶宛的肢體劇《翻滾吧,寶貝!》在上海兒童藝術劇場演出,這是我國引進的第一出嬰幼兒劇場;8月即將演出的法國形體戲劇《媽媽,我從哪里來》也屬于嬰幼兒劇場。6月的懸疑木偶劇《會說話的大房子》則是針對12歲以上的青少年觀眾。
以上是兒童劇以及兒童觀眾的狀況。對家長而言,如何在兒童劇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僅作為孩子的陪伴者,也能作為平等的觀眾欣賞演出,這需要成人觀眾和創作者們的共同努力。兒童劇在照顧兒童觀眾需求的同時,不要忘記他們的父母可能正坐在邊上,也要為他們寫點什么。如今的家長群體多為70或80后,文化層次較高,教育理念新,在孩子成長上也舍得投入,爭取他們的支持和理解十分必要。此外,由于目前劇作質量參差不齊,網絡信息鋪天蓋地,家長和孩子該如何選擇自己真正想看的兒童劇,還需要專業指導和建議。看完戲后,家長該如何與孩子討論劇場,也有待進一步思考和嘗試。
戲劇節:培養原創人才的平臺
暑假來臨,上海兩年一度的國際兒童戲劇節也拉開帷幕。兒童戲劇節的舉辦讓孩子不出國門就能欣賞到優秀劇目,豐富了假期生活,其價值是毋容置疑的,但舉辦戲劇節的目的不僅限于此。戲劇節應該不僅是看戲之所,也是藝術家、觀眾、研究者之間相互交流的平臺。國外的戲劇節往往集中在一兩周內舉行,所有的藝術家歡聚一堂,相互觀戲切磋并大量交流,也會有他國戲劇節的藝術總監來物色合適的劇目。而我國主要的兒童戲劇節(以上海和北京為例)都是以售票演出為主,只有周末演出,劇目分散。這樣藝術家之間交流的機會少,且演出主要提供給當地觀眾,因為外地人員不可能每周末抽出時間前往。當然這種舉辦形式與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和觀念有密切關系,一時難以改變,但仍要看到其局限性并尋求問題的解決。
作為綜合性劇場藝術活動的兒童戲劇節如果只提供演出,花大錢把優秀劇團請來演幾場就走了,不免可惜。真正成功的戲劇節應能夠培養起中國兒童劇的原創力量,吸引有志于從事相關領域的人才,提供機會讓他們向藝術家學習。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戲劇節應該成為一所最好的學校,舉辦戲劇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和發展我們自己的兒童劇事業,不僅要培養觀眾,也要培養我們的創作、研究和管理人才。
除了專門的兒童戲劇節之外,一些有口碑的戲劇節也會引進老少皆宜的劇目,這是很值得鼓勵的。比如愛丁堡戲劇節的《LEO》(翻譯為《反轉地心引力》)就適合大人和小孩一起看,其足跡遍及南京、杭州、成都、貴陽、武漢等地,這類劇目往往自成一格,奪人眼球,為兒童劇場的多樣化體驗拓展空間。
學生劇場:成果卓然,如火如荼
在學生演劇方面,主要分為校內和校外兩大系統。作為現代戲劇發源地的上海,本身就具有非常深厚的學生演劇傳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每年都會舉辦學生戲劇節,中學生話劇節至今已辦3屆,大學生話劇節已辦11屆,這些活動培養起了校園戲劇的熱情,加強了學生之間的戲劇交流。
尤其要提及的是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作為教育劇場的試點基地,她們率先在高中開設了戲劇課,重金打造小禮堂為小劇場,由語文老師和美術老師合作組建劇團,聘請新加坡富有經驗的戲劇導演來給學生排練。去年她們演出《小王子》,今年兒童節上演了根據郭寶昆的代表作改編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前者純情唯美、詩意盎然,后者情感熾烈飽滿,發人深省,均為學生劇場的上乘之作。校外的學生劇場以少年宮為主導,浦東新區少年宮的張忱婷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導演的兒童音樂劇《多杰》由一群藏族兒童演出,彰顯出屬于孩子的昂揚而鮮活的生命力。
研 究:遠遠落后于實踐
學術研究是兒童劇場發展的重要組成,是實踐創作的引領和指導,然而相較于藝術實踐,我國對兒童劇場的理論研究非常薄弱。目前為止出版的有關兒童劇藝術的個人理論專著只有四本,分別為《兒童劇散論》(程式如,1994)、《兒童戲劇藝術的魅力》(李涵,1997)、《中國兒童劇導演藝術論——暨中小學演劇活動參考手冊》(徐薇,2008)、《任德耀與上海兒童劇創作》(許敏,2014),無一本為基礎理論。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著名戲劇家和特定劇種兩方面,著名戲劇家又多聚焦于黎錦暉和任德耀兩人。史學方面較重要的著作為《中國兒童戲劇史》,尚無專門的地域史和斷代史。由此可見,兒童劇場的已有理論較為零散,不成體系,劇評和感性經驗居多,基礎理論非常匱乏,核心概念混亂,理論體系尚未建構。理論匱乏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專業的研究人員、缺乏研究工具和方法、缺乏研究的宏觀視角、本土意識和國際視野、戲劇土壤的缺失和戲劇觀眾培養過程緩慢。同時兒童劇研究沒有自己專門的發表園地,這也是研究凋零的一大原因。雖然有些劇院設有內部刊物,但可以公開發表,擁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刊物是理論研究的命脈,是研究者賴以交流的平臺。
熱切期望能有更多人來關心和支持中國的兒童劇場,更多的藝術家和研究者參與其中,為兒童創作和求索;更多的媒體記者和編輯關注兒童劇的發展動向,為兒童劇專業論文和評論的發表提供機會;更多的民間和公益劇團發展自己的特色,形成兒童劇演出的不同層次、面向和梯隊;更多的制作方和管理團隊提供成熟的商業和市場運作模式;更多的父母和教師認識到兒童劇場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到兒童劇場的建構中來,從而使得更多的孩子們能夠有機會走進劇場,獲得愉快而富有意義的觀戲體驗。當然我們也需要國家和政府更多的扶持,以及更多的民間投資者的介入。正如戲劇是一門綜合藝術,劇場的實現歸根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兒童劇場的發展壯大也迫切需要眾人的參與和協力。中國兒童劇場發展路漫漫,曲折艱辛,但前景廣闊。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天華學院講師,上海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博士。該文為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ZZTH12016;應用型本科建設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Y1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