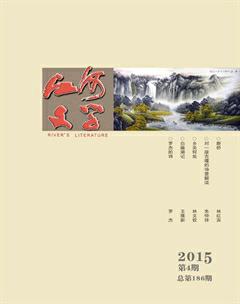暗流涌動的激情和詩意
劉波
要談論柳向陽,相對于其他一些詩人來說,更富有挑戰性和進入的難度,倒不是因為他是詩歌原創與詩歌翻譯上的雙槍手,而是在于他這個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古今中外之書,他皆涉獵,這種閱讀的廣博讓他獲得了寬廣的視野,對于有著濃郁知識分子氣質的柳向陽來說,這也是再好不過的一種狀態了。可是,他并沒有滿足于在純粹的閱讀里尋找樂趣,而自我創造則成為了他閱讀上的延伸,它們共同構成了柳向陽詩歌翻譯和創作生涯的一個精神之域。
從這個角度來評價柳向陽,可能仍然顯得太過寬泛,只是他在創作上不斷地收緊自己,縮小范圍,這與他在閱讀上的寬廣形成了一種反差:一面是在無限擴大,另一面是在盡可能縮小,這種狀態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具創造活力。在我看來,柳向陽首先是一個詩人,才是一個詩歌翻譯家。詩歌寫作的訓練為他從事翻譯提供了技藝上的膽識,同時也給他帶來了語言和思想交融的底氣,而且這兩者在柳向陽身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這些和他的廣博閱讀又一起豐富了他作為詩人的人生經歷,他甘于寧靜生活與寫作的理想,在當下這個追求“有用”的功利時代,確屬難能可貴。因此,評論家沈奇在見到柳向陽后,幾次提及他對“柳公子”的印象,他的不合時宜,他的多思姿態。
柳向陽為更多讀者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他的詩歌翻譯作品。但與那些廣撒網的詩歌翻譯家不一樣的是,柳向陽只是專注于兩位美國當代詩人的翻譯,一位是杰克·吉爾伯特,另一位是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兩位有著自己獨特風格的詩人,也從某種程度上成就了柳向陽的翻譯。這些年來,他集中力量投入到對這兩位詩人的中文翻譯中,并于2012年底出版了杰克·吉爾伯特的中文翻譯詩集《拒絕天堂》,朵漁在讀過這本詩集后,認為這是當年度最好的翻譯詩集,因為每年出版的翻譯詩集并不算少,可見朵漁的評價之高。當然,這樣的評價也并非出于“點贊”的友情,而是因為他譯出了吉爾伯特詩歌中的神髓。“黃昏與大海如此這般。那只貓/從兩塊地以外橫穿葡萄園。/如此安靜,我能聽到甘蔗林里/空氣的聲音。金黃的麥子暗了下來。/光亮從海灣離去,熱氣消散。/他們在另一個農場還沒有點亮燈,/而我突然間感到孤獨。讓人吃驚。/但空氣安靜,熱氣又回,/我感到我又好了。”(《幸免于難》)吉爾伯特是一個浪子,有著布考斯基的叛逆,他們的共同之點在于,兩人都反對詩歌的過分修辭,也即是我們常提到的華麗文采,他們的寫作皆忠于自己的內心,以最真實、樸素的語言呈現眼中所見和心中所想。而柳向陽的翻譯,也忠實于吉爾伯特的這種詩風,在漢語中為他樹立起了一個簡潔詩人的形象。我們說,翻譯講求信達雅,首先信是基礎,這是不可動搖的,有些人翻譯了多位外國詩人的作品,而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他似乎在翻譯一個詩人,將曼德爾斯塔姆也翻譯成了布考斯基的味道,這種典型的“誤譯”,并不在于他沒有掌握基本的翻譯技巧,而在于他沒有理解他所翻譯的詩人詩作本身。任何一個經典詩人都是有其獨特個人氣質的,而如何在翻譯中不丟失掉他的這種氣質,是對翻譯家最高的要求和嚴格的考驗。柳向陽的翻譯就在竭力做到此點,無論是杰克·吉爾伯特,還是露易絲·格麗克,他都是在對他們作全面了解的前提下,才會下筆。這也是他這些年只選兩位詩人翻譯的原因,他要對得起詩人的創作,同時更要對自己的翻譯負責。
當下,不負責的翻譯太多了,大家都喪失了精益求精的態度,隨便可以拿來就譯,顯得簡單粗暴,最后就可能導致,翻譯了很多詩人,也像是翻譯了一個,給人審美疲勞之感。柳向陽所遵循的翻譯中的信達雅之準則,已在這些年的實踐中成為了他的自覺,那些廣博的閱讀訓練也給他提供了更寬的通道和更高的眼界。翻譯詩歌的魅力,不僅源于詩人本身的特質,而且也在于翻譯者的再創造,尤其是翻譯外國詩歌如何為中國讀者所接受,且還不失韻味與詩性,這是有難度的。柳向陽一直在挑戰這個難度,試圖在信和達的基礎上作更精準的超越。詩意的呈現,有時就是一種飛翔之感的敞開,漢語原創詩歌如此,翻譯詩歌同樣有這樣的境界和風度。柳向陽在翻譯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的過程中,就與杰克·吉爾伯特那種內斂的激情呈現不一樣,他試圖譯出女詩人那種敏感的傾訴之意,有時是張揚的激情,有時又變成內斂的禱告。“這兒是世間嗎?那么/我不屬于這里。//你是誰?在亮燈的窗里,/此刻掩映在那棵綿毛莢蒾樹/枝葉搖曳的陰影里。/你能存活嗎,在我活不過/第一個夏天的地方?//整夜,那棵樹細長的枝條/在明亮的窗邊擺動,沙沙作響。/請給我解釋我的生命,你啊不露痕跡者,//雖然我在夜里向你大聲呼喚:/我不像你那樣,我只有/把我的身體當作嗓音;我不能/消失于沉默——//而在寒冷的早晨/在陰郁的地面上空/我的嗓音回聲飄散,/潔白漸漸被吸入黑暗//仿佛你終于在制造一個跡象/讓我相信你也無法在這兒存活//或向我顯示你不是我所呼喚的光/而是它背后的漆黑。”(《白玫瑰》)格麗克的詩在抽象與具象之間自由轉換,既富有玄學色彩,又不乏日常經驗的流露,這對于柳向陽的翻譯來說,就是要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切換的秘密鑰匙,他于細節展現中見真情,而在詩的升華上又通向了某種無限之意。這肯定不是單純的文字能力所可以解決的,它要求翻譯者必須入情入理且入心,方可真正進入詩歌文本的內部,還原當時詩人創作時的心境變化。
格麗克寫過兩組非常獨特的詩,一組題目皆為《晨禱》,還有一組為《晚禱》,雖然標題相同,但都有著各自微妙的感受呈現,隱秘、沉潛,在宗教和日常信仰里捕捉對人生的體認。我很喜歡這兩組詩中已翻譯成漢語的幾首,詩人雖然在記錄,但又有著沉思和辯護的味道。“你想知道我怎樣打發時間?/我走過前草坪,假裝/正在拔草。你應該知道/我根本不是在拔草,我跪著,從花圃/扯著幾叢三葉草:事實上/我在尋找勇氣,尋找/我的生活將要改變的某種證據,雖然/耗時無盡,檢查著/每一叢,找那片象征的/葉子,而夏天很快就將結束,已經/草木搖落,總是那些病樹/首先開始,那些垂死的/變得燦爛金黃,而幾只深色的鳥在表演/宵禁的音樂。你想看我的手?/此刻空空如在第一個音符邊。/或者總是想/延續而沒有標記?”(《晨禱》)詩人在向誰禱告?那個對象是上帝,還是有具體所指,我們不得而知,但閱讀和理解中一定有冥冥中的那個接受傾訴的人存在,詩人在想象的發揮中羅列著不同的意象,它們組合、變幻,成為詩人無盡的困惑,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交流的神秘感。詩人希望找到出口,但生活始終像個迷宮,我們只能在現實的纏繞中尋找與神對話的清醒詩意。柳向陽在翻譯這組詩時,想必也沉浸在對《圣經》的感受中,由此獲得了另一種洗禮。格麗克詩歌中的宗教感得以清晰地呈現,并為漢語讀者所接受,還是在于柳向陽如何更精準地去處理那些不為我們所知的人情、歷史和更高遠的異域情調。在《喀耳刻的悲傷》《花蔥(雅各的梯子)》《遠去的風》《一則寓言》等詩作的翻譯中,我們可以看出柳向陽同樣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對宗教的精準把握,確實是在檢驗翻譯者的學識和素養。他在這種有難度的翻譯中,一方面做了詩意的中介者,另一方面,最終還是通向了自己的內心。
我在前面說過,柳向陽首先是一位詩人,然后才是翻譯家,也即是說,他的詩歌寫作是其一切文學創造的基礎。沒有詩人的身份認同,沒有詩歌寫作的訓練,翻譯可能也會因此打折扣。柳向陽的詩歌寫作不完全是受誰的影響,而是在于他本身所擁有的氣質和性情,還有他所提倡的詩歌美學。他對玄學詩有著自己的看法,這給他帶來的是一種智力上的挑戰,詩人樂于其中,并由此找到了自己在寫作上的靈感。這一路徑很少有詩人能夠走得通,但柳向陽這一獨特的美學偏好,卻成就了他不同于一般詩人的詩風。他寫于2007年前后的《山中小城》《橙子花開》《格林諾貝爾隨筆》等詩都有著沉潛的語調,好像在避免著什么,又在追求一種準確。而近幾年,在玄學的基礎上,他在受閱讀影響的寫作中增加了介入的批判性,那不是憤怒,而是一種清醒。“昨夜讀茨威格的蒙田,書中說/蒙田知道我那個時代完全可能發生/古羅馬的帝王們統治下發生的/那些暴行。/這居然讓我有幾分驚喜。/讓我想起十多年前/一次夜深時讀王勃的《滕王閣序》/突然間的感動淚流。/今天我才清醒地意識到我有幸/親眼看到他們說的那些暴行/正在身邊發生。我說:我輩之責任/千年不易。”(《讀茨威格的蒙田》)這似乎是柳向陽的另一種詩風,貌似不會在他身上發生,但確實又出自其手,他那溫文爾雅的外表下,也藏有一顆堅韌之心。他書寫中的正義感,是其在閱讀中的轉化,同時也是他思想斗爭的某種結果:在這個時代寫作,有些東西我們不可能視而不見,它就像一種潛在的規則如影隨形,有責任的詩人只能如此運思,如此用筆。
柳向陽的詩歌翻譯和寫作,看似也像他的人一樣,平和、寧靜、波瀾不驚,其實他有著更為內在的活躍之域,里面暗藏著激流和風暴。他總是在不經意間挑戰自己,超越自己,這是一種趣味所支撐的激情使然。柳向陽詩歌中的那種激情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而是沉潛在詞語和句子內部,如一股涌動著的暗流在平靜的河面下奔騰,這并非詩人刻意為之,也不是他要由此去冒什么風險。在任何一個柔和的身體內,都可能會有著強悍的剛烈,柳向陽或許就是那以柔克剛的詩人,在四兩撥千斤的翻轉中凝取更為尖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