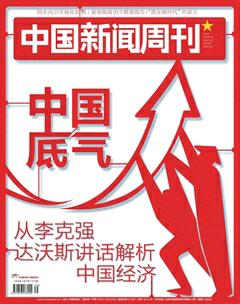困難和希望在于地方政府去杠桿化
楊英杰
國據報道,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鎖定16萬億元,預計債務率為86%。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15.4萬億元,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余額為8.6萬億元。一年半間,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加4.5萬億元,增長約41.4%。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得知中央將采用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存量債務后,為了獲得置換債券額度,會把部分或有債務轉成直接債務,不再隱瞞此前的債務,由此導致了債務規模的攀升。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債務負擔率仍屬可控,而且仍有一定的利用空間。盡管如此,地方政府債務如何消化亦即地方政府去杠桿化問題,已成為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杠桿化”一詞取自物理學,用以表示以較小的自有資金,利用財務方法和金融工具支配和撬動大量資金,用以投資和經營的模式和手段。“去杠桿化”的內涵就是在金融市場當中降低杠桿使用的過程。
中國的去杠桿化同美國的最大區別在于主體的不同。美國需要去杠桿化的對象是金融機構和家庭,而我國則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當然,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途徑以及市場化手段逐漸降低杠桿率,降低資產負債率,當前問題的關鍵在于地方政府如何加快去杠桿化進程。
雖然中美兩國去杠桿化主體不同,但操作手段卻有相似之處。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為穩定金融市場,收購了金融機構的大量不良資產,還接管了房地美公司與房利美公司。為了降低金融機構的杠桿率,美國政府、美聯儲采取資產購買等多種手段,用以消化金融危機產生的“有毒資產”,通過減少家庭和金融機構的杠桿,將杠桿轉移到政府部門。這與我國出臺的通過中央政府代行和部分省一級地方政府限額自行發債以及通過債務置換方式消化地方政府部分債務有異曲同工之處。
但需要強調的是,去杠桿化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也就是說,不經歷風雨無法見到彩虹。從當前美國和歐元區經濟發展現狀可以清晰地看到,危機之后各國經濟的恢復程度,和去杠桿的進程密切相關。美國經濟走上了持續復蘇的道路,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南歐諸國則不同程度地仍在為債務所困擾,最為脆弱的希臘已淪落到政府破產和金融體系癱瘓的地步。之所以出現如此鮮明反差,是歐元區、美國兩大經濟體去杠桿的快慢。數據顯示,美國的負債率(居民負債/GDP)已回落到歷史趨勢線,而歐元區依舊停留在2008年的水平。
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單靠地方政府債的有限發行以及各方利益博弈劇烈矛盾重重的債務置換方式,是不能很快得以解決的。而地方政府債務纏身極大地影響了社會資本對政府的信任度,阻礙地方經濟的發展。解鈴還須系鈴人,地方政府債務的化解、去杠桿化的完成,還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化解債務,需要現金流。現金流從哪里來,一是借錢,地方政府已是債臺高筑,目前來看此路艱難;二是發債,前述理由也決定了本條措施效率不高,效果亦不能立竿見影;三是土地財政,房地產市場泡沫亟待消化,也決定了土地財政的不可行。
傳統財政預算體制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是和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緊密糾纏在一起的。地方政府債務如果不能較好地得以解決,以短貸長、期限錯配問題不能有效地及時地得到持續現金流的支持,極有可能傷及中國整體財政乃至危及整個金融體系。對此,還是得建議:
一是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不是老一套的兼并重組,注重規模的擴張,依靠壟斷地位來攫取本應屬于社會的利潤,而是積極引入社會資本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加快推進政府社會資本合作(PPP)。要切忌個別地方政府采取所謂的“開門招商、關門打狗”的方式,傷害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和收益權利。也不能把PPP簡單地作為代替地方融資平臺的一種變體,如此只能加深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最終損害地方經濟發展的長遠基礎。
三是要全方位地營造良好的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生長土壤的體制機制環境。要通過更嚴格的事前決策、事中控制、事后督辦機制,結合干部任用體制的深化改革,徹底杜絕懶政庸政為官不為現象,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造良好的行政、法制環境。
(作者系中央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