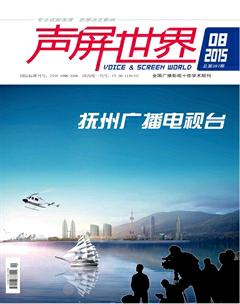關于法治節目主題的開掘
王 煒
講好“法”故事
《案件報道管理規定》要求的指導思想是:以案說法,引導群眾懂法知法守法。案件類法治節目的選題一般都富于懸念感,并有較強的矛盾沖突,尤其是故事性強。故事是一切敘事藝術的第一要素,它既是形式也是內容。
一、抓住故事眼。就是要結構好矛盾沖突,抓住故事核心,調準故事節奏,掌握好故事的脈絡,剪裁關聯度低的信息,醞釀故事的懸念、發展和高潮等。詩有“詩”眼,故事亦有故事眼。故事眼并不是一眼就看得到、看得準的,而選題也并不等同于主題。記者曾接到這樣的選題,妻子認為丈夫有外遇,于是打算自殺,但臨死前想到兒子留在世上會受苦,就拉兒子一起投河。沒成想,自己被救兒子卻淹死了。這樣的現實選題“眼”在哪里?首先,記者可以去做“婚外情”。其次,記者可以去做案情。做案情的常規做法即是展示案件過程,最后點評丈夫與妻子的各自責任和問題等。不同的處理方式眼位各有不同。筆者認為,即使外遇是客觀存在的,且節目具有道德評判空間,外遇也不等于妻子自殺,更不等于兒子死亡。值得深思的是,是什么導致了這場悲劇,以無可挽回的方式扼殺了感情,扼殺了生命,扼殺了這個家庭原本存在的希望?沿著這道思索目光之所及,我們可以關注到這對夫妻行為之上的文化意識,以及人物性格所決定的命運必然。當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的融合達到一個危險區間時,摧毀一切的爆炸就被點燃。好的故事眼可以讓法律的光芒得以匯聚,讓報道的主題更加精準,讓新聞的影響更為彰顯。
二、提煉故事線。案情報道需要從龐雜的素材中挖掘出以下元素:原因、發展、高潮、結局、矛盾等。具備了以上元素,元素與元素間方能發生化學反應,由此而衍生出戲劇性、過程性、可視性和期待感等。節目故事的線,顧名思義是線性的,是單向的,是有限的,而最具品質的故事線應是多向的、開放的、無限的,這就要求創作者還要從素材中開掘出故事背景、社會關注、文化思考、情感體驗、心路歷程等元素,從而使故事線承載起情感與思想構成的大場面,并結構起融思想性、故事性為一爐的大篇章。有時候,關注故事的背后會發現更精彩的故事,思考的深度決定故事的深度。央視《焦點訪談》欄目曾播出一期節目《青島:查黃毒》,報道了公安部治安行動總隊會同青島市公安局對青島市區娛樂場所黃賭毒進行的一次專項巡查活動。記者在這次隨行采訪中并沒有拍攝到酒店、夜總會中發生的賭博等一系列違法活動,然而公安部卻在三天前的暗訪中偷拍到了這些營業場所發生的種種違法行為。據此,該期節目講述的故事似乎講不全講不清了,但記者把報道的思路往深里延伸了一步,為什么專項巡查活動之前有賭博、艷舞、吸毒等違法活動發生,一巡查卻啥也查不到,這后面的新聞背景、社會思考是什么?按照這一思路,編導把兩次行動的不同結果先后客觀展現。節目播出后引起國務院領導重視,作出指示,成立調查組徹查內幕,結果青島市公安局長及其子落入法網。
三、視覺語碼。作為法治題材的電視報道,在講故事時有自身的特點。電視是視聽藝術,電視信息傳播的主渠道是畫面,電視是要讓畫面來說話的,電視畫面的重要職能就是再造現場,因此,如何在法治報道中彰顯視覺的力量必須充分關注。在電視畫面的諸要素中,現場性的畫面所包含的信息量、真實性、直觀可視性等都是品相極高的原礦。有時候,一個法治類電視報道成功與否,不是主持人事后在現場的主持和采訪如何精彩,不是電視解說的深度如何充分,也不是節目的結論如何高屋建瓴,而是一系列的現場畫面,甚至極端時候,只取決于一小段關鍵事件關鍵地點的關鍵畫面呈現。
社會人文在法律中的映射
法治類節目要“引導群眾逐步理解現代法治精神與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通過案件報道把握社會生活的主流,密切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血肉聯系”。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法治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法律進程中,新聞工作者需要宣傳法律,敬畏法律,也要在法律規范內深刻領悟社會人文的博大精深,體現法律映射下的人文關懷,彰顯媒體的社會價值。
在新聞報道實踐工作中,選題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涉及專業類的,二是涉及行業機制類的,三是涉及社會層面的。因此,如何把選題本身蘊藏的社會價值開掘出來,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藝術。依照央視綜合頻道總監錢蔚所說,不能把一個十段的選題做成六段的。她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貴州省有一個孩子生急病,家長撥打110,結果救護車送到后,孩子沒治好死了。事后得知,這是一段時間以來120 送來的第三例患者不能得到有效救治而死亡的事例。記者在初次報道中,把主題定位在一起醫療事故的報道上。錢蔚看了節目后說,最具價值的主題是,120 機制存在的弊端、成因及解決之道,節目的視點即社會性關注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這就是主題開掘的社會價值。
記者要做好法治類節目社會層面的選題,必須處理好以下兩點:一.深入分析研判選題內容。只有深入,才能深刻;只有吃透選題基本面,才能抵達選題至高點。當然,這需要記者下工夫:熟悉法律基礎知識,洞察人情世事,胸懷社會發展大局。此外,記者需要培養鍛造一雙“鷹眼”,能夠在紛繁的各類矛盾中精準抓住問題的核心,并且善于分析其中的成因、影響、解決途徑等要素。二是電視化表達節目主題。電視報道不同于工作報告或學術論文,它需要將節目主題深刻性與節目表達藝術性合為一體。一個法治類選題,需要記者敏銳深刻地去開掘其主題的內涵,同時記者又需要把“硬”主題用“軟”表達來實現和完成,藝術地呈現,這就要求記者遵循電視傳播規律去取舍、選擇、組織、剪輯素材,寓觀點于鏡頭中,寓深刻于平實中,寓復雜于清晰中,寓多義于平白中。上饒電視臺《天天看點》欄目曾接到這樣一個選題,婺源縣段莘鄉村民發現了一塊石頭,這不是普通的石頭,而是一塊上好的硯石,價值不菲。就在村民熱議應該如何處理這塊硯石時,石頭突然失蹤了。一塊寶貝石頭,重達2 公斤,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不翼而飛,引起了當地極大的震動。警方及時介入,根據一系列蛛絲馬跡最終破案。那么,這個選題做成一個刑事案件當然有關注度,而且情節曲折,懸念叢生,記者在初做該片時也是如此處理的。但當筆者審看了節目后,卻將節目的關注度轉到了這塊石頭的出現與消失給當地帶來的沖擊,將選題的中心確定為一塊石頭所投射的社會話題——古老村莊的人心在利益的風波里沉浮,純樸農村在時代的浪潮中嬗變。
法治類電視節目的主題開掘形式多樣,各有精妙,若能于萬象之中見事,于見事之中見人,于見人之中見社會,那么法治類電視節目則光彩自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