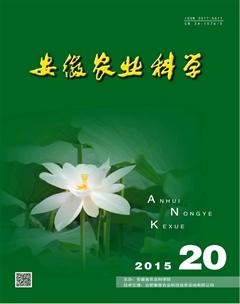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研究
王夢思 劉紅光

摘要 結合基尼系數構建了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因素分解模型,將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變化分解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家庭生產支出、其他支出5個因素的貢獻程度,并對1990~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1990~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區域差異總體上呈現擴大趨勢,高收入地區工資性收入的提高是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最大因素,而低收入地區只能依賴減少家庭支出來換取純收入區域差異的減少。因此提高低收入地區的工資性收入,且加大對低收入地區的支出補貼,應該成為我國減少農村收入區域差異的政策選擇。
關鍵詞 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因素分解
中圖分類號 S-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5)20-321-03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up a model to decompose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change into factors including salary income, family business income, property and transfer income, family production expenditure and other expenditure mix by Gini index. And then take China as example to empirical analysis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er capital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er capital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shows overall enlarge trend. The salary income of high income areas increase is the biggest factor leads to the chang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er capital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nd the low income areas only rely on to reduce family expenditure for reduc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salary income of lowincome areas and increase expenditure subsidies should be the policy choice of China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income.
Key words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Regional differences; Factors decomposition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及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2]。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早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縮小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問題是當前政府、社會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這一問題的解決與否關系到國家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實現。研究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相較于國內而言,國外專門研究農村居民收入與支出區域差異的文獻較少。但對于這一問題,國外學者在各個國家農民收入不同情況系統分析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定的理論或觀點,他們將農村問題納入到收入分配、人口流動問題中分析[3-7]。
伴隨著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和經濟狀況的改善,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區域不平衡現象日益凸顯。農民收入問題關系到國家發展全局和就業問題[8]。圍繞如何縮小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問題眾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居民收入差異變化的趨勢研究和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影響因素的分解研究2個方面。區域差異研究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加權變差系數法[9]、基于隸屬函數的協調度模型測度方法[10]、基于人口加權的變異系數法[11]、聚類分析法[12]以及基尼系數法[13]等。在全國層面上,萬廣華推導了基尼系數變化的分解公式,分析我國農村區域間的收入差異,發現我國農村區域間收入差異的上升趨勢,且這個趨勢與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14] 。在省市層面上,陶應虎通過面板數據模型方法,得出了江蘇省13個市農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變動趨勢在數學意義上并沒有表現出威廉姆森倒U型曲線特征,說明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并不必然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而無條件下降[15];王雅楠等研究發現近年來山東省的農民收入、消費水平明顯提高,但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收入水平差異很大,各市之間消費支出差異與收入水平之間的差異較均衡[16]。
總之,國內外有關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研究很多,但有關其影響因素分解的研究,特別是分解模型的構建,仍有待進一步加強。許多研究結果均顯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區域差異有擴大趨勢,且工資性收入是導致這種區域差異擴大的主要原因,但多數研究并沒有將區域支出的因素包含進來。筆者在基尼系數的基礎上,構建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指數的因素分解模型,再從收入因子(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和支出因子(家庭生產支出、其他支出)2個方面系統研究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并從政策層面對解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問題提供了建議。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選取1990~2012年的數據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其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數據采用1991~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的人民生活數據;家庭生產支出和其他支出數據來源于2006~2013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的農村投資數據和1991~2005年的各省統計年鑒。有些省份部分年份的統計年鑒中沒有農村居民家庭支出數據,則采用這些省份的調查年鑒、調查數據等。
1.2 研究方法
農村人均純收入主要有收入和支出兩大部分構成,在此將影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因素分為5類,即工資性收入(X1)、家庭經營收入(X2)、財產及轉移性收入(X3),以及家庭生產支出(Y1)、其他支出(Y2)。i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的變化則可以分解為上述5個因素的變化之和,即:
類基尼系數并不是通過每一個變量直接計算的基尼系數,而是按照t+1時間區域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大小順序進行排序的其他每一個變量,根據基尼系數計算公式計算而得的類基尼系數。類基尼系數并不是通常所講的基尼系數,它可以是正數,也可以是負數。計算類基尼系數,首先要對t+1時間區域農村人均純收入進行排序,然后按照這個順序計算其他變量的基尼系數。以t時間區域農村人均純收入G*t為例,其計算公式如下:
2 結果與分析
根據上述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因素分解,可以將1990~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分解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家庭生產支出、其他支出5個因素變化的貢獻程度(表1)。從計算結果可以發現:
第一,工資性收入變化是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最大因素。如果令2012 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為100,則1990~2012年工資性收入的變化對這一差異的貢獻為65.39%,也就是說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有接近2/3是由于過去23年間工資性收入變化造成的;從區域差異的變化看,以基尼系數來衡量,1990~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擴大了1.73%。以上結果表明,1990~2012年我國的工資性收入分配不利于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縮小,即原本農村居民收入高的省份,其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持續走高,而農村居民收入低的省份,其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緩慢。如東部地區1990年農村工資性收入為247.7元,2012年工資性收入為6 684.1元,而西部地區1990年農村工資性收入為10.8元,2012年工資性收入為2 069.5元,增長量僅為東部地區的32.0%。
第二,家庭經營收入變化也是影響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一大因素,但家庭經營收入變化對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影響逐年降低。1990年家庭經營收入變化對1991年區域差異的貢獻度為13.08%,2011年家庭經營收入變化對2012年區域差異的貢獻度僅為0.73%。這主要是因為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以及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所導致從事農業生產和與農業生產相關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家庭經營活動農民的不斷減少。
第三,財產及轉移性收入變化也是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較大因素。1990~2012年財產及轉移性收入變化對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貢獻為26.73%。其中,在所有研究年限內,本年對下一年區域差異的貢獻度平均為2.38%。以上結果表明,1990~2012年我國的財產及轉移性收入變化不利于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縮小。隨著社會發展,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在農民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要縮小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離不開對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嘗試。
第四,家庭生產支出變化對于縮小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具有一定效果。如果令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為100,則1990~2012年家庭生產支出的變化對這一差異的貢獻為-11.48%,也就是說過去23年間家庭生產支出的變化抵消了2012年1/10強的區域差異。表明家庭生產支出變化對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家庭生產支出變化相對于工資性收入的巨大變化來說,變化不夠明顯。由此可見,我國農村收入較低的地區,其支出也相對不斷減少,即陷入了低收入-低支出-收入更低的惡性循環。換句話說,低收入地區農村只能靠減少支出來換取一定程度的純收入區域差距,這明顯不利于我國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
總之,1990~2012年間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變化進一步擴大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而家庭生產支出和其他支出變化卻有利于縮小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區域差異。但家庭生產支出和其他支出變化帶來的區域差異縮小,并不能抵消區域差異擴大,最終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擴大。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結合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構建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因素分解模型,將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變化分解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家庭生產支出、其他支出5個因素的貢獻程度,并對1990~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進行了分解。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工資性收入變化是導致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最大因素。1990~2012年工資性收入的變化對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貢獻度為65.39%。因此,我國的工資性收入分配不利于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縮小。高收入地區工資性收入的提高是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最大因素,而低收入地區僅能依賴減少家庭支出來換取純收入區域差異的減少。
(2)家庭經營收入變化也是影響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一大因素,但家庭經營收入變化對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影響逐年降低,表明農村勞動力轉移導致我國從事農業生產和與農業生產相關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家庭經營活動農民的不斷減少。
(3)財產及轉移性收入變化也是導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較大因素,且對區域差異的影響逐年提高,表明隨著社會發展,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在農民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縮小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離不開對財產及轉移性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嘗試。
(4)家庭生產支出變化對于縮小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具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明顯。1990~2012年家庭生產支出的變化對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的貢獻度為-11.48%,也就是說過去23年間家庭生產支出的變化抵消了2012年1/10強的區域差異。低收入地區農村只能靠減少支出來換取一定程度的純收入區域差距。這明顯不利于我國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因此提高低收入地區的工資性收入,且加大對低收入地區的支出補貼,應該成為我國減少農村收入區域差異的政策選擇。
3.2 政策建議
3.2.1 提高農村工資性收入水平。大力推進低收入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水平。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工資性收入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貢獻度是最大的。因此,如果要縮小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就必須大力提高中西部和東北部省市農村居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促進落后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發展二、三產業,加快落后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從整體上提高落后地區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水平。同時,應加快就業制度改革,逐步構筑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準入政策,建立健全包括住房、醫療保健、補貼保障等在內的優惠福利制度,實現城鄉勞動者公平就業,從而提高農民收入。
3.2.2 提高土地產出效率。采取各種措施支持農業發展,提高土地產出效率,提高農產品產量和品質,促進與農產品相關的加工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該研究表明,雖然家庭經營收入變化對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區域差異影響逐年降低,但它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影響力仍然很大。農民家庭經營活動中,農業生產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方面。要保證農業生產產量不斷提高和農產品品質持續改善,不但要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率,更要增加農業生產中科技要素的含量。農民家庭經營活動還包括與農產品相關的加工制造業和服務業。政府在實施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可通過構建產業鏈條,將農村企業納入社會化大生產,使其成為產業鏈條中必備的一環,進而提高其管理水平。
3.2.3 提高財政補貼。加大對低收入農村地區的家庭支出進行財政補貼。該研究表明,家庭支出對農村人均收入的區域差異的擴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如果僅靠抑制落后地區家庭支出來換取區域差異縮小明顯不利于落后地區小康社會的建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如果增加其支出又勢必造成人均純收入區域差異的擴大。因此,政府應在政策層面加大對低收入地區的家庭支出進行財政補貼,如提高對農村生產經營性支出的補貼、減少農村落后地區生產經營性活動的稅費水平。
參考文獻
[1] 羅守貴,高汝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及居民收入區域差異變動研究[J].管理世界,2005(11):149-154.
[2] DAI X X,LIU L Z.The impact of the income gap in rural China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il index[J].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2014(5):60-63.
[3] KAN I,KIMHI A,LERMAN Z.Farm output,nonfarm income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rural Georgia[J].Agri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2006,3:276-284.
[4] MATHIJS E,NOEV N.Subsistence far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lbania,Bulgaria,Hungary,and Romania[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4,42(6):72-88.
[5] BALINT B,WOBST P.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by individual farmers:The case of Romania[J].PostCommunist Economies,2006,18(1):101-121.
[6] XIA Y.Empirical study on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J].Energy Procedia,2011(13):9845-9850.
[7] LI S J.Demand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n the sports service products of rural residents[J].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2013,9(1):26-30.
[8] 張車偉,王德文.農民收入問題性質的根本轉變——分地區對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變化的考察[J].中國農村觀察,2004(1):2-13.
[9] 楊開忠.中國區域經濟差異變動研究[J].經濟研究,1994(12):28-33.
[10] 錢力.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適度性分析——基于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測度方法[J].經濟問題探索,2014(8):129-135.
[11] 覃成林,楊威.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不平衡的動態變化及影響因素——基于人口加權變異系數的分析[J].產經評論,2012(4):115-124.
[12] 錢力,曹凌燕.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類型的劃分——基于聚類分析法的應用[J].經濟問題探索,2013(8):43-48.
[13] 劉慧.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變化的因子解析[J].地理學報,2008,63(8):799-806.
[14] 萬廣華.中國農村區域間居民收入差異及其變化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8(5):36-42.
[15] 陶應虎.農村居民收入區域差異的走勢和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經濟問題,2010(6):71-74.
[16] 王雅楠,趙庚星.山東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消費支出及其區域差異分析[J].山東農業科學,2013,45(10):14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