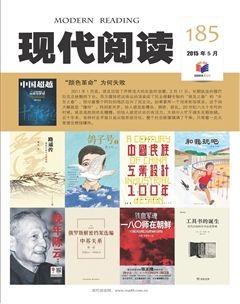歐洲的悲劇
[英]約翰·基根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令人悲傷而又并非必然的沖突。它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軍事沖突發生之前充滿危機的五個星期里,如果謹慎小心,并且人們心中共有的善意能夠發出聲音,導致戰爭爆發的一連串事件可以在任何一刻終止;它令人悲傷,因為第一次沖突的最終后果帶走了1000萬人的生命,使更多人的情感備受折磨,摧毀了歐洲大陸仁慈而樂觀的文化,而且在四年之后槍炮聲終于沉默的時候,留下一份政治敵意與種族仇恨的遺產——它如此劇烈,以致不提及它們,就無從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二戰是一戰的直接產物,造成了五倍于此的人員傷亡,以及無法衡量的、更加巨大的物質損失。一戰宣告了大規模殺傷的到來,而二戰則把它帶到冷酷的頂峰。
很少有法國或英國的社區沒有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死者的東西。在英格蘭西部的一個村莊里,岔路口的墓地紀念十字架底部刻著一串死者的名單。然而,這是后來才刻上去的。十字架本身卻是用于紀念那些沒能從一戰戰場上返回的年輕人。紀念十字架是教堂以外村莊唯一擁有的公共紀念物。在每個村莊,在每個郡的市鎮,以及在索爾茲伯里的教區大教堂里都有類似的東西。在法國的每一所大教堂里也都可以看到同類的紀念物,在這些教堂里會看到碑上銘刻著如下字句:“獻給神的榮耀,并紀念大英帝國死于大戰中的100萬人,他們中的多數長眠于法國。”
法國在一戰中損失了將近200萬人,每9個開赴戰場的人中就有2個死去。蔚藍的地平線上,向著東方的德國前線端起刺刀的、勇敢的法國戰士雕像是他們的象征。刻寫在底座上的名單之長令人心碎,更令人心碎的是同樣的名字多次出現,表明一個家庭不止一個,而是幾個成員喪生。大多數一戰參戰國的市鎮和城市中都有刻著類似名單的石碑。冷酷的石碑令人回想起歷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所經歷的犧牲。而今,這一切卻幾乎已被歷史遺忘。
因為德國軍隊的聲名受累于納粹政權的暴行,德國人沒有辦法合宜地哀悼他們死于二戰的400萬生靈;因為很多人死在他國的土地上,他們發現為一戰死者而感到的痛苦安排一種合適的、象征性的表達方式同樣困難。如果這種困難不是感情上的,也受限于物質條件。布爾什維克革命使他們無法接近東方戰場,而西方戰場的主人最多也不過是勉強允許他們取回并掩埋尸體。無論在心理還是土地上,法國人和比利時人都沒有什么地方容得下為德國人建立戰爭公墓。
當英法就士兵的永久安葬達成諒解——這些花園般的墓地在1920年代沿大戰的西線星羅棋布,驚人地美麗——德國人卻不得不在晦暗的角落挖掘萬人坑以埋葬他們的死者。只有在東普魯士,坦能堡戰役發生的地方,他們得以為戰死的士兵建立一座勝利者的陵墓。在本土,遠離德國年輕人戰死的地方,他們以大大小小教堂中紀念碑的形式寄托哀思。
大戰中的普通士兵,超過一半在西線陣亡的被丟棄在戰場的荒野中,在東線可能更多。無名尸體的數量如此巨大,以致剛一停戰,一位曾擔任隨軍牧師的英國國教牧師便首先提出,最恰當地紀念所有這些無法辨認的戰死者的方式是掘出其中的一位,并把他重新安葬在榮耀之地。選定的死者被帶到西敏寺,并安置在入口處。同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停火兩周年的日子里,一個法國的無名士兵被安葬在巴黎凱旋門下。后來其他許多戰勝國也在首都重新安葬了無名的士兵。然而,當1924年戰敗的德國嘗試為戰死者建立國家紀念碑時,揭幕式卻在政治抗議中陷入混亂。艾伯特總統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他的演講之后,本該是兩分鐘默哀,但卻被支持或反對戰爭的喊聲打斷。其后,揭幕式演變為一整天的暴亂。戰敗的痛苦持續分裂著德國,直到九年后希特勒的到來。就任總理不久,納粹文人就把希特勒——“無名下士”——描繪為“無名士兵”的代表。不久,作為德國元首的希特勒就在演說中稱自己為“大戰中的無名士兵”。他種下了將會帶走其他四百萬德國人生命的種子。
戰爭的仇恨易結難解。到1914年年底,也就是一戰爆發4個月后,2000萬法國男性——其中1000萬處于軍役年齡——中有30萬人戰死,60萬負傷。到戰爭結束時,將近200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它是法國軍隊的主力,減員率是征兵比例的22%。傷亡最慘重的是最年輕的年齡組:1912~1915年入伍士兵的傷亡達到27%~30%。這些年輕人中的許多還沒有結婚。不管怎樣,到1918年,在法國有63萬名戰爭寡婦,以及大量被剝奪了婚姻機會的更年輕的女性。1921年,20到39歲之間人群的性別比例為男子占45%,女子占55%。而且,在戰爭中傷殘的500萬人中,數以十萬計被列為“重度傷殘”,意指那些失去四肢或是眼睛的士兵。或許最深重的痛苦由那些臉部受傷而致毀容的受害者承擔,他們中的一些變得如此駭人,只得在農村建立隔離居住區,供他們一起在此休養。
德國戰爭一代經歷的苦難與此不相上下。“1892~1895年齡組在戰爭爆發時正值19~22歲之間,人口數量減少了35%~37%。”總的來說,1870~1899年間出生的1600萬人中在戰爭期間有13%以每年465600人的速度喪生。幸存的德國“重度傷殘”者中,44657人失去一條腿,20877人失去一只手臂,136人失去雙臂,1264人失去雙腿。另外還有2547人因戰爭致盲,一小部分人頭部受重傷,其中大部分后來死去。共有205.7萬名德國人死于戰爭或在戰后因傷致死。
盡管德國是有統計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俄國和土耳其的死亡人數仍未精確統計過——但從比例上來看卻并非情況最嚴重的。情況最嚴重的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的戰前人口為500萬,其中12.5萬士兵戰死或死亡,但其他65萬名平民死于貧病交加。這造成了高達15%的人口損失。與之相比,英國、法國、德國約為2%~3%。
即使這些相對較低的死亡率也留下了可怕的心靈創傷,因為它降臨在社會男性中最年輕、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身上。當戰爭逐漸隱退到歷史深處,人們逐漸習于譴責對“失去的一代”的哀悼,視之為創造出來的神話。人口學家證明,人口的自然增長很快就可以彌補戰爭造成的損失;而一些鐵石心腸的歷史學家則堅持說,這些損失只有一部分家庭感覺得到。他們論辯說,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有20%參戰的士兵死亡;而占人口總數比例更低些,為10%或者更少。對大多數人而言,戰爭不過是生活的一個片段,對常態的一次偏離,一旦槍聲停止,社會很快就會恢復如初。這是一種自大自滿的判斷。
與1939~1945年的大戰相比,一戰的物質損失確實更小。在這一過程中,沒有歐洲的大城市像二戰中德國所有的大城市那樣遭到空中轟炸,被嚴重破壞甚至摧毀。一戰是一場發生在鄉下的戰爭,無論在東線還是西線都是如此。戰場很快便成為農田或草場,而且除了凡爾登附近,毀于炮擊的村莊很快得以重建。戰爭對于歐洲的文化遺產也沒有造成難以修復的損害:伊普爾的中世紀紡織品市場今日依然矗立,一如1914~1918年的戰火以前;阿拉斯的市鎮廣場、魯昂的大教堂也是這樣。而在1914年一次非典型的汪達爾行為中被燒毀的魯汶大學圖書館的收藏,也在戰后一點一點地恢復。
尤其重要的是,交戰者并未對卷入其中的平民施以蓄意的傷害和暴行,而這是二戰的典型特征。除了在塞爾維亞以及開始階段的比利時,人們并未被強迫放棄自己的家園、土地和非軍事性的職業。不像二戰那樣,一戰中沒有系統的種族取代,沒有蓄意的饑餓,沒有對財產的剝奪,也幾乎沒有屠殺和暴行。與國家宣傳機器極力證明的相反,除了戰場上的殘酷,它是一場很奇怪的文明戰爭。
然而它確實對文明造成了傷害,對歐洲啟蒙運動理性而自由的文明造成了傷害。更加嚴重的是,這種傷害是永久性的。而且,全世界的文明都因此遭到了損失。盡管戰前歐洲各國對于歐洲大陸之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行為都是帝國主義的,但卻都對憲政、法治以及代議政府等原則抱有敬意。戰后的歐洲很快放棄了對這些原則的信心。戰后的十五年里,極權主義——這個詞匯意味著一種抗拒,自1789年君主政體衰退以來便激發著歐洲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體系——幾乎在所有地方發展起來。極權主義是戰爭以其他方式所作的政治延續。它使追隨它的選民大眾一致化、軍事化,普遍地剝奪選民的選舉權,激發他們最低層次的政治本能,并邊緣化和恐嚇一切內部反對者。一戰結束不到二十年,歐洲又一次被一場新戰爭的恐懼所包圍,雖然一戰曾被稱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傷害也存在于重整軍備的洪流中那些一戰中曾僅作為雛形而為人所知,但卻威脅使二戰成為一場更大災難的武器:坦克、轟炸機、潛艇。
1939年到來的二戰毫無疑問是一戰的結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