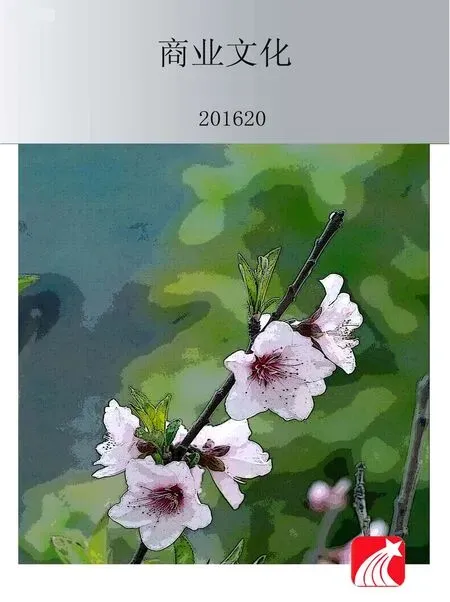崇德仰藝:權威深處的自覺問責著名畫家王立成和他的國畫鑒學
文 巴·鋼普力布

“我們在評介和探究一位藝術家藝術優劣的時候,首先要考慮到其藝術成熟程度與益世價值大小,也一定要本著對藝術家人格敬重的原則,同時關照到他的藝術前景的升擢與出眾可能(摘自《力布論畫》)”。王立成先生是我早年間便重視起來的一位資深畫家,并對其作品進行了盡我所能的研究。美術的逐步深入,為美學與美學研究提供了個強大的元素后盾。而美學深入的解剖物件,絕對是依靠對美感藝術最為精準的豐滿概括與理論認同,因此,我們在王立成先生大量的國畫作品中獲得了這方面的藝術信息,譬如他的國畫:《襟懷不染唱漁樵》、《溪徑蜿蜒烏蓬行》、《浮云淡去送流年》等等,作品典型的大氣規模和藝術規整大都具備了相類風韻。

王立成先生的《逸興遠望抒幽情》是一幅干凈利落的國畫摹本。立成總是在“憑空”構想中讓我們真切感受:正午時分,山形依舊,每座山配比并沒有太大的懸殊,卻也是遠近高低各不同,而且可貴的是,遠處山影似乎移居,漂泊的賞心與漂泊的畫面動感重合,形成藝術潮汐的巨大吞咽,給藝術以成倍的放大。這大概就是藝術家的能耐所在。而輕巧的雙舟蕩飛峽,與滄海蒼天渾圓一色,近山焦墨與彩墨混合層次,窺有聊聊戶居,如虎一座背影之山,被遙遠的江流環繞著它的氣勢,遠山近嶺渾然一體,江天共色云作補遺,真可謂:孤寡數筆之下,見十里江河天際飛流;濃淡百涂之間,聽萬千山川松濤放歌。在視聽之中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畫面有意義中讀出了無意義,有在無意義中讀出有意義。這樣既給歷史虛無以能量級別的夯實,又給人生虛無一個勁力型的誠懇支撐。所以說,“一個高品位的書畫藝術家,不是攢足時間,更多的是去檢討自己,矯正自己,完善自己。如果將貶低他人敗壞他人作為習慣性津津樂道,說輕了是個壞毛病的問題,說重了那是個道德問題。因此,畫家自己必須以投靠人的品質修為為歸宿,以奔襲藝術善本真源為地標,與安仁先賢締造的文明去有意重合,慢慢學會在自覺狀態下驅逐惡意和歹毒,驅散孤寂與惆悵——藝術家不一定非得經歷以一聲長嘆開始,以兩行悲淚結束這樣的凄憫的過程。要把平生勁力使出,讓自己心性不在難堪,讓國畫文化不再寒酸,如是足夠(摘自《力布論畫》)”。“玄冥之境”是藝術家為了追求一種超越質和解放感。而一個人作為一個感性個體的存在,總是不免帶有相當大的局限性。所以,一個人如果有所突破,能做到無懼、無私、無我,就可以超越個體存在的局限性從而從種種制約和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藝術解放。因此,國畫藝術作為畫家人性幻想的一個組成部分,無不以挖空心思的藝術天賦賜予作品最為濃情的傾注。這是國畫藝術家的歷史使命,也是國畫藝術家的現實育命。“讓文明再生是對人類文化的一種貢獻。藝術邏輯,天文邏輯,人性邏輯,都有著自己通常不可越軌的環繞行途。公民社會每生活一天,都需啟動國家資源,包括歲月資源”。而時間的誕生是很有意思的,以占卜為例:占卜的“卜”,將一根桿立在地上測量陰線,來準確定位“二分二至”點(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上下半年有個交叉點。但這是先人走過來的歷法文化,是經驗特征。而王立成先生的經驗更多的是憑覺知賴臆想,不是每每寫生然后入筆。然而,他的腦海里心性間不是憑空,是將世界萬象早已嵌入了某個符號,所謂的積淀存儲。只是隨時調用而已。“美術作為藝術門類最大的行騙行當,都是在誠懇中求證文化真理的良心過程(摘自《力布論畫》)。”王立成先生的新作三小品:《凝神》、《蛐蛐斗》、《孤泛》等等,都是用自己驚人的天賦,機緣掌得的藝能,還有情懷灌膠的賦予。所有這些,均極好地給自然或人文闡釋了藝術與藝術之間的扣合勻兌,并為藝術與之相適應的藝術本能之外的世界萬象賦予了氣脈融通。再譬如國畫:《東籬黃花為誰香》、《山水中堂》、《浮游在世勵身心》等等。“藝術語境的成人化,印證了國畫文化的正當性和深刻性;而童趣語境不能把羞恥當羞恥,也不能將罪惡當罪惡。這可能是成人與童真最大的物理落差。形式裁定,包括形式宗教,已然成為我們成長的文化背景,這也可能是為數不少國人或國人中的書畫家和其他門類藝術家在某種焦慮中翹首宗教的期待情懷。因此粗定義:國畫具有不排斥技術文明的質量,在追求理性回歸,平衡和矯正社會生活中的某些浮躁中,一定要走在時間和意識前面。厚重的藝術思想資源,以用自身的精神滋養,足可進入神教領域。立成先生的《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愛好由來落筆難》、《翁昔少年初畫山》等等,都潛隱著密密的宗教色素,因而教化來臨就更加意味著更加黛青的渾圓而成為益世不俗。“中國的國畫藝術,就藝術本質而言,最終會與其它文化走向合流。畫家能將僵硬賦予藝術動感,是畫家本心技術的最初萌發;能將凌亂賦予藝術動情,是畫家感性藝術的升華暴露;能將空濛賦予藝術圓潤,使文化主客體之間共構靈魂之動容,這是畫家至高的理性操縱(摘自《力布論畫》)。”王立成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令人動感、動情、動容的優秀畫家。

美術的發生不僅僅有臨摹大自然與人文境象的志趣與義務,而且與追求光明有關,與贍養真理有關,與抬愛生命有關
依照“三個有關”規則,從藝如此多之年頭,王立成先生概莫退卻巇險,更未葸恐不前,他總是以自己最沉穩的精神風貌,育生淡定的人情世故,賜予國畫最為虔誠的藝術靈魂;總是在不急不躁的情緒中,行進著自己意識深處最為坦蕩的藝術步履。人性的不亢不卑,造就了他藝術的不亢不卑,這也算一門絕技。
立成之畫以此“三大”陳詞據理,來說明物事兆應的準確水平,來求證“贍養真理”的除邪清腐,來呵護心理能量間可能受獵的一種智慧避讓,品讀立成的《瀟瀟山澗水潺潺》、《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浮云變幻豈無心》等等,在藝術風格存異的同時,共構著人文風格的致同性十分明顯。這些作品共同承載著人世間的酸甜苦辣,共同承擔著藝術家的人文情懷,共同承托著人類憧憬美好的遠景期冀。而在國畫的細枝末節上,立成更為注重:從朵瓣點綴到枝椏放生,從月云飛渡,到蓬蒿茂盛,從橫石走紋,到冬松翠蒼,從清流媚嫵,到柔風四起等等,以此紛繁的人世間,來豐富畫家內心深處的不易排遣,來暴露畫家藝術靈思之外的欲達向往,來珍惜人世間“抬愛生命”的熙熙攘攘。
世間之事的絕對,定然是蒼白的、茍且的,因而也是短命的;而相對是公達的、真理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比起藝術起步與早些時候的前期作品,現如今已然成型為王立成先生自己的獨到,也就一并成為他相對的藝術美妙。他十分用功,在為自己的藝術請命立法的同時,也在為自己的國畫藝術創造了自身權威,更一并為自己的國畫藝術形成自覺狀態下的本體引領。大家明白“理性的最高境界是握切理性至適的分寸。理性過度,就意味著勢必回踅至感性軌跡(摘自《力布語錄》)。”而立成用自己高潮的理性嚴苛,在畫余閑暇常常問責自己:我的國畫藝術使命究竟在哪里,我的國畫藝術水平究竟在哪里,我的國畫藝術的前景,究竟在哪里?
王立成:其人不怠,其畫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