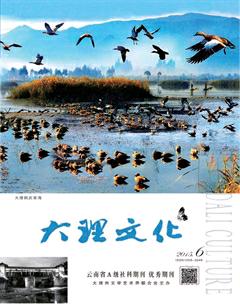我的電影情緣
一
我生在南澗,長在南澗,小時候最喜愛的事情就是看電影。
記得那時南澗和巍山還沒有分開設縣,每隔個把月,縣電影隊就會用牲口馱著16mm的老“長江”牌電影放映機和非常笨重的水冷式“03”型發動發電機來南澗放電影。
那時的南澗小城,還沒有禮堂和電影院,可供選擇的放電影場地只有一塊用石灰、碎瓦、粗沙混合打成的籃球場(我們習慣稱其“大白場場”)和“合作社”(供銷社)里面一個稍微大一點的院子。“大白場場”上每天晚飯后都有“公家人”在那里打籃球,而且一面與民房相鄰,三面是空地和臭水溝,沒有遮攔不好賣票,所以電影隊一般都會選擇在合作社院子里面放電影。
合作社院子很大,東邊蓋了倉庫和門市部;南面圍墻上開了兩扇木格子的大門,外面是一條臭水溝;西面砌了一個燒松香的老虎灶,煙囪順著爬高的地勢就地挖成,里面橫七豎八地鋪著蓋房子用的板瓦,以便把熏出的煙子刮下來做寫毛筆字用的墨;北邊擺了幾大口泡鹽梅、泡黃連用的木缸和晾曬的篾笆;院子里還堆放著收購來的木料。好在那時人不多,何況大多數人還是舍不得買那一毛錢一張的“全票”和五分錢一張的“半票”。所以不算擁擠。
一個“門”字型的木架穩穩地栽在院子西面。用繩子掛上銀幕(掛銀幕的時候就像升五星紅旗一般,銀幕下會聚集很多興奮不已的孩子們);銀幕桿往南十幾米放一張桌子架放映機,桌子邊順著桌腳綁上一根立起的竹竿。上面連接著一個電燈泡:發電機擺在院子外面,用一根黑黑的電線和放映機相連:馱放映機的牲口就拴在合作社的馬廄里。
一切準備就緒之后,開始清場,然后大門緊閉。只把開在大門上的一道小門打開,一邊一個人把守著開始收票。
那時候家里很窮,兄弟姐妹又多,買一張半票的錢還要跟父母磨幾天。得知要來放電影,但是電影隊還沒來時,那往往就是最煎熬的時候。我和幾個小伙伴經常到路口張望,聽到馬叫都會跑出去看看。
偶爾也有要不到錢的時候,看到別人撕了票進去,心里那個癢癢,簡直比什么都難受。也曾有小伙伴約我去“翻圍墻”,但素來膽小怕事的我一直不敢。有一次,約我的人被抓了個正著,說是要交給老師,我看著他苦苦哀求的樣子,心里暗自慶幸,如果我跟了去,那多丟人。
我們最喜歡看的是“戰斗片”。看過之后,幾個人還要在上學放學的路上講上幾天。那時候,好多臺詞都記得清清楚楚,像《偵察兵》:“你們的炮是怎么保養的?太麻痹了!太麻痹了!宇宣,你喝大粕好嗎?這瓶茅臺給德彪……他罵我是吸血鬼,還罵我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還罵我是蔣匪幫的狗腿子。今天該是我報仇出氣的時候了!”
《閃閃的紅星》:“各位父老鄉親,想不到吧?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這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過去誰拿了我什么,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什么,給我吐出來!”
《英雄兒女》:“……為了勝利,向我開炮!”
我最崇拜的演員是王心剛和田華搭檔簡直是絕配。還有王曉棠、謝芳、秦怡、張良、趙丹。印象都很深。
1965年我到巍山讀高中。當時的巍山城里有個“大禮堂”,幾乎天天都有電影放,那種誘惑用“心癢手抓”來形容也不為過。無奈囊中羞澀。很少去光顧。好在縣城里駐了個解放軍步兵團,每個星期六都要在“大操場”放廣場電影,我就跟著學校排隊去看那不出錢的電影。每次都是部隊列隊喊著口號來,占好中間位置,放好背包坐下,老百姓才能找地方看。開映前,部隊連與連之間相互拉歌,什么“猛虎連,來一個,來一個,猛虎連!”、“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不唱歌對不起……呱唧呱唧”。你剛唱罷我登場,歌聲、掌聲、拉拉隊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據說那時的巍山是女多男少,那些個大姑娘小媳婦總愛往部隊那邊擠,有幾個膽大的還寫好“戀愛信”悄悄塞給當兵的。部隊首長發現后采取了措施:部隊坐好后,四周留出一圈一米多寬的“隔離線”,外面才能讓老百姓坐,哨兵還要在隔離線上來回巡查。在這里,我又看了《野火春風斗古城》、《打擊侵略者》、《紅色娘子軍》、《兵臨城下》、《柳堡的故事》等一些好電影。
文革中,除了“三大戰”,幾乎所有的故事片都被打成“封、資、修”的黑貨而被封存。1968年,巍山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我被抽調到縣革委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當時的宣傳隊、文化館、新華書店、電影隊同屬“文化單位革委會”,我們天天混在一起,開批判會也搞在一起。漸漸地,我跟電影隊的人便處熟了。不僅看電影不用買票,而且時不時還纏著石師傅,跟他學習怎么發動發電機。有時到附近公社去放電影,我還能“獨擋一面”,專門負責發電。只可惜,那時放的、看的,除了“三大戰”,就是“八個戲”,最多加映一兩個《新聞簡報》,或者是那個百看不厭的西哈努克在表演。
說來也怪,頭天看電影看得發誓賭咒,第二天照樣又樂呵呵地跟著去看電影,雖然心里期望著看好電影的夢想一次次破滅。卻在行動上無法克制,只要聽到有電影看,再難看的電影,依然會博得陣陣喝彩。
1969年初,縣革委宣傳隊解散,我下鄉當了知青。鄉下的生活顯然比城里枯燥得多。每天晚飯后,要么就著月光吹吹笛子,要么帶上房東家的兒子,背上氣槍,拿上手電去打鳥。偶爾聽到有附近村子放廣場電影的消息,幾個知青,約上村里的幾個年輕人,男男女女一行十幾個人,硬是跌跌碰碰地走幾公里的田埂路,去看那看了無數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電影。幾個月后,為了“慶九大”。縣宣傳隊重組,我又回到“近水樓臺”的“文化單位”。繼續著我的電影夢。
二
1970年我參軍到了部隊,開始在高炮六連當文書,期間參加了師政治部舉辦的“新聞報道培訓班”。1971年我被抽調到團宣傳隊。宣傳隊和電影組隸屬團政治處。在野營拉練中,我們與電影組的人朝夕相處,遇到沒有演出任務時,我經常去電影組幫忙,從車上搬機器、架銀幕、拉電源,臟活累活搶著干。在那里我加入了共青團。
野營拉練結束后,電影組那位和我同年入伍,擅長寫“兒童文學”的大個子河北兵被軍區炮兵司令部調走,團政治處準備在全團新兵中選一個“長得精干、字寫得好、普通話比較標準”的人到電影組補員。這樣,我便鬼使神差地來到電影組當上放映員,圓了我的電影夢。
當時的電影組一共三個編制。一個干部兩個兵,組長暫缺。老兵姓李,北京人,本來部隊準備提他當電影組長,并承諾提干前先給他解決“組織問題”,但那時的“安置政策”是:“戰士哪里來回哪里去”,“干部統一分配”。加上李師傅的父親和準岳父都是地師級干部,家庭條件比較好,他怕提干后干上十年八年轉業回不了北京,所以“寧愿不入黨,也不愿提干”。晚他一年的兵姓蒙,來自江西農村,高中文化,腦子靈活,字也寫得好,政治處里有好幾個干部又是他“老鄉”,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重點培養對象,是電影組唯一的黨員。
初來乍到,我借來一套業務書認真學習。更多的時間就是幫政治處那幾個干事抄寫他們寫的材料。
兩位老兵各有各的性格脾氣。李師傅耐心教我倒影片和檢查、鑒定、修補影片,還教會我掛片子、放電影:蒙師傅在我剛進電影組幾天就安排我寫一個“熱烈歡迎紅河州歌舞團蒞臨我部慰問演出”的布標。好在“文革”初期我在南澗文化館做過臨時工,在制作展板過程中,老師給我講過美術字的結構和筆畫規律。后來在“紅海洋”活動中還牛刀初試,有過幾次書寫經歷。所以我把布標字寫好,和老兵一起剪好,別好后,剛剛把布標掛到禮堂舞臺的前上方。正好政治處的戚副主任帶著曾股長(宣傳股長)、夏干事(文化干事)、黃干事(宣傳干事)來檢查,都說寫得好,間架結構穩,字體規范,較之“小蒙”寫的字,倒顯得大氣。
就在我進電影組一個月后,在李師傅指導下放二號機還不到10場,有一天上午,蒙師傅就出了個擴音機“無聲故障”的考題讓我排除。說實話,我雖然學了一點理論,但真刀真槍的故障排除還從未經歷過。看著那花花綠綠的電阻器、電容器,變壓器、電子管,還有那密如蛛網般的線路,我頭都大了。加上我知道理論上有兩組420V的高壓,更是心里發怵。不知道該往哪里著手。
蒙師傅布置完任務后揚長而去;李師傅本來就文化基礎薄,對擴音機也是帶通不通,似懂非懂。我只好硬著頭皮對照線路圖一個元件一個元件的查,用三用表順各個電子管的八個腳一極一極地測。忙碌了整整一個上午,還是未能排除故障。睡午覺時,躺在床上,腦子里還是在想上午檢查的情況和各個數據。突然,眼前一亮,有了。我翻身起床,燒上烙鐵,把一個被蒙師傅取走的電阻找來重新焊上,然后開機,插上話筒,用嘴試著吹了吹,話筒里面傳出了我的吹氣聲,終于響了,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心里無比高興。
那個年代,我們用的放映設備是一套八一電影機械廠生產的、專供部隊使用,而且經歷過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回來的老機器——“解放103型”35mm移動式電影放映機、“1101型”二行程發動發電機。由于年代久,又是在惡劣環境下顛來簸去,所以故障率特別高。尤其是那臺25W電子管擴音機,幾乎是放三場修一場的比例,有時出去拉練路途長一點,路況差一點,那就是逢放必修。電影車不固定,由汽車連、指揮連、警衛排臨時派。
我們的固定放映點有團部、兩個高炮營、一個雷達站、一個生產連隊。流動放映點主要是每年一次野營拉練的駐練點。五個固定放映點中,只有團部有一個禮堂,但因為附近的老百姓經常來“蹭電影”。禮堂根本容納不下,所以只是在放“內部電影”(如《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和“軍教片”(如《火箭布雷》、《空降兵打坦克》)時偶爾用一次,其余絕大多數時間還是放廣場電影。不固定的放映點有友鄰部隊、附近工廠、農村。那時的“拷貝”比較少。新一點的片子和好看一點的片子都需要“跑片”。
到電影組三四個月后,我參加了師部舉辦的“放映員初訓班”學習三個多月。培訓班開設《電工基礎》、《電影放映機》、《放映擴音機》、《發動發電機》四門課程和“三鏡頭幻燈機”、攝影理論等講座。實習和故障排除以各自使用的機型為主。由于愛好,我學習特別刻苦,不僅認真聽講,記好課堂筆記。而且每天還整理學習筆記。滇南的氣候熱得要命,但別人睡午覺我不睡,每天中午穿個背心、短褲。在教室里看書、畫圖,分解、裝配機器。通過系統學習,我能蒙著眼睛拆、裝放映機,并調試到符合技術要求;能準確背熟放映機每一個齒輪的齒數、運轉方向,每一個滑輪的直徑和作用;能默畫出擴音機線路圖,放映機傳動系統圖、輸片系統圖;“歐姆定律”演變的十二個公式更是倒背如流,運用自如:能排除放映機常見故障、擴音機簡單故障(比如“無聲故障”)。結業考試,四門功課全部在97分以上,平均分98.5分。
培訓結束回到電影組,蒙師傅繼續掌握一號機和擴音機,我單獨操作二號機,李師傅負責聯系交接影片、安排放映點、跑跑片、遇到故障時修修機器。由于我的“兵齡”最短,平時的倒片、鑒定、修補影片和放映中的倒片由我包干。“新兵打下手”這也是電影組的老規矩。
每個放映點的接待人員和觀眾都很熱情。裝、卸車,掛銀幕、接電源,都有人協助。茶水、夜餐那更不用說。即使遇上等片子、中途修機器,都很配合。要么組織拉拉歌,要么原地休息。最難忘的是到河口去給守衛那里的二營放電影。我們每次去都帶上幾部片子和照相機。白天,我在高炮陣地附近選好位置。對著越南方向或“中越友誼大橋”取好鏡頭,讓戰友們蹲伏在草叢中,一個個移動到我事先指定的位置,站立、舉槍。我迅速按動快門,為戰友定格難以重復的瞬間。晚上,在營部和友鄰部隊、建設兵團放電影。河口是云南有名的“火爐”。兵團還專門安排一兩位女知青用她們自己編的。特大號的篾扇子為我們扇風。有趣的是,有一次受當地政府的邀請到屏邊去放電影,事先我們不知道他們那里的電是靠白天蓄好的一塘水發的,水放完就完,所以也沒帶發動發電機。結果第二部影片《琛姑娘的松林》剛放了一段,水沒了,電也沒了。觀眾口哨聲,呼叫聲此起彼伏,有些人直接來要求我們接著放,但我們毫無辦法,在觀眾的惋惜聲中黯然離開。
還有一次擴音機故障,李師傅負責修,我在旁邊遞工具,可搗鼓半天,還是不行。李師傅說只有到友鄰部隊借機器,可他剛剛開車走,蒙師傅在一旁看得清楚,記在心里,只一烙鐵下去,好了。等李師傅借機器回來,我們已經放了兩三本片子。
當時朝鮮寬銀幕電影《賣花姑娘》剛到,因為分給我們的片期只有一天,所以政治處決定在團部禮堂白天晚上的放(白天放映,禮堂的窗子可以用黑窗簾遮擋),把兩個營的兵分批拉來看。結果消息不脛而走,老百姓涌入團部,與哨兵發生沖突,以致以后越好的片子越不敢在禮堂放。
1973年1月,春節臨近,由后勤處一位副處長、一位裝備股副股長帶隊,到硯山慰問我部在那里挖錳礦的官兵。13日,在返回的路上發生車禍,電影車沖出公路滾下山谷。在離公路89米的地方卡在懸崖邊。車上拉的人、機器、面粉撒落一地。我隨著慣性在陡峭的山坡翻滾。邊滾邊抓。也不知抓到什么,身子穩住了,上下一看,車子在我的下方卡住,但車廂、駕駛室全都沒了,只剩下四個輪子挑著一對大梁(嘎斯63型)。
我長舒了一口氣——總算沒有犧牲。這時,旁邊的副股長也穩住了,只聽他急切地跟我說:“小楊,趕快去救小常(河北兵,汽車連配給我們的兩名駕駛員之一,但車禍時是另一名駕駛員開)”。我一看。一個兵頭插在面粉口袋里,脖子和頭一樣粗,一動不動地躺著。我趕快上去把他從面粉口袋里拉出來,拍掉臉上的面粉,摳出鼻子里面的面粉。解開他軍裝最上面的兩顆紐扣,將他頭朝上,兩手放開。仰面躺在山坡上,看到他恢復了呼吸,然后去找李師傅。將他背上公路,堵下一部地方車,請他們將他送往59醫院。
這時,有幾部地方車路過停下,老百姓下來幫助我們搶救傷員。我趕快去找蒙師傅,找到蒙師傅時,他的頭腫得差點認不出,我將他背在背上,兩位老百姓趕忙過來,一位朝前拉我。一位在后面推我,終于把蒙師傅背上公路。我剛想坐下喘口氣,就有一位老百姓過來跟我說:“老兵,你那位戰友快不行了,你趕緊把他送進醫院。”我過去一看,這不是我們團的兵,他是613團挖錳礦的一個病號,搭我們的車出來看病的。他哼哼唧唧喊腰疼,我以為是腰椎骨折,喊他堅強些,不要在老百姓面前丟人現眼。然后把他抱進地方車駕駛室,雙手抱住他雙手下面的胸背部,往上使力,盡量減輕他腰部的受力。
車慢慢開行。他力氣很大,又蹬又掙,我用盡全身力氣才能把他托住。到了59醫院,廣播早已通知,醫護人員提著擔架在大門前守候。見我們的車一到,馬上過來兩副擔架,我跟他們說,趕快搶救這位重傷員,請一位同志領我去給部隊打電話。電話那頭團長剛聽我匯報到出車禍了,馬上問有沒有人犧牲,我說現在沒有。團長哽咽了,讓一位參謀聽完我的匯報。
打完電話,護士扶我到病房休息。這時我才發現,穿在身上的大衣、棉衣全不見了;挎包也丟了;頭上的帽子沒了帽徽,而且也不是我的:腳上穿的鞋子一只三號,一只四號。躺在床上,喊護士來給我挑刺,護士挑完刺剛走,又發現一棵,又喊護士來挑,這樣反反復復,讓護士跑來跑去,后來她跟我打招呼,原來是我們一年的兵,姓宋,她父親當過州政府秘書長,她媽媽下放到南澗,她是我妹妹的同學,我們認識的。
背人的時候不知哪來的力氣,可躺在床上我才覺得真累了,兩個墊褥被我的汗水濕透了一個。護士忙把濕墊褥換了。
不久,護士告訴我:“你送來的那位戰友犧牲了!”
我說:“怎么可能,他只是腰椎骨折,力氣還是那么大。”
護士說:“他脾臟出血,我們盡力了。”
我在醫院住了一晚就回部隊了。隔了一天,一位參謀來通知我陪團長去看車禍現場。到了現場一看,是一個八十度左右的陡坡,團長年紀大,參謀不讓他下去,我們幾個人只有蹲下身子。拉著茅草,慢慢挪,才能下去。真不敢想象當時背著人是怎么上來的。
傷員慢慢痊愈,陸續回部隊后,那位副股長、還有那位姓常的戰友等幾位“難兄難弟”積極為我去請功。
立功之后,政治處多次動員我寫《入黨申請》,我的回答是:老兵一天不入黨,我就一天不交申請書。直至1974年政治處決定讓李師傅復員,之前通過、批準了他的“組織問題”,我隨后遞交了申請,不到一個月就人了黨。當然,這是后話。
以后,蒙師傅提了干,我被選送到“昆明軍區炮兵司令部放映骨干培訓班”(中訓班)繼續深造。骨干班學員是來自各部隊的電影隊(組)長、準備提干的老兵以及軍工系統的地方電影院老師傅,一共二十多人。我們高炮65師一共去了五個人。學員們各有各的優勢和特長。昆明7321工廠來的賀師傅、沾益某廠來的楊師傅,自稱是當地赫赫有名的“電影師傅”,“手到病除”的高手,而且事關今后“技術等級”的定級問題,所以剛來時傲氣十足,似有不把“當兵的”比下去誓不罷休的氣勢;但部隊的同志也不甘示弱,占著年輕,接受能力強,能吃苦的優勢,個個憋足了勁,一定要把真本事學回去。
課程設置跟初訓班差不多,但學得更深、更細。我知道培訓班上臥虎藏龍,所以學習更加刻苦、努力。學習的氣氛很濃,理論和實踐(主要是實際操作和故障排除)分開考。因此“中考三六九,小考天天有”,根本沒有星期天。可無論小考、中考;理論考、實踐考,考來考去,前五名全被我們65師去的人包了。師部的李佐民、613團的陳剛、614團的我,輪流在前三名上轉;623團的王建華、616團的小趙穩坐四、五名。
也難怪,小李是大城市來的(北京人),當兵前就能把半導體收音機的安裝、修理當作玩:小陳是高干子弟,雖然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但和我一樣,都是高中生,而且最年輕。開始的理論考試成績下來,我們都是98分上下,賀師傅他們最多也就七八十分。地方的師傅有點不服。說是“實際操作見分曉”。誰知“年紀不饒人”,他們哪是我們的對手?就拿“掛片子”來說,從上一本片子片尾脫離供片盒開始計時,到片尾進到收片盒,然后取下上一本片子(按操作規程不準拉片尾),裝進帶軟包裝的片盒,取出下一本片子裝上,搖到“開機信號”,檢查完畢。賀師傅他們一般是兩三分鐘(一本片子的放映時間為9—10分鐘,所以2—3分鐘裝片也合格,還算“比較快”),而我們去的五個人,全部在一分鐘左右完成。我在55秒至56秒之間,最多58秒。賀師傅他們嘆為觀止,但還是不服氣,一定要“故障場上見”。
擴音機的故障排除最考人。賀師傅他們進去一個抓頭皮一個,好像懵了一樣,精神高度緊張,結果有的能排除,但超過規定時間:有的干脆就放棄了。我們進去可就不一樣了,按檢修步驟,先插上烙鐵。取出電表在不通電的情況下量量有沒有短路現象,沒有短路再插電源、打開開關,“音輕故障”(聲音小)按“前置放大”、“混合放大”、“(推挽)功率放大”的順序檢查;“無聲故障”按倒過來的順序檢查,基本上做到穩扎穩打,萬無一失,快速排除故障。
三個多月的培訓過得很快。期間,《火紅的年代》、《金光大道》、《青松嶺》剛剛上映,我們到“國防劇院”參加了昆明的“首映式”。
結業考試的成績下來了。李佐民第一名;我因有一題計算題在檢查時用擦膠擦過、改過,“卷面不清潔”被扣了一分,屈居第二名:陳剛第三名。王建華還是第四名:小趙第五名。后來,賀師傅向我討教學習的經驗,我如實回答:“笨鳥先飛”。
我學習回來后,正好趕上部隊換裝。我們上交了老機器。領回了一套全新的“解放103型”放映機、擴音機和“解放10A型”四行程發動發電機。放映機的光源已由以前的“白熾燈”改為“銦燈”,接收光學信號轉換為電子信號的“光電管”改為“硅光電池”:擴音機由過去的電子管整流改為晶體管整流。使機器更輕便。性能更穩定,聲光效果更好。
新機器一到,大家都圖新鮮。有一天上午,蒙組長搗鼓那個發動發電機,我和李師傅在旁邊看。有時遞遞工具。可是新機器捉弄人。一拉就能發動,聲音也正常,就是發不出電。弄了半天,發電機像是故意罷工,電壓指針一直為零。其實我邊看邊琢磨,心里已經有底。
午休時(電影組輪流放廣播,此時正好輪到蒙組長住廣播室),我問李師傅“要不要我們兩個把發電機弄好?”李師傅當然求之不得,立即翻身起床。我請李師傅先把發動機發動好,我退出手電上的一節電池用一根表筆(線)連接在“高壓線包”兩端。只見電壓表的指針慢慢向右升起。我退出連接,看著指針慢慢走到220V停住。事后李師傅問我是怎么回事?我說:發電的原理(前提)是切割磁力線的相對運動。正常的發電機,通過繞在轉子上的線圈與定子上的磁場相互作用,電就發出來了。而我們這個發電機是全新的,可能是永久磁鐵沒有充磁,或者是失效了,所以盡管有“相對運動”,但沒有磁力線,不產生“切割磁力線運動”,哪能發出電來?我之所以給“高壓線包”通上1.5V的電,是人為制造一個小的電磁場。這樣轉子就能在磁場中作相對運動,電就慢慢發出來了,發出的電又給“永久磁鐵”充磁。充的磁場越強。發出的電就越多,電壓不就慢慢升起了來了嘛。不過轉子上線圈的匝數和發動發電機的轉速是固定的,“永久磁鐵”充磁后也會達到“磁飽和”,所以發出的電壓是恒定的,220V。
回部隊半年后,小李、小王、小趙、小陳陸續提了干。我因“文革”的耽誤,當知青又在農村蹉跎了兩年,參軍時年紀大,當時已經超過了提干的年齡,所以兩年半以后復員。倒是陳剛,一直干到31師政委、昆明陸軍學院政委、貴州省軍區政委、少將軍銜,是我們那批放映員中的佼佼者。
三
政治處曾紹宗股長是福建人,與我素昧平生,但卻是我遇到的貴人。我在團宣傳隊時,他就是宣傳股長。雖然新兵與“營級干部”之間,沒有更多的接觸,我到電影組也是戚副主任找我談的話,但是送我到師部和軍區炮兵參加培訓是他的安排。我遭遇車禍那次,剛好他正在辦理家屬隨軍后的安置,所以沒有帶隊去,但是我才從59醫院回來,他就請我到他家吃飯。為我壓驚。我入黨的時候他和蒙組長是我的介紹人。
當時,蒙組長的“介紹人意見”寫得“很不怎么樣”,他讓他重寫。“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他轉業前,我用我學到的無線電知識,自己繞變壓器,安裝了一臺電子管收音機送他(計劃經濟年代。收音機是緊俏商品,憑票供應);2010年,他從漳州市副市長崗位退休,我趁出差機會帶著云南特產去看他,他帶著夫人和兒子為我接風洗塵。李師傅與我更是“患難之交”,雖然他跟我同齡,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一直很敬重他,與他保持聯系。2008年,他和同事一行十人到大理旅游,我請他們吃飯。席間,他的同事說:“李主任(他是北京608廠廠長助理、辦公室主任)一直在我們面前念叨,說您是他的救命恩人”。那天。李師傅給我孫子1000塊錢,他們老大(廠長)給了我兩副(高檔)“堡圣牌”偏光眼鏡。蒙組長,雖然為人有點“那個”,但那都是年輕時的事。后來他從贛州一家文化企業下崗,2009年還專程來大理看我,感謝我的救命之恩。陳剛,雖然多年沒有聯系,但有一次我因工作關系到師部,他還主動問我“有沒有什么人需要關照”。
我在部隊帶過兩個徒弟,新兵小張和女兵小余。
小張來自河南洛陽郊區,人長得精干,但心不在電影上,字也寫得歪八斜扭。也是“憨人有憨福”吧,退伍時“支援石油會戰”去了四川自貢,混了個電影隊長。小余本來跟我不在一個部隊,那年軍區搞“樣板戲”匯演,師部為排練《智取威虎山》從北京特招了幾個兵,她。就是招來飾演衛生員白茹的。幾年后師宣傳隊解散,演員們分散到師部下屬的各個部隊。小余的媽媽是中央廣播合唱團的演員,要求她改行學放電影,以后復員回北京,一個系統好安排。這樣就陰差陽錯地當了我的徒弟。
我們團級單位屬“基層部隊”,清一色的男兵,有人形容說,連營房周圍跑的耗子都是公的。高挑、苗條、白凈的女兵小余的到來那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在營區成了特大新聞。她哪都不敢去,白天就在我的指導下學習電影相關理論,修補影片,倒倒片子,開飯時跟在我后面到“大灶”去吃飯,晚飯后要么和我們一起去放電影,沒有放映任務時也大門不出,二門不進,躲在電影組看書,我(用有線廣播)放完“熄燈號”后,送她到招待所。小余當我徒弟幾個月,我從來不問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復員去了哪里。去年,我寫了一篇《我教白茹放電影》的文章刊登在報紙上,有一位原師部宣傳隊的北京兵通過戰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寫的“小田”真名叫余景麗,復員回北京了,見過幾回。但沒有聯系。
張愷悌、巍寧夫婦曾經是我服務過的電影觀眾,但以前我們并不認識。還是有一次張先生作為駐聯合國訪問學者歸來后偕夫人造訪大理,州外事辦和單位派我去接待。交談中才知道,二位曾經是從北京下鄉到云南河口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共同的知青經歷,同一塊銀幕下的放映員與觀眾,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共事幾天,合作愉快。其間還一起回憶了在橡膠樹林邊看電影還要涂抹“萬金油”防止“小黑蟲”叮咬等趣事。奇怪的是,二位回去之后,我便每個月收到一期《大眾電影》雜志。一打聽,原來巍寧老師在《大眾電影》雜志社工作。于是,我又得寸進尺,將我寫的《電影夢難圓》在《大眾電影》2005年第8期刊出。也是“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張老師后來當了“中國老齡科研中心”主任,于是,我撰寫的《對開展老年文藝活動的思考》等論文,又陸續在《老齡問題研究》上發表。
由于我們經常到部隊附近友鄰單位放電影,地方的電影隊也常來我們團部慰問放映。所以我跟當地的一些廠長書記和工會主席、放映員也熟悉了。聽說我要復員,幾個單位都來做我的工作。1976年,我退伍到一家中型企業。本來說好是去放電影的。可誰知,廠里準備安排我當“武裝部長”。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我不想介入地方派性斗爭,所以說什么也不干。但來也來了,廠里只好安排我到工會,以后又調整到辦公室,一個人兼廠辦、黨辦兩個辦公室的事務工作,掌握黨委和廠里的公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落實政策”的工作量很大,我負責起草廠黨委、廠行政上報的所有材料,并負責“過目”“運動辦”、“落辦”準備上報的一切材料,拿不準的地方直接向書記請示,一般的由我把關。此間,由于我寫的材料得到上級機關和有關部門的認可,有那么一點點“知名度”,市公安局、市委辦多次發函想“借調”我。但我放不下電影,魂牽夢縈的還是電影。幾經周折,1980年,我終于如愿以償調回家鄉放電影。
我所調入的企業在郊區,電影院剛剛落成,使用機器也是剛剛配備地方的“解放103”。已經有兩名年紀不輕的新手。
廠里的書記是個“老資格”,在過省委組織部工作,不知什么原因調來調去來到廠里。他硬說我的《放映員合格證》“少了一頁”,所以只安排我打雜,寫海報、倒片子、跑跑片。還是州電影公司領導看了我的《技術檔案》后,把廠里的書記、工會主席叫去,指定讓我負責電影院的業務、技術工作。大概是廠礦電影院在業務上接受電影公司指導,同時片源上又有求于電影公司,我才在書記極不情愿的情況下安排上機。并當上“電影組長”。
當時,正值中國電影的黃金時期。大理市區的影院都是每天三四場,場場爆滿,呈現“萬人空巷,一票難求”的局面;我們郊區影院也是“一個拷貝幾家跑,影院門前像趕街”。尤其是武打片《少林寺》,創造了在我們影院每天放五場的記錄。我從車間工人的影迷中臨時借用了幾個人加強場務工作,但這時的禮堂人滿為患,連過道上也擠滿了人,趕也趕不走。我只好讓場務配合票務去“補站票”,并在取得工會主席同意的情況下,用補來的錢買了一輛跑片用的“永久51型”加重自行車、每人一只手電筒,還給跑片的人配備了雨衣、雨鞋。
離我們影院不到1000米有一個“公社電影院”,由于地處小街中心地段,更是加班加點地放,影院門前熱鬧非凡。可放映員都是大理縣電影公司派來的年輕人,技術很不怎么樣。每每遇到機器故障,都要請我去修。甚至連他們公司經理坐鎮時,排除不了的故障也要來請我。久而久之,“楊師傅”的名聲(在小街)大噪,公社影院只要一出現“白布電影”或“無聲電影”。場子里總有人在噪聲和口哨聲中對著機房大吼“去請楊師傅,去請楊師傅”。也許是“緣分”吧,每次只要我去,都沒有讓觀眾失望。
這時聽說省電影公司分給大理州幾個“指導放映員”(放映技師)的名額,但要統一到昆明去考。我到州電影公司要求報考,但州公司領導和管技術的人說:“我們看過你的技術檔案,你考起絕對沒問題,但那樣就占了“政府隊”(當時把縣市電影隊稱作政府隊,把廠礦隊和農村隊打入另冊)的名額,不行,你下次再找機會”。
可是事情遠沒有結束。因為我們廠書記廠長關系微妙,我又是通過廠長調來的,所以書記時時處處找我的茬。有一天,書記把我叫到辦公室,心平氣和地問我:“小楊,昨晚上這個電影我在市電影院足足看了兩個小時,咋個你一個半小時就把它放完了?注意,今后放慢一點”。
我那時年輕氣盛,便直言:“書記,放映機馬達轉速每分鐘2880轉是額定的,傳動系統的皮帶輪直徑、齒輪齒數也是固定的,輸片系統每分鐘拉過24幅畫幅(膠片)也是不會變的,我想放快放慢都做不到。”
結果被書記很赳了一頓。說我一點也不謙虛。時隔不久。工會老主席喘著粗氣蒞臨機房指導工作時說:“小楊,我看你的技術蠻好嘛,你想想辦法,能不能放成‘立體聲電影?”
我說:“主席,立體聲一般是多聲道錄音,多聲道還原,才能欣賞到立體聲音樂的展開感,也就是交響樂隊的高度感、寬度感和深度感。而我們的影片只有一條光學聲帶,擴音機也只有一條放大線路,不可能放出立體聲。”
老主席卻也實在,笑著說:“你看你看,又謙虛了不是。我知道你行……”
我正欲解釋,老主席轉身,倒背著手下樓而去。老主席的表揚讓我感到有些沉重,擔當不起。他畢竟是我的頂頭上司啊,雖然外行,卻沒有壞心,迎合一下總沒有壞處,反正我怎么弄他也不懂。于是,我在擴音機輸出端加了個“分頻線路”,搞成“仿立體聲”。把分出的高音頻部分供給高音喇叭還原,高音喇叭安在影院臺子的中上方:把分出的低音頻部分供給低音喇叭還原,低音喇直接放在臺子中間。
搞好后,我去請老主席來欣賞“仿立體聲”,并事先給他介紹了“欣賞要領”。
老主席滿面春風的來了,才聽了一首歌就夸我:“不錯不錯,我就說你行嘛”。
大概兩三個月以后吧。我正在專心致志地放電影,老主席又親自駕臨:“把聲音開大一點,下面后排的觀眾聽不到”。
我耐心跟老主席解釋:“我們的流動放映機不能和正規影院的座機相比。現在音量已經開到最大,但由于擴音機功率小,實在沒有辦法。不過明天,我一定想辦法解決”。
第二天,我把150W的廣播擴音機搬到機房,從放映擴音機“前置放大”極取出同期信號輸入廣播擴音機,廣播擴音機輸出端和原來的廣播網相連,用不完的功率接進禮堂,在臺子上方和大門上方左右各接一只高音喇叭。從此,只要禮堂放電影,整個廠區、生活區都能聽到電影里面的聲音。禮堂里就更是吵都吵不贏。讓老主席著實高興了好一陣子。
老主席的高興反而讓我不安。一方面,這樣內行忽悠外行總覺得心里不踏實:另一方面,擔心不知什么時候老主席還會給我出什么難題。
此時,電視的發展日新月異,仿佛一夜之間錄像廳就如雨后春筍般遍布城鄉。電視劇與電影爭奪觀眾的情況愈演愈烈,影院開始入不敷出。在內心的煎熬和不舍中維持了幾年,加上那段時間郊區的治安狀況又比較糟糕,廠礦電影院陸續倒閉。我不得不告別我所鐘愛的電影事業。
也許是“風水輪流轉”吧。多年后我從州級機關退休。有一次老協會活動和州電影公司老協會活動不期而遇。都是老熟人了,免不了客氣、寒暄一番。可這時他們的會長來“拼錢”,一問,“AA制”,我心里一陣陣酸楚。再一聊,老經理的退休工資才二千多元。
想想當年風光一時,曾為我州電影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電影人”。晚年生活是如此結局,同情、憐憫之心油然而生。趁著單位回聘我去“寫志”的機會。我將情況向領導反映。為州電影公司老協會爭取了兩萬元“活動經費”,暫緩燃眉之急。
如今電影科技的發展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我居住的小區離“巨幕影院”不足百米。每天晚飯后出去散步時,我都要習慣性地看一看那寬敞明亮的售票廳。可除了零零星星的觀眾外。幾乎“門可羅雀”,與當年的熱熱鬧鬧,擁擠不堪看電影的場景形成鮮明的對比。我的心中油生了一種莫名的苦楚。
編輯手記:
電影,是根據視覺暫留原理,運用照相,錄音等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及聲音攝錄在膠片上,再通過放映,在熒幕上把運動的時間和空間里創造出來,再現和反映生活的一門藝術,是大眾文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如今,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電影看似已經逐漸淡出了我們的視野。通過楊永德先生的《我的電影情緣》,讓我們看到了,電影曾經帶給我們的諸多快樂與美好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