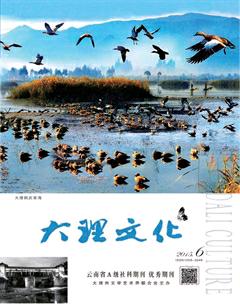平行線
1
更多的時候。日子和日子之間的差異,在我看來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比如眼下,這個猴年也可能是雞年的春節(jié),對我來說就只是幾個平常的日子而已。
讓我心情不錯的,是一場中雪,已經(jīng)下了兩天了,這會兒還在窗外飄零。昨晚,澗河電視臺的新聞聯(lián)播采訪了一位農(nóng)業(yè)專家。是個有些謝頂?shù)哪凶樱瓷先ビ?0歲左右吧。這人攥著拳頭,信心滿滿地說,這場雪百分之百預兆豐年。而我不敢確定。老天爺?shù)氖虑椋挥欣咸鞝斪约赫f了算。
不管怎么說吧,北方的冬天,只有下了雪,才像那么一回事,感覺才對路。半個小時之前,我的老婆出門了,去找她的閨蜜打麻將。我呢,沏了一杯紅茶,坐在窗前,有一搭無一搭地構(gòu)思一個男人的故事。過日子嘛,總要做一點事情的,一直混著不是辦法,是吧?
老實說,對于這個男人的故事,我覺得無從寫起。眼下,我只能確定它將是一篇短篇小說。至于這個男人姓什么,我暫且不提,但必須要說到他的名字:槐樹。由此,我想這個短篇小說的題目,就叫《男人槐樹》吧。
雪下得慢條斯理,像個紳士。我長久地看著窗外,看著看著,我突然就想,坐在那列火車上的男人槐樹,他也一定是長久地盯著窗外吧。所不同的是,我看到的是一片清冷而纏綿的白,他看到的卻是一個盛夏的午后。
那個午后悶熱異常,讓人透不過氣來。天空詭秘地白亮著,繼而又變成了陰森森的鐵灰色。男人槐樹斜倚在座位上,看到窗外的天空越來越低了,像一口巨大的鐵鍋,倒扣著。不由分說地壓了下來。這輛哈爾濱開往澗河的列車,正在勻速前行,遠處的山脊和近處的樹冠,也就勻速地向列車后方撤退。而雷聲說來就來了,轟隆隆、咔嚓嚓,不遺余力、不可一世。閃電這條抽搐著的鞭子,被雷聲肆意地揮動著,天地之間就被劈出一道緊接一道的傷口,腥紅并且詭異。緊跟著,雨兜頭而來,跟個潑婦似的,一點過渡也沒有,直接就下瘋了。大地在瞬息之間就被一團濁白所籠罩,而風也開始趁火打劫了,撒著歡、打著旋,恨不得要把這個它所不滿意的世界,連根帶梢地吹走一樣。
雷聲、風聲和雨聲糾纏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們一股腦地灌進男人槐樹的耳朵里時,一定是我出現(xiàn)了錯覺吧,我也聽到窗外傳來了一陣噼噼啪啪的聲響。猛地愣怔了一下,我清醒了過來——春節(jié)了嘛,有人在放鞭炮,這再正常不過了。鞭炮炸開的聲響,急促、固執(zhí),一氣呵成,是那種沒有起伏的抒情,讓人聽起來覺得累。
接下來,我的手機就響了。我就不由得長嘆了口氣。真的,我特別討厭構(gòu)思小說的時候。有人打擾我。而且,我感覺電話一定會是總編打來的,讓我去報道相關領導頂風冒雪給窮困市民送溫暖什么的,過去的幾年,每一年的春節(jié),我都會遭遇這類的事情,想躲都躲不開。
我就咬著牙,接聽了電話。還好,不是總編打來的,而是一個女士。
我又嘆了口氣,當然是放松的那種嘆氣了,就聽女士說,過年好啊劉編輯,我是張萌。
我愣了一下,隨即想起這個張萌女士,是我曾經(jīng)的一個采訪對象。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她應該是自費出版了一本詩集,名字好像是叫《我的我的我》,也或者是《你的你的你》,反正聽起來很是擰巴。張萌通過文聯(lián)的一個編輯找到了我,要我在我所供職的《澗河廣播電視報》上,給她發(fā)個消息。這年月,文學的日子不好過,詩歌似乎就更難,我就給她發(fā)了個半長不短的通訊,什么出身書香門第啊,在某縣文聯(lián)主辦的全國性征文中榮獲佳作獎數(shù)次啊,等等,好像還配了詩集封面照片和她本人的一張藝術照。哦,對了,應該還附了她一組或者一首詩歌吧,我真的有些記不準了。
我說,謝謝你,你也過年好啊。
張女士說,祝你新年萬事如意,發(fā)財、健康、走運,包括桃花運。
我說,好啊,你也一樣。
我是真的沒心思跟她聊天,就要掛斷電話。就在這個時候,張女士說。劉編輯,前幾天我聽廣播,是交通臺還是生活臺了?反正我聽見你點歌了。
我就笑了。我是三十多歲的人了,點歌?我竟然還有點播歌曲的興致?我就告訴張女士,沒有,我沒有點歌。
張女士說,撒謊的孩子被狼吃!就是你點播的,點的歌是刀郎的《情人》,獻給一個叫獨孤蝴蝶的女子。
我的老天!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真的閑得難受,我撓墻玩好不好?我怎么會去點播《情人》,而且明目張膽地送給什么蝴蝶、蒼蠅?這事要是屬實,而且又讓我老婆知道的話,我老婆不拆了我那才叫怪呢。但我不好跟張女士發(fā)作,我就耐著性子說,一定是你聽錯了,我從來就沒有點播過歌曲,從來沒有。
張女士似乎有了些不耐煩。她說她沒有聽錯,她說我所在的廣播電視報社,跟她提到的交廣、生廣同屬廣播電視局,我點歌是有便利條件的。
我說,是,你說的沒錯。如果我想點歌,不用把電話打到導播間,早上上班時,在通勤車上告訴主持人我想聽什么什么歌,就行了。但是……
張女士搶著說,這不就得了。
我說,關鍵是我確實沒點歌,你以為我腦袋讓傻子摸過還是被驢踢了?
張女士說。劉編輯,你這么說就沒勁了。我想點歌,電話還打不進去呢。你說吧,除了你,澗河還有別人敢叫劉浪嗎?我借他個膽子。
我就一下子沉默了,因為張女士的話提醒了我。據(jù)我所知,在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除了我,至少還有三個人叫劉浪——這跟張女士說的敢或不敢,當然沒有任何關系。我聽說其中一位劉浪是個老者,六十幾歲了,退休之前在市第二人民醫(yī)院工作,好像是內(nèi)分泌科的主任吧。另一位,聽聲音應該是個20歲出頭的男孩子,他給我打過電話,開口就說“我是劉浪”。正經(jīng)嚇了我一哆嗦啊。這個跟我同名,也或者說是我跟他同名的男孩子,當時是要給我提供一條新聞線索,忘了是由于我忙沒去采訪,還是他的線索新聞價值不大,反正我們再沒有了聯(lián)系。至于第三位劉浪,是個犯罪分子,5年前被執(zhí)行了死刑。
我就想告訴張女士。也許是哪個跟我同名的人,在廣播里點播歌曲了。可電話那頭呢,張女士一定是認為我理屈詞窮了。就把電話掛斷了。
我長嘆一口氣,小聲罵了一句,媽的。
2
老實說,張女士的電話擾亂了我的思路。我不知道這篇《男人槐樹》,接下來將怎樣展開。放下電話,我喝掉那杯紅茶,打開了電腦,又打開了Word2003空白文檔。再之后,我耷拉著頭在屋子里轉(zhuǎn)圈,客廳到臥室、臥室到客廳,轉(zhuǎn)了七八個來回,謝天謝地,我總算想起男人槐樹乘坐的那列火車,這會兒該在澗河站停下來了。
澗河站很小,一棟黃色的平房而已,不足兩百平米。槐樹和另外十幾個人走出了列車,一串驚雷剛好在他們頭頂滾過。雨傾盆而下,又霸道又天真,又放肆又單純。那十幾個人縮著脖,撒腿向票房狂奔。槐樹卻停下了腳步。
一眨眼的功夫。雨就將槐樹整個澆透了。雨肆意地打在他的臉上,我們看不清他正在流淚。是他聲嘶力竭的一聲慘叫。暴露了他臉上濕濕的東西,不光是雨水。
槐樹叫喊著的,是這樣三個字:綠葉呀!綠葉呀!緊接著,他就撲通一聲跪在了站臺上,仍舊叫喊:綠葉呀!綠葉呀!
槐樹的叫喊。竟然沒有被風雨完全稀釋掉。向票房跑的人中,有兩個男子停下腳步,回過頭來。其中一個男子停頓了一下,又向票房跑去了;另外那個男子卻回過身來,跑到了槐樹身旁。這人大約30歲左右吧,穿了一件猩紅色的襯衫,經(jīng)雨一淋,就像渾身在冒血似的,有些恐怖,也有些滑稽。
咋的了哥們兒?跪這干啥呀?紅襯衫男子問槐樹。“干啥”這兩個字,在紅襯衫男子嘴里的發(fā)音是“尬蛤”。這樣的口音,表明這個男子應該是東北籍的。
槐樹根本沒有理他,而是繼續(xù)用兩只手掌輪番擊打站臺的水泥地面。邊擊打邊喊:綠葉呀綠葉呀!開始時,槐樹是左手擊打一下,右手擊打一下,再左手。再右手。但這種有序的節(jié)奏轉(zhuǎn)眼就紊亂了,他時而用左手連擊兩下,時而用右手連擊三下,間或還用前額去叩擊。手亂了,嘴卻章法依舊:綠葉呀!綠葉呀!
哥們兒你別整這出行啵?我心里毛個愣的。紅襯衫男子抬手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他一邊說著,一邊倒退著往票房走。
槐樹仍舊沒有理他,仍舊綠葉綠葉地喊著,只是聲音似乎不再那么尖銳和抽搐。
這時候。列車一聲長鳴,緩緩啟動。倒退著的紅襯衫男子猛然看到,槐樹踉踉蹌蹌地站起身來。向列車快步跑去,很明顯,他是要用自己的頭顱去撞擊列車。
還好,就在槐樹前傾的頭顱,距離開始加速的列車只有不足10厘米左右的時候,紅襯衫男子快步追趕了過來。一把拽住了槐樹的后脖領子。又一聲驚雷在他們的頭頂炸響,槐樹的身子被紅襯衫男子扭轉(zhuǎn)了過來。紅襯衫男子一手抓著槐樹的衣領。另一只手狠狠地掄了起來,啪!扇了槐樹一個大耳光。這個耳光實在太響,連傾盆而下的雨水都似乎在瞬間停頓了一下。
你他媽的跟我裝啥犢子!紅襯衫男子大罵。“啥”這個字,在他嘴里的發(fā)音,仍是蛤蟆的“蛤”。
槐樹被打得渾身一抖,似乎清醒了一些。他想拿開紅襯衫男子的手。但紅襯衫男子仍舊牢牢地抓著。
槐樹說,兄弟,謝謝了,松開我。接著,槐樹用手抹了把臉上的雨水和淚水,說,說心里話,我真不想活了。
紅襯衫男子看到火車開遠了,就放開了槐樹。他說,哥們兒,你他媽的都要嚇死我了,我還是先蹤桿子吧我。紅襯衫男子說的“蹤桿子”,是個東北土語。大致是快速跑、逃跑的意思。說完這句話,紅襯衫男子就快步走開了。
可是。走出沒幾步,他又返回來了。
你剛才喊的是綠葉,還是莉葉?紅襯衫男子問。
槐樹反問。你說什么?
你剛才喊的是綠葉,還是莉葉?紅襯衫男子重復了一遍。
槐樹的左嘴角微微有一點上揚。算是笑吧。他說,綠葉。可能是怕紅襯衫男子聽不清,槐樹就解釋了一下,他說,就是綠色的葉子。
我操,嚇我一跳。紅襯衫男子說了這么一句,就嘿嘿一笑,接著他就出了出站口,向火車站斜對面的一幢高樓走去了。
而我知道。這幢十六層高的大樓,它鵝黃的外表在這個冬季來臨之前,已被涂刷成了淺粉色。它是北岸賓館。澗河市的標志性建筑之一。
3
在電腦上敲完上面這些,我就停了下來,點了根煙。真的,我不知道接下來,我該怎么敘述男人槐樹的故事。這個男人的命運,在我看來真是倒霉又無辜。可我該怎樣盡可能平靜和有條理地記錄下來?我正沒有思路,我的手機又響了。
這一瞬間里,我是真有摔碎手機的沖動。我好像在前面沒有交代過,我們報社其實沒有專職記者,記者都由編輯兼著。新聞隨時可能發(fā)生,記者的手機相應地就得隨時保持暢通,這是我們報社的制度之一。摔碎手機的后果,只能是我馬上再買一部新的。所以這樣犯傻的沖動,我只能是動一下念頭而已。
穩(wěn)了穩(wěn)呼吸,我接了電話。
這次給我打來電話的,是一位李姓先生。就在春節(jié)前不久,我們報社舉辦了一次規(guī)模還算說得過去的征文賽事。李先生是這次賽事的冠名贊助商。
過年好,劉編輯。李先生說。
我也說。過年好。
李先生說。前幾天我聽見你點歌了。
我渾身激靈抖了一下,真是他媽的活見鬼,剛剛張女士說我點歌,這會兒李先生又這么說。我說,那不是我,我沒點歌。
李先生說,啊。
我說,嗯。
李先生說。你現(xiàn)在在哪個網(wǎng)吧呢?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來,打翻了煙灰缸。我說,網(wǎng)吧?我在家呢。
李先生笑了,說,劉編輯你真幽默,我在QQ上都跟你聊十多分鐘了。啊,我知道了,你家電腦安上寬帶了啊。上次見面你還說你家電腦沒上網(wǎng)。
我說。我家電腦一直就沒安寬帶。
李先生說,兄弟,這有什么可藏著掖著的?其實吧,我就是想告訴你,壞事人人有,不漏是高手。
我說,你什么意思?
李先生說。兄弟,那我就直說了。你犯不上把場面鋪那么大,點歌給那個啥啥蝴蝶,沒有必要,直接拿下她就是了。一看你就是沒經(jīng)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