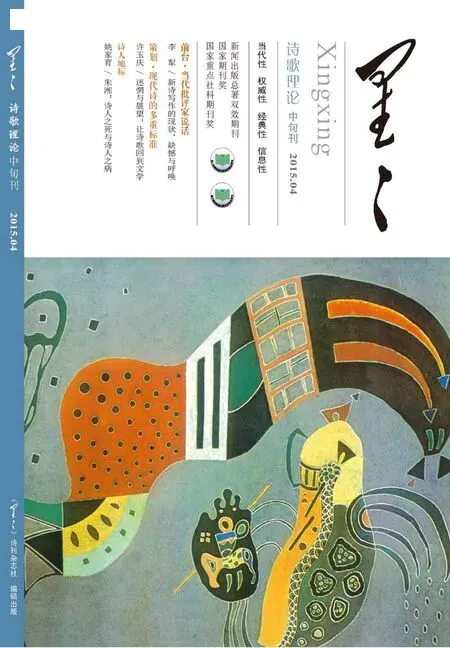跟著詩歌走,心無比純潔
——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傅亮篇
詩人訪談
跟著詩歌走,心無比純潔
——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傅亮篇
訪問者:姜紅偉
受訪人:傅 亮
姜紅偉: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傅 亮:黃金時代主要是源于社會變革給人們帶來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而大學生正是這種氛圍下最易于和善于“噴發”的群體。不管從作品和流派的數量上、從圍繞詩歌創造的群體性活動規模上,還是從對詩歌投入的熱情與探索上看,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這個評價恰如其分。
姜紅偉: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革命生涯”(大學期間創作、發表、獲獎及其他情況)
傅 亮:1982年加入復旦詩社,1983年任第三任社長,同年在《詩刊》發表處女作。1984年,在擔任復旦大學校學生會社團
部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將復旦詩社社刊《詩耕地》升級成為上海市高校第一本鉛印出版的大學生詩刊,并與華東師范大學夏雨詩社社長陳鳴華、上海交大文學社社長張佩星等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大學生詩社,任首屆社長。1981年至1989年,在復旦大學參與編輯大學生詩集《海星星》與《太陽河》、主編《詩耕地》共13期、策劃舉辦大型賽詩會15場、在上海各大高校舉行公益詩歌推廣講座逾百場。先后在《上海文學》、《萌芽》、《飛天》等雜志發表詩作200余首。1988年獲市作協、團市委和《文匯報》主辦的首屆上海青年文學詩歌獎。
姜紅偉:能否請您詳細談談上海大學生詩社的創辦情況?上海高校的哪些大學詩社參加了?詩社社員共計多少人?創辦了什么刊物?舉辦了什么活動?
傅 亮:1984年秋天,由復旦大學復旦詩社、華東師范大學夏雨詩社、上海交通大學文學社共同發起,成立上海大學生詩社。傅亮、陳鳴華、張佩星等成為首屆詩社理事會核心成員。此外還有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機械學院、上海海運學院、華東理工學院、華東紡織學院、復旦大學分校等高校成為成員單位,社員累計超過1000人。當時確定的活動宗旨十分“超前”,即:上海大學生詩社不是“秦始皇”,不會獨裁一統江山,而是推動、鼓勵各成員自由發揮,成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局面。核心成員不是自封的官員,而是一群服務者,理事會的任務,就是負責把定期匯總的上海大學生詩壇最新成果,及時推薦給全國各大雜志的詩歌編輯,幫助大家把優秀作品盡量多地“變成鉛字”;此外,注重詩歌普及和理論的提高,核心成員無私地
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義務邀請、組織著名詩評家、編輯和成功詩人,到各大高校開設詩歌講座、參與詩歌活動。因此,在沒有一本正式的社刊、沒有一個正式的官爵班子的情況下,上海大學生詩社在20世紀80年代,在全國率先成為一個“服務型社團”。其推動舉辦的高校詩歌活動,累計超過了1000場。僅我一人,在2年不到的時間里,就幾乎走遍了上述高校,舉辦講座、參與活動累計不下100次。
姜紅偉: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是如何積極參加并狂熱表現的?
傅 亮:有賽詩會必報名,有詩刊必投稿,有詩歌講座必搶座。
姜紅偉:《復旦風》在80年代是一本很有影響的大學生刊物,作為首任編委會核心成員,能否談談創辦的過程、影響?
傅 亮:《復旦風》是復旦大學20世紀80年代第一本大學生自己創辦的綜合性雜志。創辦的初衷,就是體現當代大學生的思考性和實踐性,表達他們主動參與學校事務管理、主動關切社會發展進程、主動為現代文明社會構建風險力量的精神狀態。1984年秋,復旦大學哲學系幾位學生,在校園里自發創辦了第一個經營性的實體——大家沙龍,不大的簡易房空間里,學生義務參與,自己調制咖啡,自主經營,創造了一個公共溝通的平臺。當時,能在大家沙龍里搶個座,約朋友談天說地,簡直就是一種“晚尚”。正因此,復旦新聞系、中文系的幾位文學、新聞“大咖”聚集在一起,開始籌辦一份正式的學生綜合性雜志,力圖更
高端的延續這種學生自主創造的風尚。此舉由當時擔任校學生會要職的張力奮、傅亮等,制定詳細辦刊計劃,上報校黨委、團委和學生工作部,并不遺余力地請求、呼吁,終于,1985年春,由當時的校黨委學生工作部部長張德明,在一次大家沙龍中舉行的座談會上宣布:經學校同意,《復旦風》正式創刊。第一任主編為張力奮,來自新聞系80級,那時已經畢業,成為新生的輔導員。
與大家沙龍一樣,《復旦風》一律由80級、81級的學生主創,宣布在復旦的學生人文風潮,并未因名人如云的77級、78級學生畢業離校而出現斷層,相反,一些足以留在復旦史冊的創舉,均有這一代學生創造性地完成。創刊號上刊登的政治、歷史、人文、文學作品,均展現了80年代大學生獨立的思考精神,堪稱復旦精英學子聲音的大集結。
姜紅偉:當年,您創作的那首《自行車與五香豆》曾經很受讀者喜歡,能否談談這首詩的創作、發表過程?
傅 亮:成年后,一直在思考自己與父輩的“代溝”問題,兩代人的沖突,也是80年代初期青年學子的共同話題。后來我找到了上述這兩個意象,那是生活中真實的體驗,通過對父親與我對騎自行車是否有風險和喜不喜歡吃傳統食品五香豆所表達出的差異,既揭示了兩代人的理念差異,更對兩代人如何攜手共創明天,表達了理想的設計。這首詩最早在1982年秋天,我在復旦詩社的朗誦會上首次朗誦,恰好當時《詩刊》社編輯雷霆老師應邀出席,當場就表示了贊賞,并將詩稿帶回。后來,該詩發表在1983年6月號的《詩刊》,成為我正式發表的處女作,并被人民
文學出版社收入其出版的《1983年詩選》。
姜紅偉:在您印象中,您認為當年影響比較大、成就比較突出的大學生詩人有哪些?哪些詩人的詩歌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傅 亮:復旦大學許德民,當代大學生詩歌組織的發起者和元老,成立大學生詩社、編輯大學生詩刊和詩集,他的貢獻是開創性的;華東師范大學宋琳和復旦大學孫曉剛,以清新之作開創了一代大學生獨特的詩風,成為經典;哈爾濱師范大學潘洗塵,一個無畏而有情的詩歌使者,他的游走,使大學生全國性的詩歌網絡開始出現雛形,興起了全國性交流的熱浪。
姜紅偉:能否談談您主編《中國當代詩歌總集》這份詩報的具體情況?
傅 亮:年輕時的夢想,偶一為之,但因單槍匹馬、財力不濟,而未能延續,說明了理想與現實的脫節,現在,欣喜地看到有姜紅偉等兄弟,正在系統地完成這項偉大的工作,十分欣賞,敬祝成功!
姜紅偉:能否談談您主編《上海的情緒》這本詩刊的具體情況?
傅 亮:此問題可請陳鳴華先生回答,最為貼切。
姜紅偉:您如何看待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意義和價值?
傅 亮:以“跟著真理走”的主題,對傳統詩歌進行了躍進式的提升;以百家爭鳴的規模與模式,對現代詩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探索與實踐。
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最積極意義,就是體現了人們的政治意識覺醒和詩歌的社會價值。80年代,撥亂反正,人們對頌歌式的假大空口號極度厭倦和仇恨,所以希望詩歌多一點藝術、多一點人性、多一點真實,就像《天安門詩抄》廣為傳誦,就像“朦朧詩”一夜成名,這是很自然的;后來,西方現代派作品來了,人們又在新鮮感中去追隨,又雄心勃勃地認為中國人同樣能創造出現代派杰作,但那時的中國詩人并沒有理解“現代派”的精髓,只是學了一些皮毛,所以詩歌又從過去的假大空一下子發展到五花八門,達到不知所云的地步。
其實,就像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一樣,詩歌的發展同樣會走彎路、入歧途,那時,詩人們的誤區在于,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進行反對是可貴的,但這決不意味著遠離政治,走向另一個極端。艾略特寫《荒原》、金斯伯格寫《嚎叫》,誰離得開政治?面對政治,他們都沒有逃避,而是通過詩歌有效、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與思考。逃避就是無能。一個根本點在于,詩人必須關注現實,這是他最本原的沖動,也是他能力的體現。詩人一旦遠離了政治,其使命感即隨之消失,其“精靈磁場”的魅力與價值也就無從體現,就像《天安門詩抄》和“朦朧詩”,人們首先認同它們的政治意義,才能認同它們的藝術價值,它們在當代中國社會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是政治主題上的,因而奠定了它們的地位,也奠定了新詩的地位。從這一點來看,90年代詩壇出了那么多流派,看似“百花齊放”,而詩歌的
地位卻日益下降、日益遠離社會中心,就并不令人奇怪了。
當代詩人楊牧在《我們身后站著李白》中說:當我們的詩歌越來越變得瑣屑化;當蒼白的面孔被蒼白掩蓋;當空洞得到空洞的支持;當遠離塵世、遠離眾生、遠離人間煙火和生命痛癢成為時尚;當無知、淺薄、奴性和乖張被“先鋒”、“前衛”的絢麗旗幟晃得眼花繚亂,當如此等等的病態自賞,我們的詩壇恐怕要真正到達“最后”的時候了!
在80年代,詩人讓大家“跟著真理走”,每個人的真情都被激發著,那真是一個幸福的年代;到了90年代,詩人一下子讓大家“跟著感覺走”,技巧越來越多樣,詞語越來越花哨,可“感情”變成了“感覺”,人們倒反而對詩歌沒有感覺了。
所以,一個詩人必須樹立正確、健康的世界觀、社會觀、生活觀,這個話題絕對不是老生常談。我的觀點是:詩人首先好好去生活,認真走好人生的道路,然后才去寫作,你的作品才有真貨,才能打動人,才會有“市場”。
政治抒情詩人,更要“東山再起”,走回時代的峰谷浪尖。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當時大學生普遍的“平民”身份。
追憶一下歷史上的中國政治抒情詩人們,被推崇的、被認可的乃至被傳誦的,絕大部分都是“官”。“當官不為民發聲,不如回家賣紅薯”,他們“在位”時,確實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寫下了至今還“名垂青史”的作品。他們當官,因此要寫詩,寫政治抒情詩;他們寫詩,寫政治抒情詩,所以才當官。他們的作品,幾乎涵蓋了相當長歷史時期政治抒情詩作品的主流。
時代不一樣了。誰還期待寫政治抒情詩而當官,他會被懷疑
智商有問題。一個相信自己價值和責任判斷的時代來到,人們不會再盲目傳誦只發一種聲音的詩篇。這時,一個來自生活現實中的尊嚴平民登場了,那就是當代的大學生們。
雖然只是平民,但他們可以分析現實、評價偉人、批判社會、倡導理念,這才是今日中國在文明進程中應該發生的事,這才是一個政治抒情詩人應該要做的事。
更有價值的是,當代大學生的實踐為我們開啟了通往未來中國政治抒情詩發展道路的門扉。他們不具備官員的優勢和渠道,他們的生活與創作均付出了一個平民百姓都在付出的辛酸代價,他們的創作實踐才是真正源于生活的,因為他們因此了解了社會、了解了自我、完成著精神與靈魂的歷練與蕩滌。
這樣的人,應該最反感虛偽、反對趨同、崇尚真實與個性。
這樣的人,才具備當代政治抒情詩人的要件。
那就是:從自我的生活出發,關注現實、思考現實、發現未來、創造未來。
不要一聽政治就“托大”。政治,就是百姓的營生;政治,就是每一個個體為了未來而對時代的冀望和批判。
政治抒情詩不是根據官方的既定政策重復概念,而應該是發自每個具有獨立權利和意識的人內心的真實見解與情感。
這就需要一個開放的語境,擯棄曾經因此而使政治抒情詩飽受詬病、喪失陣地的“傳聲筒”。評論家任仲倫先生說:詩人不是表演團體操的,他們擁有各自的思想姿態、藝術脾性。可以自豪地說,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堪稱典范!
歷史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真實記錄。人類在向文明社會發展的探索和奮斗中創造著歷史。這樣的歷史,需要真實的記錄,目的
是為了評價功過、辨明是非、尋找真理、繼往開來。
文本嚴謹、規范、科學、完整的歷史當然會有人去書寫。但我們還需要另外一種記錄歷史的方式,這種方式更個性化、更有感情色彩、更能發射出生命的亮點,那就是政治抒情詩。
如果說,我們的紀念碑和博物館需要專業的歷史學家,那么,我們心靈的記憶庫和興奮源,就需要政治抒情詩人。歷史是故事,詩歌就是故事情節;歷史是記述,詩歌就是演繹;歷史是數據,詩歌就是旋律;甚至歷史是公共設施,詩歌就是私人財產。詩歌和詩人,給予了我們另外一種解讀歷史的切入點。這就是詩歌的魅力,這就是詩歌不能代替歷史、卻能成為歷史一部分的理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為什么需要詩歌、我們的社會進步為什么需要詩人的原因。
80年代以來,大學生不斷有新作品問世,每次都轟轟烈烈,不僅續寫了中國新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詩的新篇章,而且開拓性地繼承、發揚了通過朗誦誕生效應的優秀傳統,為低迷的詩壇注入了強力。
手捧一本又一本散發著墨香的大學生詩集,也許,我們應該這樣思考:
首先,詩人應該怎樣認知自己在時代發展中的價值與行動。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作為一個詩人,你必須要行動,你必須要用自己的足跡和聲音,融入并且解讀這個不同尋常的時代。在每一個文明進程的歷史節點上,可以沒有飛黃騰達,可以沒有榮華富貴,但是,一定要有詩人的作為!
其次,詩人應該怎樣衡量自己對于社會的貢獻和親和力。
詩人不是政治家,你可以擺脫很多世俗的糾纏,但這不是逃
避的理由。另外,詩人不是快餐店老板,你可以不去顧及大眾的口味,但是,你的行為和創作,必須具備一種澤被天下的人文精神與道德力量,你的作品應該是一種充滿智慧的哲學、一種傳遞時尚的風景。真誠和熱情,是沒有階層之分的,心靈之歌,是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第三,詩人可以是精神的貴族,但這不能成為你無所作為的理由。
我們不能確認,一個善于在午后陽光里熟練地端起一杯咖啡的詩人,他可以擁有不去從事任何現實生活砥礪的特權。我們應該相信,我們要自己塑造自己、自己磨練自己,不會有人因為你是一個詩人,就寬容了你的慵懶和散漫。80年代大學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佐證:他們并非以詩人的單一角色活躍在詩壇,除了創作,他還可以是一個學生、一個兒子,甚至是一個戀人、一個跑腿的打工者;多種角色,轉換在他們對詩歌忠實的追求與熱忱的行動中。這樣的詩人,才可能把他的作品有效地傳播出去,才可能在豐富的體驗中贏得深刻、獨到的人生領悟,贏得人們的尊敬和認可。
今天,在這里,在太陽升起的地方,在一個理想經過無數行動和犧牲終于走向現實的地方,感謝80年代的大學生詩人們,為我們奉獻了一次具有超越意義的激勵和感悟——
他們不斷推出的新作,雖然不能夠完整地涵蓋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巨變,但讓我們真切看到了其中最耀目的亮點;雖然不能夠完全地復述共和國幾代人為理想奮斗的境界和思想,但讓我們深刻地聽到了人們發自內心的代表性語錄;雖然不能夠完美地展現綻放在華夏大地的百花爭艷,但讓我們醒目地把握到了
具有世界影響的地標和關注點。激情的語氣,回蕩的卻是理性思索。
這就是詩歌的魅力,這就是詩歌不能代替歷史、卻能成為歷史一部分的理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為什么需要詩歌、我們的社會進步為什么需要詩人的原因。這也是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經久不息傳遞給我們的啟迪意義。
姜紅偉:回顧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最美好的回憶是什么?
傅 亮:收獲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放歌;我懷念那個素樸但是真實的自由思考與歌唱的大平臺。
姜紅偉:當年您擁有大量的詩歌讀者,時隔多年后,大家都很關心您的近況,能否請您談談?
傅 亮:年過半百,終于認識到詩歌是宗教,是哲學,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嚴肅目標,因此,已經很久沒有動筆寫詩,只是沉浸于漫漫人生,做最實在的事、當最實在的班、盡最實在的義務。相信終于會在某個月色皎潔的時刻,思如泉涌、才情蓬發,寫就更為深沉的詩章。我喜歡在大學時大家送給我的一句話:“生命不息,朗誦不止。”
姜紅偉: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嗎?
傅 亮:當初為了讓上海第一本鉛印的大學生詩刊問世,我曾經數次乘坐輪船,往返于上海市區與崇明島之間。記得在崇明
島印刷廠那個鄉間,當時條件何其簡陋,房間里只有一張木桌、一張板凳,晚間伴著窗外的蟲鳴,我徹夜校對書稿,此刻,內心無比純潔。現在回想起來,這段經歷是我最值得珍藏的,也是我參與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最大收獲,它使一個人感到了追求崇高目標的快樂,這種體驗,無疑將影響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