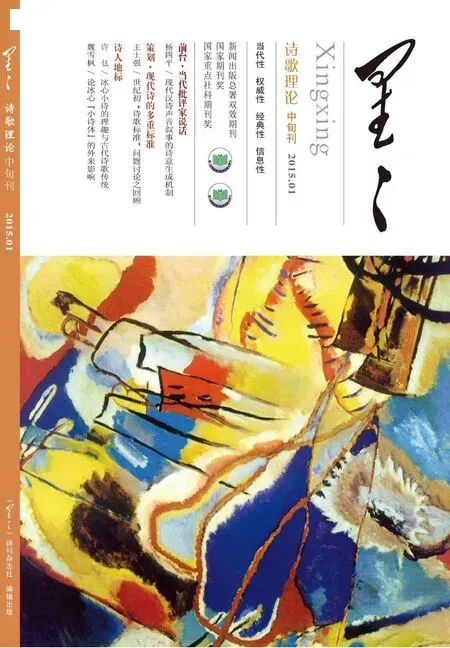冰心小詩的理趣與古代詩歌傳統
許 乜
冰心小詩的理趣與古代詩歌傳統
許 乜
“五四”的一聲驚雷,“民主”和“科學”思潮蓬勃興起,科學理性的文學觀念成為現代作家的普遍信仰。新文藝成為思想啟蒙的橄欖枝,冰心作為其中一員,并不是以狂風暴雨般的犀利言辭鼓動改革舊有文化的思想先驅者,也不是身體力行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者,她走現代知識分子在思想沖擊下由個人轉向大眾的道路:以清新柔和的筆端訴諸文字,用小詩唱出了“五四”狂飆突進的上下求索的青年人的迷茫、苦苦追求的失落。當時掀起的“小詩”熱潮,是詩歌自身發展的規律所致,也是社會發展變化的反映。周作人認為“如果我們‘懷著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復隨即消失的剎那的感覺之心’,想將它表現出來,那么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1]小詩篇幅短小凝練,內容含蓄雋永;在藝術結構上,通常寓情于景,也注重情理結合;在表現形式上,文字抒寫自由靈活,不受格律韻腳的束縛,在濃郁的智性理趣中又透露出清新雅致的恬淡氛圍。小詩是人作為獨立個體呈現后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問,是出于生長期的中國新文學特有的文化現象。冰心的小詩既具有濃郁的審美趣味,又閃爍著智性哲理之光,淡雅柔美的文字娓娓訴來,流淌著意味深長的真諦、醒世的哲理,是魏晉玄言詩和宋代理趣詩的現代傳承。
冰心小詩凝結了細膩的情思,精致的雅趣,而其回味雋永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趣”。“理趣”是指既具有激發讀者的審美趣味又能展現文字的哲理。包恢答《曾子華論詩》時說:“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情,狀理則理趣渾然。”[2](《敝帚稿略》) “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發展的規律,它為語言承載將無形變為有形,理趣詩注重地便是“狀理”的過程,而所謂“趣”則是“生機與靈氣也”,枯燥的道理規律不是直接訴諸,而是借助語言的美感形象地展現。冰心在接觸到生活中的物象后在聯想中結合生存經驗,以文字為寄托,將妙句橫生的話語與回味無窮的哲理結合,便形成了其小詩獨特的審美趣味:精煉的文字中散發淡然幽香,細細玩味便立現雋永的真理。
錢鐘書的《談藝錄》談及“理趣”云:“竊謂理趣之旨,極為精微,前人僅引其端,未竟厥緒。高彪《清誡》已以詩言理。此后有兩大宗。一則為晉宋之玄學。……二則為宋明之道學……”[3]可見理趣傳統在晉宋時代蔚然興盛,為冰心小詩的理趣鋪墊了文學傳統。廢名說:“打開冰心詩集一看,好像觸目盡舊詩詞的氣氛。”[4]周作人也認為“這種小詩在形式上似乎有點新奇, 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遍的抒情詩, 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5]“五四”運動雖具偏激性,但在客觀創作上卻并未與傳統徹底斷裂,實際上搭建起溝通現代與傳統的橋梁。
一、魏晉玄言詩的影響
魏晉時期玄言詩興盛,成為逃避紛亂現實,躲避塵世煩擾,抒發心靈獨語的寄托,在對外界的體味下,冰心與魏晉詩人同樣有著對“時代”的親身體驗和沉痛思考,深知籠罩在時代的黑暗風暴下,個人猶如微渺的蜉蝣,難以用血肉之軀抵擋社會的發展潮流,因此開始尋覓哲學視角,在超越生與死的阻隔中探討永恒不變的真理。冰心繼承了中國傳統詩歌對遼闊宇宙的衍生和歷史滄桑的變幻孜孜不倦地追問的傳統,同時其詩歌也具有獨特的哲理思考。她循著外化的思想感情軌跡尋覓人生真諦,懷著憂思與希冀、焦灼與等待,對埋藏在心中的關于生與死、瞬間與永恒的哲理命題,進行深刻的探求和追尋。如:“倘若世間沒有風和雨/這枝上繁花,/又歸何處?/只惹得人心生煩厭。” (《繁星·129》)傳統詩人往往感慨落花無情,流水無意,柔弱的花兒被風雨無情摧殘,而冰心卻揭示出生命不只在于光榮的生,還在于絢爛的死,生與死是自然發展的常態,如果花無凋落之殤,只會惹人生厭。生命的生生不息通過“花兒”榮謝展現不僅意趣生動,而且還啟迪智性思考,是機智與生趣的巧妙結合。東晉山水詩人謝靈運也長嘆:“短生旅長世。恒覺白日欹。覽鏡睨頹容。華顏豈久期。茍無回戈術。坐觀落崦嵫。”(《豫章行》)詩人窺鏡凝視一去不復返的華顏,思索著宇宙萬事萬物的哲理,喟嘆著生命時空二維的有限性,嘆息著萬物的渺小與可悲。
玄言詩講究“以玄為尚,以淡為美”[6],劉師培稱“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 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鐘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缺理趣耳,夫豈尚理之過哉。”就是評價陶、謝不像孫、許等人運理過度而失去詩趣,而又包涵著精致玄妙的哲理。自然是陶、謝二人展現玄學的最佳方式,謝靈運酷愛山水仙境,陶淵明追尋世外桃源,借自然以玄思哲理,其中滲透的審美趣味在冰心的小詩中可找到依據,在空靈醇雅的短句中彰顯著自然的勃勃生機,卻又隱含著含蓄雋永的“理”,如“高峻的山巔/深闊的海上——/是冰冷的心/是熱烈的淚可憐微小的人呵!”詩人在悲傷之中感慨人在山、海面前的渺小,嘲弄人類的無知,與苦口良心陳詞概述的胡適不同,她并不是抽象的思緒,而是自然的鳥語花香賜予的靈感;與懷抱宇宙精鶩八極的宗白華不同,冰心是內省的頓悟,將思想的火花充分沉淀成精煉的語言。玄言詩要求物我合一的深層境界,在山水一色中暢懷抒志。冰心在寫景摹物時,“我”也成為了客體,在婉轉輕柔地筆墨描繪中,探索人生的真理,意象的建構為哲理的探索帶來一種霧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模糊感,卻別有一番風趣。
魏晉很多詩人講究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超脫于現世而回歸于自然,冰心也在喧囂的亂世中為自己筑起了心靈的烏托邦,透露出玄思的趣味,她認為“影兒落在水里/句兒落在心里/都一般無痕跡”(《繁星 九十六》)俗世煩擾煙消云散,宇宙萬物融為一體,所有的爭執、喧囂褪去了丑陋的表皮,綻放出新的生命,與陶淵明“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精神契合。他們都想要剝離開俗世的紛爭,了卻利益的牽絆,但也絕不消極避世,他們都擁有心靈的凈土,可以洗滌雜念的污染,撫平蕩起的漣漪。這種超然于物外的詩情,為詩人紛亂思緒的展現增添了些許思索的趣味。
二、宋代理趣詩的影響
宋代理學繁盛,不僅包含普遍存在的宇宙哲理,還有鉗制思想的倫理道德,詩人崇尚“理性”,哲理之言廣泛見于創作中,主體在體察社會現象和自然物象時,往往在體味心中流淌著的哲思之激流,在意志地掌控下詩人又逐漸擺脫思緒的控制,幻化成活潑生趣的形象性表述,洋溢著智性的光芒。程頤說:“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途人,一也。”因此推崇“格物致知”、“筋骨思理”,在詩歌創作中浸潤著對物象智性地觀察,這便是宋詩影響冰心的獨特詩趣。
宋代理學從禪宗的二維對立的思辨中汲取營養,從心出發體察社會的發展,認為統攝宇宙萬物的是永恒不變的真理,不同的事物都有不同的發展規律,雖理有千姿百態,但最終歸于一處。因此宋朝詩人在從宇宙萬物中擷取寫作依托時,一般會思索其內在的蘊理,其主題一般分為三類:暗含自然法則的理趣;玄思生命內涵的理趣;靜思禪宗辯證思想的理趣。冰心的理趣小詩便與此不謀而合,“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繁星五十五》)與王安石“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客易卻艱辛”意旨一致,揭示了人生浴火重生前的辛酸:旁人不在意你涅槃前的艱辛,只在乎你成功后的驚艷。小詩凝結了詩人對宇宙哲理的嚴肅思考,理在思索中達到升華,它引導人們沉淀不斷浮躁的心靈,在塵世的煩擾中淡泊明志。理與趣融為一體,使得包涵禪思的詩歌,富有回味無窮的趣味。
宋代理趣詩中托物比興成為了主要的表現手法,宋人李仲蒙解說為“: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7]在自然物象的感發中某種哲思瞬間凝聚,情感的波動起伏,詩思的恣意流淌,在興來神往中幻化成賦有理趣的詩作。梅堯臣:“木杪芙蓉花,開非紅艷早。常畏晚霜寒,朱華競衰草”(《拒霜》),還有冰心的“露珠/寧可在深夜中/和寒花作伴——/卻不容那燦爛的朝陽/給她絲毫暖意”(《繁星一二一》)都是站在哲理的高度上托物興懷,“芙蓉花”、“露珠”生命的短暫,讓詩人們體察到時光的流轉,人生飛逝,韶華白首,然而生命可以是絢爛的,又在隱約間透著一絲憂心,迷茫。冰心借物象的自然天性寄托興懷,抓住體征聯系賦予了小詩頓悟妙趣的魅力。
嚴羽《滄浪詩話》評價宋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 歐陽修也稱:“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理性的枯燥并沒有禁錮詩人詩思的揮灑,反而在對“理”的思考中“返璞歸真”。冰心繼承了宋人的思考,運用了一般人未曾領悟的感官,巧妙地結合理與趣,將司空見慣的現象表現出言有盡而意無窮。
三、明代李贄“童心說”的影響
溫馨和睦的家庭、中西結合的教育、清新自然的滋養、培養了冰心的童貞之心,“童心”是最純粹的,沒有雜質的侵蝕,它像上帝一樣凈化每一個沾染凡塵的俗人。兒童的心靈世界是澄澈透亮的,用稚嫩的眼睛探索著陌生的世界,用鮮嫩的小手撫摸著廣袤的大地,冰心大力頌贊:“萬千的天使/要起來歌頌小孩子/小孩子!/他細小的身軀里/含著偉大的靈魂”(《繁星 三十五》)。冰心以“童心”寓理著詩,其實是深受李贄的“童心說”的影響,李贄認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8]童心是人回到本真,卸下世俗的羈絆,從最原始的自我觀察世界,理解世界,也許能還原人最初的情感,擺脫奴性,邁向人性。李贄希望擺脫儒家對文本創作的鉗制,解開道學和封建道統對個性釋放的束縛,破除僵化的程朱理學對精神發展的殘害,他扮演著打破舊觀念,啟蒙新觀念的角色,希望實現最純粹的自我的文學,這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呼喊。冰心同樣也是以啟蒙家的姿態用凝聚真理的小詩,震醒依舊活在封建禮教的精神奴役下沉睡的中國人。并且“童心”是一種心靈狀態,是體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在物我一體、物我同質的心物契合中把握客體世界跳動的韻律,詩人以兒童的視角抒發哲思的感慨,讓乏味的理蒙上童真之趣,如“嬰兒!/誰像他天真的頌贊/當他呢哺的/對著天末的晚霞/無力的筆兒/真當拋棄了”(《春水 一八零》),展現了對晚霞的渴望,是對打破黑暗之光的向往。“我們是生在海舟上的嬰兒/不知道/先從何處來/要向何處去”,用嬰兒發聲提出人們的迷茫,在動亂的現世不知該何去何從。以兒童的視角賦予詩人窺探世界的新視野,反而起到了振聾發聵的效果,讓凝重的哲思富含意趣。
國家的積貧積弱、社會的動蕩不安、現實的爾虞我詐,讓冰心理解了世界矛盾性的二元對立,于是以童心提出反抗。她的小詩因為歌詠真善美且富有恬靜、純凈、真實的心靈而成為了新詩中的一抹曙光,為小詩的含蓄雋永、理趣橫生奠定了基礎。
郁達夫曾評價冰心“意在言外, 文必己出, 哀而不傷, 動中法度, 是女士的生平, 亦是女士文章之極致。”[9]可見冰心文章的特色在于將哲思、情思埋藏在字里行間,而有法有度,哀而不傷。這是因為冰心不僅繼承了傳統詩歌理趣的抒懷,還超越了傳統詩歌的形式,用自由的形式擷取“剎那間的內心生活的變遷”,點化成蘊藉豐富的作品。
《莊子·秋水》說:“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冰心便是將理與情結合抒寫小詩,細細品味會體悟到冰心小詩的晶瑩透徹、清新雅致、率真坦誠、雋永深刻。詩人凝聽生活,玄思人生,詩情因一剎那的哲思燃燒,從紛亂的情思中摘取精華,凝結成“零碎的思想”,是情理交融、趣味橫生的藝術珍品。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周作人:《論小詩》《周作人早期散文選》(許志英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74 頁。
2. 顧之京:《宋詩理趣漫論》,《河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
3. 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8頁。
4. 馮文炳:《談新詩·冰心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頁。
5. 周作人:《論小詩》, 《周作人早期散文選》(許志英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年第1版,第274 頁。
6. 陳順智:《東晉玄言詩派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
7. 杜月仙:《梅堯臣說理詩研究》,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8. 田興國:《李贄“童心說”新解》,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9.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