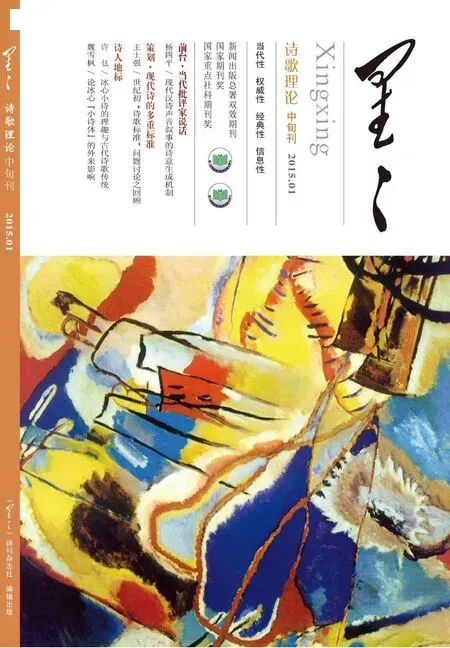尋找的意義:尋找一條路
——轉角散文詩集《荊棘鳥》閱讀印象
薛 梅
[文本導讀1]
尋找的意義:尋找一條路
——轉角散文詩集《荊棘鳥》閱讀印象
薛 梅
近年來,正當中國現代詩越來越被邊緣化的現實中,散文詩這種詩體卻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親睞,這看似一種偶然的接受現象,其實擁有也有其一切必然性的原因。現代詩被讀者們冷落,雖然原因不可能是單一的,但近年來的大量新詩作品的詩性缺失,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國社科院劉福春研究員指出:“在新詩無邊界的審美拓展的創作的亂象中,只有散文詩還堅守的詩性的體質。”。散文詩仍然獲得讀者的審美支持,一定與散文詩的“詩性堅守”的審美追求有關。而體現這種堅守的是近年來崛起于詩壇,并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的“我們”散文詩群中涌現出一批優秀的作者以及他們的優秀作品的接連問世。在這批優秀作者中,轉角是極其受到矚目的一位新秀,她的作品,代表著“我們”的一種藝術傾向。
初識“轉角”的名字當然是筆名,首先覺得這個筆名取得很好。近年有一句頗時髦的話,轉角遇到愛。影視及歌曲都很紅火,大抵突出兩個核心,一個是奔向你,一個是下一個路口。這樣的“轉角”意味是奇妙的,說明她有方向感,不是被動的等待,而是積極地尋找心所向之處,也并不是一馬平川,而是若一條長河,曲里轉彎,但卻絕不斷流。
尋找是一生的事,也許心靈最終也還是漂泊,最終也還是徒勞,也還是若莊子所云的“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但現代文人自魯迅清醒并痛苦地發現了“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的真相之后,尋找一條路,反而成為一種可能,成為一種必然。朦朧詩人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確認了一條真理之路。轉角以她的散文詩點亮了四野的螢火,讓靈魂提著螢火蟲找家,也意在確認出一條內在的永恒之途。
轉角說:“2011年,我邂逅了散文詩,并為此開始了我波瀾壯闊的尋找與跋涉。三年來,靈魂與生命在我的筆下交相熔接,我傾盡荒蕪,詩意地流浪在這塊遠方的芳草地,我已分不清是散文詩接納了我,還是我不自覺地踏上了皈依散文詩的路途。……之于寫作,我感知了他們的美如同我在自我超越的旅程上割舍出另一個我,并讓這個‘我’從起點最終回到了源初的位置,午夜過后,黎明醒來,我攥著我的靈魂與生命身臨其境。”(《荊棘鳥·后記》)
這就是轉角的尋找,尋找一條路,并能夠走下去。
一
尋找一條通向潛隱體內的豹的路徑。當代散文詩的美不僅在于承繼了初創時期的獨語方式,更創造性地進入到了半開半合的對話意味中去。一如美國大片《星際穿越》中展開的時間的蟲洞,當出生這個點和成年后的點對折起來,洞穿兩點后,距離就奇妙地縮短了,我們和轉角一樣就可能重新洞見我們自己的誕生(我多年前也曾寫下過這樣的詩題《我參與了我的誕生》),從而具備了一種開蒙場景與成熟敘述者的對話效應。然而轉角似乎感覺更為敏銳,更為奇妙,當各種文本中“時間”已成為一種泛化意象,轉角便不屑再用。她將之靈化為“太陽”,與之追慕則是一種常態,與之為敵則是一種變通。她像極了余光中筆下的夸父,她回身揮杖奔回東方,“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她撞上了她的誕生,她放射著自信的光芒,她向世界大聲地宣告:太陽,我要終生與你為敵!
這是令人膽寒的宣言,也是令人傾倒的告白。她尋找的目的不是棄絕,而恰恰是為了真正擁有。“從渾濁到渾濁。從冰冷到愈加冰冷。/從一座深山到遠方的陸地,我們,緩慢駝行。/而誰最終成為火的種子。/虛指向太陽——”(《第三輯:幽冥的花朵·黑夜里的一次誦唱》),“太陽,清醒于海天一色的遠方。”(第四輯:夜雨·搏殺)這是轉角尋找并選擇的路徑。她在返還中有了新的身份和認同,她成為一只傳奇的荊棘鳥。她在撞見自我的誕生中誕生了荊棘鳥的寓言。眾所周知,荊棘鳥“屬于自然界最執著的生命象征”(靈焚《超越死亡,抵達澄明》)。它一生只唱一次歌,它的歌聲比世上所有一切生靈的歌聲都更加優美動聽。從離開巢穴那一刻起,它就在尋找著荊棘樹,直到如愿以償,它才歇息下來。然后,它把自己的身體扎進最長、最尖的荊棘上,在那荒蠻的枝條之間放開歌喉,曲終而命竭。世界也為之側耳肅立,因為最美的往往是由最痛的換取。
荊棘鳥的執著成全了轉角的執著,她的散文詩長旅便在開卷長詩《荊棘鳥》中壯行。全詩由36章構成,隱喻著某種時間向性或生命年輪的所指。轉角便在成長與誕生這半開半合的時間維度中,使對話進入到一種寓言性的世界中去。這只“來自天堂的夜鳥”,以“熱愛”銜著誕生之火照亮暗夜:
“融入浩大的歷史煙塵和波瀾壯闊。我用完整的黑解讀黎明前更深層次的囚期。我用一把四角利刃割破,以骨血滋養豹子的太陽,迎接新一輪日出。我十月的太陽。
用盡一切光輝!”
——《第一輯:烈焰·荊棘鳥》
這樣回返之后的誕生見證,已經不再單純是靈魂的獨語,而是呈現出了與這個世界,與生命歷程的對抗與對話。割破以骨血養育豹子的“太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涅槃——“豹子”意象,這“新一輪的日出。我十月的太陽”。 自此,豹子成為荊棘鳥的魂魄,一路踏上尋找“幽冥的荊棘叢”的塵世征程。幽冥即是宿命,即是命定的皈依。而“豹子”意象則成為更有意味的象征,那有著幽秘的不確定的氣息的豹,那充滿著滋潤的水分和閃電的威力的豹,那有著滑行中最大穩定和速度的豹,正是強意志力的生命的象征。如果說轉角的“荊棘鳥”意象只構成艱辛和悲壯,那么以豹為魂則凸顯了生命的神力和偉大的意志,這兩個意象的誕生才真正使轉角的“荊棘叢”有了生存陡峭的獻祭,使對話有了生命哲學思辨的閃電。于是,場景的轉換碎片一樣,高山、河流、大地、城池、黃昏、夜的荒涼、月下、燈前、草木蟲魚、冰霜雨雪、四季流徙,成為快速旋轉的碎紙機,將浩大的地理和綿邈的時空盡數切碎,艱辛、苦痛、背叛和死別深陷其中,轉角、荊棘鳥、豹子三位一體,互生互證,鑲嵌著精神的迷宮,這就意味著,作為意志的主體,終能識別命定的歸屬:
“喧嘩的聲浪氣勢磅礴。我掏空了韜光養晦的暗,袒露最原始的真身。我張開不曾委曲求全的喙,縱情歌唱。我放出最昂貴的碧血,目送自身和豹子一程。
我的豹子啊,領走我一顆不斷懺悔的初始心!
我和你最終完成一致的絕美,進入嶄新的世界,嶄新的空無。”
——《第一輯:烈焰·荊棘鳥》
轉角在荊棘鳥的泣血歌吟中完成了宇宙裂變的新世,生命澄澈的回歸和山水同盟的本相,豹子隱退,以其潔身自好還原了自我。“靈魂的施暴者終被黑暗碾為粉塵。天地澄澈,在永生中誕生新的黎明”,顯然,這寓言中有荊棘鳥或者轉角的自我靈魂的撕裂與張揚,超越死亡中,亦有對世界對萬物的坦誠與和解,轉角之上有更大的觀照者,精神之豹中有神秘的啟悟者,這潛隱的對話,以有詞和無詞的言語,構成了象外象、意外意的雙重旨歸,最終走向情境,走向詩性,走向境界。
“太陽”意象至此完成了它的使命,無論是真理還是謬誤,無論是光明還是強權,都將以涅槃重生而化為澄明。這是通透的理性,不懼死,必得生。
二
尋找一條通向澄明空茫的重生之路。轉角是一名70后女詩人,但她的文字中幾乎少見70后一代的娛樂性、消費性、表演性、商業性和肉欲性,轉角是深邃的、嚴肅的,對自我的命名有著高貴而純正的知識分子氣質。她飛沙走石般得去咀嚼沉重的生命史碎片,她是不安靜的、不妥協的,她是靈魂的探險者,她是沉實的,是重的,是緊張的。她的尋找和選擇的路徑絕不是輕松的美學,她沒有調侃、游戲、情調、好奇和對發跡向往的時尚流弊,她只是沉醉在自我靈魂的漩渦中,像一位久經沙場的將領,指揮著千軍萬馬有序的沖突出來,并獲得重生的澄澈和清明。
誠如轉角在《西藏書》所獲得重生意味:“路,是回旋的,是向著遠方的,對此我深信不疑。在西藏,我所見到的不是在風景,而是靈魂的發現,是對自我的識別,是命運和因果輪回的反復疊加,是期許擁有美好未來的永恒愿景,這條寬闊的大路是朝向太陽屏蔽黑暗的路啊!”
“朝向太陽屏蔽黑暗的路啊”,太陽的重生,意味著轉角的重生,尋找的重生,生命的重生。然而,轉角的重生姿態帶著禪心,帶著禪性,《荊棘鳥》中的每一篇幾乎都在結尾呈現出空茫的意緒。這是她對世界的姿態,清楚每一條其實都沒有終結,人生終要以自身的簡質和澄明走向別一維度的居處。“澄明”才是尋找一條路的本相,是萬物與自我必須面對的澄明的空茫,是萬物與自我泰然處之的澄明的空茫:
“一聲又一聲呼喚,被神孕育的喘息,在水上澄澈,使水澄澈。
路途,終被青草占領。開花的籽粒,立在風的礦脈上,打掃萬物。
天與地在第三日,藏起忠貞和大雨……”
——《第二輯:大地之殤·第三日》
“站在時間之外,天地懸浮!
恍若大雨傾盆,塵世皆是隨身抖落的一粒灰,即是整飭之后,也根本無法安身立命。徘徊,猶豫,輾轉反側……
被認領的過程早已蛻變,生死上升為火的高度。
盜火者需要安寧!”
——《第二輯:大地之殤·火的盛況》
“十五萬片!他經受火炙、榮辱、屈尊、降位,以廣闊的胸襟終究抵達了生命的近處。
他失聰之后,獨自瀝出虛無,用空曠接受昨日之絢爛,今日之芒刺,明日之浮沉。
他棲息在大地上,言簡意賅地活著,從容,淡定,寂寞,孤獨……”
——《第二輯:大地之殤·甲骨,甲骨……》
“孤獨的落日見證生命這悲辛的雨水怎樣脫離海與天的束縛,萬物生生不息,萬物突出體內荒涼的月夜。
一盞失足落水的燈正在照亮我們前行的遠方……”
——《第四輯:夜雨·失足落水的燈》
“而我飽和的痛苦披衣而起,從出生日走向出生日。
日落的時刻!
我偶然締結的虛空途徑一扇門,一只死亡的手正撫摸我。時間和蒼老被阻隔在門外。
火焰,守住波光粼粼。
逝者,終于見到了一處海岸——”
——《第四輯:夜雨·搏斗》
轉角幾乎每一首都在全心袒露著自己的靈肉之思,那些普通、卑微,和荒蕪,那些火光、夢境和花朵,那些眺望、傾聽,和匍匐,那些盲區、退隱,和深淵,那些地獄、落水,和搏殺,每一次靈魂的掙扎,都是一次靈魂的洗禮;每一次靈魂的安詳,都是一次靈魂的涅槃。轉角始終不是在寫紅塵滾滾,但每一處掙扎的痛和累,都寫滿了滾滾紅塵帶來的傷害及警醒;轉角始終不是在寫人生游戲,但每一處安詳的慈與愛,都寫滿了游戲人生帶來的選擇及摒棄。
轉角本身就是幽冥,是宿命,是不甘的魂魄,是清白的風。
我們恍如見到了李叔同淡然的背影,看到了賈寶玉初陽的溫度,他們的智慧在轉角的路口,在智慧的心的路徑,在走著,并有蝴蝶重生的翩然……
這是澄明的智慧,承受沉重的,即獲得輕盈。
三
尋找一條通向文字能量的語言之路。散文詩究其根本首先是詩的,然后才是其它。詩人韓東從瓦雷里那里獲得了啟示:“詩到語言為止”。語言構成了詩性的材質,語言的趣味決定了一首詩的風格乃至風骨。散文詩也一樣,必須無條件地信任語言,就像蜜蜂信任它的毒針,牛信任它的犄角,愛信任她的吃醋一樣。轉角深諳其道,她信任她的語言的醋意十足,她介入語言的味道不是麻辣的,不是齁咸的,不是淡如白水的,她是發酵的,有意味的,有婉曲的,有淚水在里面溫潤而酸澀的,有疼痛在里面攪動而絕望的,有混沌在里面變通而清醒的,有堅執在里面吶喊而不悔的,有理想在里面活著而不棄的,轉角的語言昂首走在散文詩的路上,幽僻小徑也吧,通衢大道也可,它那么義無反顧地走著,暗夜來了接住,黎明來了重生,她的語言構成了大境,構成了屏障,構成了堅不可摧的防線,和帶著硬度的質感:“他疼痛,隱忍,糾結,卻只能高昂著頭顱向內咆哮,哭泣”,“他經受火災、榮辱、屈尊、降位,以廣闊的胸襟終究抵達了生命的近處”,“他棲息在大地上,言簡意賅地活著,從容,淡定,寂寞,孤獨……”(《甲骨,甲骨……》)。這樣的描述是對轉角語言最好的詮釋,她最幸運地是,她走向了語言的內里,并被融化。
轉角散文詩的寓言性、象征性,當然也得益于她這種創造并運用語言的特質。她很少選擇那些小的、弱不禁風的、香水氣的,或者中性的詞匯,她總是喜歡在語言中掌控那些有能量的,有爆破力的,有歷史深度的,有縱深感的,有活躍的細胞組織的,甚至是男性的硬度和寬闊的肩膀的,她試圖用這樣的零件建造一座文本的時光機,在散文詩的星際之路上穿越,并尋找適合人類情感安居的所在。這是她的美夢,也是她的現實。她的理想宏大,氣魄超人,但她還需要重視一個女性性靈深處更樸素、更細微、更動人的細膩和以柔克剛的情愫,否則,人性繁復,在駕馭的過程中,時光機會容易意外而變形和失控。這是轉角急需的改變。
語言喜歡藏匿,只有真誠的心可以找到它。語言像珍珠一樣散落在黑暗的想象之中,只有真誠的情感能把那些閃光的東西串起來,那是一條既看得見,又看不見的“藕斷絲連”。我們有理由相信,轉角的散文詩語言的架構只是轉角的,這是她的路徑,她會一直走下去,在沒有出口的出口,因為情的真、愛的美、思的誠、訴的切,下一個路口,下下一個路口,都屬于她。
從“烈焰”到“夜雨”,從荊棘鳥的死亡穿越到“青龍”的激蕩搏殺,轉角“企圖完成從出生日到出生日的一次輪回或回歸,她欣然在暗夜中撫平“不安之書”,她快意于《在黎明里出場》: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幾乎所有的歷史都源于河流,而我與河流的相遇則在詩歌的現場里。在水之湄,在山之巔,在我魂牽夢繞的故鄉,我幻化成一只盤旋在河流上方的藍蝴蝶,只為去生命的源處尋找自己”。
轉角決絕得表現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坦然和坦蕩,從來處來,到去處去,在“碎金子似的河流”里,成為“彼此的路人”,在“隱秘的城堡”里,足以給出幸福的慰藉:
“而你,是我啜飲的壺,殘忍而溫馨到讓我甜蜜地死去。”(《日光與憧憬》)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尋找,尋找一條走下去的路。轉角的文本意味在于,走自己的那條路,百折不撓地走下去,即便空茫也要澄明的走下去。我在轉角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前面走得太急了,我要悄悄地告訴她:慢下來走,要能夠傾聽到自己的心跳……
“慢下來,請再慢一點,我將更有資格黑得發亮,綠得發青,并空出整座城池供養一座江山——
神州大地!”
——《第四輯:夜雨·日光與憧憬》
(作者單位:河北民族師范學院)
1. 轉角《荊棘鳥》代序:“是腳印,就應該留在時光里(代序)”,燕山出版社,2014年9月,P.1.
2. “我們”全稱“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群”,創立于2019年3月14日。該詩群秉承“大詩歌”創作理念,提倡“意義化寫作”,在沉寂的當下詩壇卷起了一陣詩歌審美藝術的新風,正在努力改寫中國現代詩近百年的分行詩一枝獨秀的審美版圖,企圖建構分行詩與散文詩并駕齊驅的嶄新紀元。這個群體的領軍人物是周慶榮、靈焚,而轉角則是“我們”的主力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