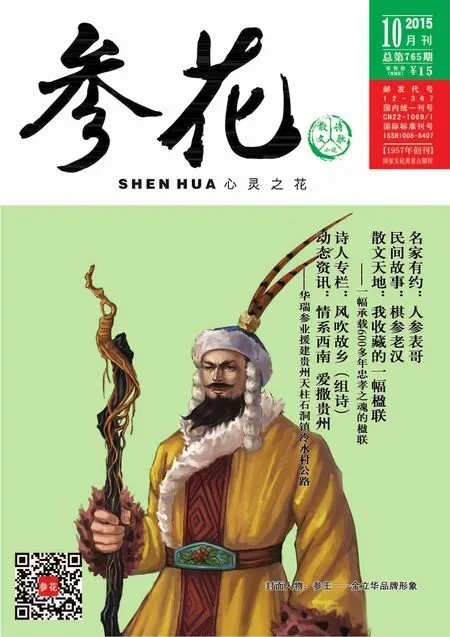誰言寸草心
——母親,我們家的那些人和事
◎柯友如
誰言寸草心
——母親,我們家的那些人和事
◎柯友如
(1)
母親,十七歲那年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七歲剛從舊社會過來的農(nóng)民。十幾年間,一順溜生下了五個男孩,接著又添了兩枝花。老人說,“五男二女”是要硬“八字”載的。也許是母親“八字”差了那么一點,因而,我手下的小弟“老五”出世不多日就夭折了。
母親三十一歲那年,因父親當(dāng)上了村支書,要帶頭響應(yīng)計劃生育號召,不然不知后面還有多大一串。三十一歲啊!如今有多少這個年齡的姑娘正在閨中待嫁呢!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讓這個妙齡秀女依附這塊土地,一晃就是六十多個春秋,始終心甘情愿地圍著六個兒女轉(zhuǎn)了一輩子。大概是天意吧!
從兒時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母親像往常一樣急匆匆放工回家,沒歇口氣就上灶臺做飯。
這是一個打了補丁的土灶臺,破壁殘?zhí)牛抑腥丙}少油、缺米少菜,滿屋多的是高矮不齊、懵懂無知的孩子,有的爬上灶臺等飯吃,有的依偎在墻邊不做聲,有的在打鬧,有的在啼哭,有的……見狀,焦急、心痛。不巧,外公碰上了“槍口”,磨破了的母親就把外公當(dāng)出氣筒:“爺呀(母親管外公叫爺,方言),你害死我了呀,把我弄到這個鬼地方來遭罪,老天爺也不長眼,把這多‘冤孽’送到我身邊,討債啊!”“爺”一聲不吭。他露出無奈而又慈愛的笑臉。半晌,迸出幾個字:“秀兒,莫焦急,熬過去就好了。”
凡事有原委。解放前夕,外婆在建筑隊提灰桶,外公拖板車,同在一個城市——武漢。唯一不到十二歲的女兒也在武漢一紗廠當(dāng)童工。假如,要驗他們的身份,外公和外婆屬農(nóng)民工,舊中國的農(nóng)民工。母親呢?打工妹,小小打工妹。按理說,一家人有點事做,有口飯吃,也算有一份安靜。可是,快解放了,“爺”聽說要炸紗廠,怕這根獨苗斷了(因為母親幾個兄弟沒拾起來),便擅自偷偷地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把在工廠注了冊的“在冊職工”母親引回了老家——張前灣。外婆知道后氣急,從此與外公分道揚鑣,再也沒有復(fù)合。
母親從一個準(zhǔn)市民,陡然變?yōu)橐粋€地道農(nóng)村婦人,雖不叫“落魄”,但總覺得一時難以適應(yīng)。干農(nóng)活顯然吃不消。尤其是她最怕螞蝗,從不敢下田插秧,地道的“旱鴨子”。后來,經(jīng)生產(chǎn)隊長安排,她成了禾場的一名“固定工”。禾場上一群清一色的婦女,只有一個男的,叫保管員。他負(fù)責(zé)派工、記時、看護什么的,是她們的頭兒。禾場的活主要是收收撿撿、翻翻曬曬,比如棉花、玉米、稻谷、芝麻等物。好在不下水田,但活兒也不輕松。盛夏,憑那草垛、谷堆與烈日產(chǎn)生的高溫就有四五十度。熱浪襲來,像蒸包子似的汗水直淌。那年頭哪有像今天這樣五花八門的飲料呀!解渴的是大桶盛的野山楂加一花兒鹽燒的茶。稍賦閑點,幾個婦女偷偷地找個草垛與驕陽斜切的陰涼處庇一下蔭,有時屁股還沒坐穩(wěn),就被保管員吆喝到太陽底下:“田里干活的人不是人嗎?有蔭嗎?”
這群婦女也不是吃素的,趁機,她們嘻天哈地地將這個“老單身”保管員放倒,使勁地將麥須往他身上塞,讓他害癢難受,她們竊笑。雖苦雖累,但她們也會找樂子,經(jīng)常說一些不堪入耳的葷話,母親一般不茍言笑。有些活是技術(shù)活,比如:篩篩子、扇風(fēng)扇、捆草頭等等。你沒有一年半載的學(xué)習(xí)和磨礪是注定不會做的。你不會做,背后是注定會有人貶損的。那年頭,工分就像今天的高考分?jǐn)?shù)一樣的金貴,七個工分日是不好混的呀!
(2)
盡管母親日夜操碎了心,但她臉上露出的表情一向安詳。偶爾對外公發(fā)點怨言,外公也從不“對抗”,安之若素。“有人才有世界,熬過去就好了”。他不停地幫母親做家務(wù)事,比如絞把子、打要子、添柴火、生爐子。日久,爺倆成了相依為命的良師益友。母親愛聽外公邊干活邊講故事。
外公很少講鬼與怪的故事,按現(xiàn)在時髦的說法,都是正能量的。下雨天,外公也在做針線活的母親旁邊細(xì)細(xì)地講,慢慢地述。水滸呀,宋江呀!三國呀,劉關(guān)張呀!辯賢良、識奸佞,有褒有貶、引人入勝。有時還講本地名人張裕釗(曾國藩門下四弟子之一,排行老二)如何回鄉(xiāng)乘船沒給錢,現(xiàn)場寫字讓船翁去當(dāng)鋪的故事。還講仁人志士盛浩如如何開展革命斗爭的故事。講的,聽的,旁聽的,時而流淚,時而歡笑。
外公也常細(xì)說自己的身世。父母早故,在舅舅家寄養(yǎng)。舅舅視其如子,送他念書。他說學(xué)堂里有個“神童”,背書不是一節(jié)一節(jié)地背,而是以老師用針在書上使勁一刺的針眼為準(zhǔn),只要是有針眼的頁碼,他在第二天全都能順背如流。也許是天妒英才,這人命短,不久就死了。外公數(shù)“次神童”,也算得上聰穎過人。難怪后來電臺播放社論,他一口氣可以復(fù)述出來。要是繼續(xù)念下去,說不定外公也會成個什么“家”之類的。可問題是,外公只念了一年半就輟學(xué),因為舅舅家有人頗有微詞,說讓外姓人讀書不合適。外公聽后氣憤地甩掉書包,步入了社會。
他是個硬氣的人。有一回,在一個中學(xué)當(dāng)伙夫時,校長要他一斤米煮出八斤飯,他咋舌地說煮不出來。校長又說煮熟了再蒸一次,“雙蒸”就出來了,外公還是說蒸不出來。那校長氣急了,逼著外公寫檢討認(rèn)錯。外公也惱極,偶露了一回崢嶸,“拿筆來,我念你寫:
校長叫我作檢討,
雙蒸八斤蒸不了。
游龍淺水遭蝦戲,
黃鶯啄了大鵬鳥。”
寫完,外公拂袖而去,校長半晌愣著。
我家就這么點文化底蘊和沉淀。祖輩、父輩均為文盲,只有外公是個“科班”。哦,還有我父親后來通過夜校和培訓(xùn),認(rèn)識了一些字。母親,受了外公的熏染,崇尚文化,再苦再窮,也要讓孩子讀書,女孩也不例外。我尋思著:母親傻呀,為何不像別人一樣,早早地讓孩子幫自己干活?母親經(jīng)常引用外公常說的話告誡我們: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外公是我家的“智庫”。我們許多為人處事、安身立命的精神動力就來源于此。
(3)
我四五歲時,外公經(jīng)常肩負(fù)我看戲或玩耍,很當(dāng)真地教我哼一首歌謠:亢頭亢頭,有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亢頭。我津津樂道,他喜極而笑。后來,我才知他是戲弄我的,因為我是亢頭。我上當(dāng)了,被“老狐貍”帶上鉤了。何止上當(dāng)一次?每逢過年,母親時而請裁縫到家里來做新衣服。這下可好,他興致大發(fā)地唱念著:“新老大,舊老二,補老三,破老四。”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忽視,哭了。找外公評理:為什么輪到老四說是破的?他又捂著嘴巴笑。
他對我是寵、謔、教于一體。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大約七八歲,外公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一張紅紙攤在桌上,折成豎格,放好硯池,將一支毛筆遞到我手上,教我寫字:“新正發(fā)筆,筆中有花,花中結(jié)果,果然如意。”他又給我買了一本柳體字帖。臨呀,摩呀,那個間架,那個骨,我的毛筆字就從那時發(fā)端、啟蒙。
外公是個和藹可親的善老頭,也是一個玩世不恭的倔老頭。他疼我們一家人,勝過他生命,掏心掏肺,無怨無悔。他從不呼我們的名字,總是昵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他在“博愛”的同時,還有點偏愛。最鐘愛的是我和大哥。我排行老四,他時常調(diào)侃我為“四先生”。因我小時候瘦,他也喊我“四猴子”。他從不打我們、罵我們,一貫的和顏悅色。我們做錯了什么事,他從不大聲呵斥,從他的眼光里,我們似乎看出,不是縱容,而是耐心的期待。在生產(chǎn)隊“看山”時,在梁子湖畔放養(yǎng)了幾只鴨子,他幾乎把所有的鴨蛋都拿到了我家。有時攢幾個叫我或大哥去開點“小灶”,那菜油煎的鴨蛋,一碗四個、五個,香噴噴,其味無與倫比,我們一呼嚕就幾乎連同舌頭一起吞到了肚子。他在旁邊望著我們咽,露出快慰的笑容。只要有一點有用的東西,他就要積攢起來,隔三差五地從十里開外向我家馱。比如小魚小蝦、菱角蓮蓬、紅苕、玉米、柴火、棉絮和親手為我們織的魚網(wǎng)、竹簍。三十年如一日,幾乎天天風(fēng)雨無阻地往我家跑。有時瞄我們一眼就茶飯未進地折返了。外公過去是一個高大健碩的男子漢,一晃,老了,背弓了,拄著拐棍,身軀像干柴一樣,瘦骨嶙峋,一點肉也沒有。能有肉嗎?一年到頭沒進一點葷腥。母親心痛:“爺老了,別再跑了,萬一在哪兒栽倒了怎么辦呀!干脆在我家歇著吧!”“爺”回答:“我來瞄一眼心里好過些!”
外公有時披星、有時戴月、有時驕陽、有時雨雪地把那條周而復(fù)始的路跑成了槽子。我家本無路,他走多了就成了路:一條施援之路,一條溫馨之路,一條邁向希望之路。
(4)
1978年,外公病臥我家,我快高考了。每天,我趕十幾里路程放學(xué)回家,給外公喂流食,比如苕粉糊、玉米糊和稀粥。我把臉貼在外公那褶皺、冰冷的臉上說話,外公總是笑著將我推開,生怕我聞了老人氣。我還給外公暖腳,捏著他那皮包骨的腳肚子,在被窩里暗自掉淚。我給外公清洗大小便糊了的褲子,從心眼里沒半點嫌棄。外公撒手那天,我們都不在,只有母親給他送了老:“爺呀,眼看日子快熬穿頭了,您怎么不熬了呢?”該享兩天清福,可是,沒有可是。
外公在我心中是高大的形象,我對外公有份特別的感情。每逢談及或者夢見外公,我無不潸然淚下,沾滿衣襟,所以,外公故去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我沒有缺一年去他老人家的墳前祭拜:鮮花、冥幣、糕點、蘋果,還有鞭炮和煙花。仿佛他教誨我們的聲音還在耳邊縈繞:橫草不揀、直草不撿呀;小洞不補,大洞叫苦呀;穿釘鞋、拄拐棍——穩(wěn)上加穩(wěn)呀;嘴穩(wěn)身穩(wěn)到處好安身呀……
(5)
我雖然很懷念外公,但真正承襲了外公品質(zhì)的人還是母親。“挨餓時期”吃“大食堂”時,母親到一二十里開外的地方挑一擔(dān)上百斤重的煤回來,只在食堂里換回半斤“芽谷”。胡嬸從山上挑一擔(dān)柴回來換了兩個糠粑,純糠的。母親伸頭問了一句,胡嬸護食,立即轉(zhuǎn)身以背相對。母親識趣地調(diào)了頭。那時候還沒有我,有一次,母親打回照得進人的稀粥(從東北運來的發(fā)了霉的粟米煮成的),喝到快要見碗底時,母親將剩下的不到半酒盅稍稠一點、有幾粒粟米蕩呀蕩的糊子,給不足一歲半的三哥喝了,五歲多的大哥在旁邊頓生不滿,兩行眼淚“叭嗒、叭嗒”地往下流,母親也心酸地紅潤了眼睛。孩子餓不得,太吃粗了受不了,故此母親經(jīng)常來個“一鍋兩制”。一天,外公正拿著鍋壁貼熟的榆樹葉做成的“粑”吃,將鍋中央燜的紅苕省給孩子們吃。大哥發(fā)現(xiàn)后,以為是好吃的“粑”沒給他吃,歇斯底里地哭著把外公罵個不停,還拾石頭砸外公叫他滾。母親見秀才遇了兵,有理說不清,含淚打了大哥,且攆著他圍灣子轉(zhuǎn)了幾圈,家里鬧騰得叫人簡直不能安身。第二天,大哥大病,肚子痛,求診無門,禱告無果。好多時,母親自責(zé)、悔恨、心碎,淚眼婆娑。也許是上天突發(fā)慈悲,大哥忽地病好了,母親喜極而泣。
在那饑腸轆轆的年代,觀音土、榆樹葉、野菜、粗糠也成充饑之物。
有一年春天,母親挺著大肚子,到田里去挑野黃花菜。跪著用小鏟挑了滿滿一籃子,正要回家時,撞了“鬼”,被鄰村一王姓男子悍然劫持。母親拼命地護著菜籃子,他就使勁地拖拽母親,把母親拖得直打翻滾。母親敵不過他,只好眼巴巴地瞪著他劫獲了自己用汗與血掙來的“果實”。算這小子命大,野菜沒了,胎卻保住了。
這小子是誰?就是我。不多久的一個黃昏,我呱呱墜地了。家里米、油全無,母親用怎么也捏不成疙瘩的米糠煮成糊子喝了一大碗。次日,全灣子搜個遍,只借了三個雞蛋。碗里用雞毛也沾不起來油珠子。
“大食堂”撤銷后,田地里慢慢長出一些莊稼,紅苕、玉米、蕎麥、豆類也算有了收成。真是“天不滅曹”啊!俗話說:“饑寒起盜心。”母親和隔壁的劉嬸,兩個人相約做“賊”。在我剛滿月不久的一個黑夜,伸手不見五指,她倆在對門壢正貓著身偷摘青蠶豆,往籃子里裝。忽見一個黑影荷著鋤頭攏過來了。母親嚇到了,用力一閃,滾到了幾米深的坑下,眼冒金花,脊骨梁炸得響,也不敢吱聲,直到看清來人是“看水”的五叔,才敢哼出聲來。五叔見是我母親,默念著:“快摘點回家吧!”你說,我對我那個五爺——母親的五叔,是怨?還是贊?
(6)
“杵秤桿子”, 也是我家的一件很難受、很尷尬的事。由于我家人口多,拿工分的人又少,所以時常碰到它。
“杵秤桿子”就是生產(chǎn)隊分余糧時,隊排到你家的時候,握秤桿子的人說:你家沒余糧。就“砰”地一聲將秤桿往地上一杵:“下一位。”
每逢秋冬,母親就要盤點“家底”,謀劃對策。他憂心忡忡地對父親發(fā)話:“他父,這么多嘴巴,都成飯糙子了,家里糧食遠(yuǎn)遠(yuǎn)不夠吃,孩子們餓了肚子,將來怎么成器呀!”隨即,父從母命,穿一雙母親做的新布鞋,挑著扁擔(dān)籮筐,帶著布票和棉布(我家人多,當(dāng)年分布票是優(yōu)勢,棉布是母親紡的棉線織出來的),揣點干糧,進山里。布票棉布換苕干。
父親翻山越嶺百十里,兩三天后換回一百五六十斤干苕絲、干苕片。每一程,父親累得必須癱睡兩日。母親煮粥時,撮一兩把苕絲、苕片,粥稠一些,好吞些也稍耐餓些,聊以添補,以度春荒。這成了我家多年的自救模式和機制。要不是母親別出心裁的得當(dāng)措施,我們家定會餓死人的。
無米之炊固然難,但母親有時也被“有米”之炊而難倒。家里一年到頭稀有見葷,偶爾煨點湯算是“大餐”。煨湯不易分湯亦難呀!有一年中秋節(jié),家里宰了兩只子鴨,母親蹲在地上幾小時,頭暈?zāi)垦5貙蝺袅嗣镍喿屿泻茫罅艘淮箦伱鏃l。上十人圍住灶臺等湯喝,有的目不轉(zhuǎn)睛地緊盯著“獵物”,有的喉嚨里早就伸出了爪子。這時注定母親最難辦,她遲遲不敢揭“蓋子”(揭開鍋蓋的意思)。她思忖:全家老小哪個不重要?這僧多粥少,分得不勻會鬧別扭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毅然揭開蓋子,先將鴨腿、鴨翅和胸脯肉歸個類,再從當(dāng)家人父親開始排個序,一氣呵成,三下五除二地將肉、面和湯分別盛到各人的碗里。剩下一點滑醒了的寡湯或鴨架子留給了自己。
全家人要過頓肉癮,那就得耐著性子等候。等母親千瓢糠萬瓢潲地把豬磨大,送到食品公司去“購半留半”(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政策,農(nóng)民自己喂的豬要交售國家),因吃不起正肉,只能提回一大籃子豬頭肉、豬油、豬骨頭、豬大腸小腸等大雜燴,全家人可以潑潑辣辣地美食一陣子。最讓我記憶猶新的事是母親“煉豬油”。炊煙裊裊,香溢四鄰。那個煉完油后的豬油枯子,撒點鹽干吃,既香又脆,爽口得不可言狀。有時,我趁母親不在意,伸手偷吃一兩顆,差點挨了爆栗子。
(7)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這一晃,我已年過半百。當(dāng)我們的生活過得美滋滋的時候,無時不刻不感恩一物——苕(紅薯)。如今,我在街上行走時,只要聞到飄香的炕苕味,必須駐足買一個,口中吃著,心中念著:滋補的苕!救命的苕!感恩的苕!
追憶青少年時代,我的家鄉(xiāng)有“四大奇葩”,值得深深的眷戀和感嘆。正如近代詩人何其芳所寫的那樣:“凡是有生活的地方,都有快樂和寶藏。”也許是上帝的有意賜予,在物資匱乏的時候,偏偏送給你個精神樂園,讓你怡然自得而去戰(zhàn)勝貧窮與饑餓,對生活產(chǎn)生美好的憧憬。一葩,“大雁南飛”。幾乎每年深秋,在暮靄西沉、帶月荷鋤時分,湛藍(lán)的天空上潔白的云朵直掛樹梢。天光云影,鴻雁排空。母親領(lǐng)著我們仰天呼喚:雁子,你排成個“一”字呀;雁子,你排成個“人”字呀!雁子很聽話,應(yīng)聲而列,排成了“一”字或“人”字,比現(xiàn)在的飛行表演還整齊好看。我常發(fā)愣、發(fā)傻,問母親:“它們怎么能聽懂我們的話呀?”二葩,“雨霽飛虹”。有時驟雨初歇,天空忽地騰躍出拱曲形、似橋狀、七彩繽紛、絢麗奪目的彩虹,讓人愜意,頓生精神。三葩是“青龍吊尾”。村野東方保安湖,忽見一個黑色的碩形“煙囪”,剎那間從天上垂直伸向湖面,盤旋閃動。忽而又自下而上盤旋而消逝。頃刻,瓢潑大雨從天而降,氣勢磅礴,煞是壯觀。這第四葩就是“山鳴谷應(yīng)”(俗稱應(yīng)山黃)。對門壢的應(yīng)山黃,只要一呼喚,必定跟原聲一樣回應(yīng),有呼必應(yīng),屢試不爽。
(8)
嘴巴基本管住了。腳呢?我家這么多腳,一年四季要鞋穿呀!于是母親就成了鞋的供應(yīng)商。每年將閑碎的布塊,用面粉煮成的面糊在門板上一層一層地疊加糊起來做鞋幫子。索子是用幾股自己親手紡的線搓成。鞋底是一針一線地納起來的。做鞋完全不占正工,總是挑燈夜戰(zhàn)。由于腳多,又長得快,鞋碼子變化很大。一般母親都不去記碼。便使用土辦法,備一根索子,趁我們熟睡時,就一個一個地摸著腳量。最難做的是父親的鞋。父親過去長年打赤腳,腳磨得又大又厚。母親做他的鞋要花費雙倍的時間。
母親每天沒睡一個安穩(wěn)覺。頂多只有三四個小時。夏天,我們常在門口的禾場,或者田埂乘涼。幾張常發(fā)“吱呀”聲、磨光成肉紅色的竹床早被我們搶占光了。母親只好蜷縮在某一個床角,或瞇一下,或拿著蒲扇不停地為我們拍打蚊子,或當(dāng)巡視員,看我們有沒有摔到地下的。有趣的是,我有時感覺她是個超人。那么疲憊不堪,她還經(jīng)常仰望著皎潔的天空,對著月亮跟我們講嫦娥與吳剛的故事,還教我們指認(rèn)“北斗星”“牽牛星”“織女星”……
母親愛“護犢子”。她既教誨我們不要出去撩禍,但也絕不讓別人欺負(fù)我們。父親雖然是“土皇帝”,但她從不仗勢欺人。她不是那種只會疼愛而不管教孩子的母親,兼慈母與嚴(yán)父于一身。對待孩子犯錯,小錯實在管不過來,但大錯絕不放過。大哥八九歲時,在灣里與群童賭博,母親得知后,手拿著一個光滑的、用來捶打濕衣服的棒槌,躡手躡腳地走到他后面,二話沒說就照他捶了兩下!捶得大哥還沒醒過神來就拔腿飛跑。追呀追,直到大哥求饒才放下。從此,大哥從不瞄牌一眼。這一招,讓我驗證了臺灣學(xué)者余世維的觀點:“小孩,必須痛打兩次,方可長記性。”
(9)
我們這個家從來沒有因為家大口闊,而嫌棄哪個是多余的。再窮再苦,擠在一個屋里,總覺得還是暖洋洋的。日子熬到剛剛有點模樣,不愿發(fā)生的事偏偏發(fā)生了。
我畢業(yè)后參加工作的第二年,1982年。恰逢我放農(nóng)忙假(那時家里有責(zé)任田的,機關(guān)干部要放幾天農(nóng)忙假)的第二天,5月6日。這一天注定要讓我悲痛一輩子,痛悔一輩子。因為在這之前,我為了乞求父親少抽煙或不抽煙,與他大吵了一架。畢竟父親畢生只有兩大愛好——抽煙和下象棋。不該逼迫父親啊!
這一天,父親溘然去世,腦溢血。剛起腳,正早粥。噩耗傳來,我如五雷轟頂,亂箭穿心。父親啊,當(dāng)初我與你吵架,您為何那樣善良大度,不給我?guī)讉€爆響栗子呀?撫今追昔,悲從中來。
頂梁柱倒下,全家黯然失色,群龍無首,萬緒無頭。千斤重?fù)?dān),怎叫一個羸弱女子扛得起?兄妹六人只有大哥成了家,并有了三個孩子。二哥二十七,還沒成親。最小的妹妹已有十七歲。家徒四壁,全家唯一像樣的東西是一張硬面方桌。哦,還有土改時分的淡褪了朱紅、破損不堪的摞櫥和梳妝臺。更何況,母親多年“怪病”纏身。
屋漏更遭連陰雨。如果說父親病故是“天崩”的話,那么二哥失常就是“地裂”。
二哥從部隊復(fù)員,心神恍惚,茶飯不思。他時常發(fā)了瘋似的四處亂跑,又入了魔似的悄然回家。大哥抱著母親痛哭:“多聰明伶俐的二弟呀,萬一……我們這個家豈不雪上加霜?”母親沒有選擇逃避。“兒呀,閻王不會那樣便宜地把我收走,只要我眼睛睜著,留下一口氣,也要把這個千鈞重?fù)?dān)扛起。”她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沖破一個個生活難關(guān),排除一個個前進障礙。她每天早晨用開水沖一個雞蛋或鴨蛋給二哥喝,并不時地跟他話聊。為求醫(yī)她到過他鄉(xiāng)異域,為求神她跋涉古剎深山。盡管窮甲鄉(xiāng)里,她也要四處籌措錢物為他娶媳婦沖喜。也許是送子娘娘被她老人家的“愚公精神”感動了,給二哥送來了“二子一女”。雖說喜事連連,但也包袱重重,他家便成了響當(dāng)當(dāng)?shù)摹案F二代”。由于兒弱,母親經(jīng)常托福挨罵,耳里聽出了“繭子”,心里滴出了鮮血。小孫子在一歲多時得了一場重病,昏迷不醒。母親心急火燎,忙手忙腳,卻招來不堪入耳的辱罵和莫名其妙的奚落與鄙視。母親默想:罵算什么?孫子比天大。這種日子,注定母親活得最苦。如果可以頂替,為了兒孫好,她寧愿去死。守候一整夜沒眨眼,孫子醒來,她才露出笑臉。如此的淡定和堅守,終出功果。二哥病愈。三個侄兒侄女均已大學(xué)畢業(yè),兩個侄兒還齊刷刷地雙中公務(wù)員省考分組“狀元”,當(dāng)上了人民警察。
(10)
母親多年“怪病”附體,是有名的“藥罐子”。不時到鬼門關(guān)去走一遭。記得小時候,常見母親手捂著腹部,雙膝跪在地上,嘴咬著床弦,豆大的汗珠往地上直滾。如果病發(fā)在晚上,我們或結(jié)伴到鄰村請醫(yī)生,或守候在母親身旁。母親那無奈和呆滯的目光,看到我們有的挨在那褪了漆的摞櫥邊,有的泣不成聲,凄惶落寞。她呻吟:“閻王爺啊,你收我不是時候,我的任務(wù)還沒完成呀!”吞了幾粒藥,稍好一些,她就撐起來照常出工,或漿衣洗裳,或燒火做飯。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丟了槳就是網(wǎng)。有時候,我們暗自嘀咕:是不是我們屋里有鬼呀!好多次,母親病在屋里,我們不敢出門。放牛或放學(xué)回來了又不敢進屋。生怕不該發(fā)生的事發(fā)生了。
這是個端午節(jié)。我凌晨四點起床,騎著水牛去趕“露水草”(端午節(jié),太陽曬了的草有毒,所以早起將牛喂飽)。本來按慣例興沖沖趕回家有老面粑和鴨蛋吃。然而,印入眼簾的是清爐冷灶,不見炊煙。母親又發(fā)病了!我們家鄉(xiāng)對這個節(jié)日是很重視的。有姑、姐的獨兒,這天在胸前掛著頭幾天打好的“蛋絡(luò)子”,有的蛋絡(luò)打三個節(jié),分別裝上雞蛋或鴨蛋。每個蛋還要打紅胭脂,儼然一個美麗飾品。我家人口多,一人攤一個蛋就不錯了,沒煮熟到手就搶著吞到肚子里了。有“蛋絡(luò)子”也派不上用場。后來,母親還是扶墻摸壁給我們做了老面粑,還每人發(fā)了個鴨蛋。我們和著淚水往肚子里吞。母親你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啊!
當(dāng)我參加工作多年后在城里混了個臉熟時,便為母親尋醫(yī)問診。1987年,我將母親接到市中心醫(yī)院,做了全面檢查。重點查了一下“怪病”。原來,是一個“怪物”作怪,殘害了母親好多年,弄得母親生不如死。一個菱形、小指大結(jié)石,像矛一樣扎在母親的輸尿管上,不疼得鉆心才怪。由于是“怪石”,大夫費了很大力氣,小心翼翼地將它取出。母親“石”去病除,如釋重負(fù),重見日出。我們心中的“怪病”疙瘩解除了,松了口氣。俗話說:寧可走個當(dāng)官的老子,不能死個要飯的娘啊!
我雖排行老四,但有一定的話語權(quán)。把母親從閻王爺那兒拽回,我獨斷專橫地給母親立了個規(guī)矩,七個字:吃好玩好莫做事。按現(xiàn)在的平均年齡,父親和母親要活到一百五十歲,才夠保本。然而,父親只活了五十六歲就撒手人寰。我常囑托:“母親啊,您要爭口氣,活到九十四歲,把本扳回呀!”于是,我給母親訂了“三個一”計劃:去一次首都北京,不枉做一回中國公民;坐一次飛機,鳥瞰祖國山河;觀一次大海,飽覽驚濤駭浪。
(11)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家新一輪“革命”開始了。家庭人口裂變增長。靠一點田地注定養(yǎng)不活。于是全家人不約而同地尋找了一條革命路線,即毛主席路線:農(nóng)村包圍城市。進城謀生,重新創(chuàng)業(yè),談何容易?住房,就業(yè),就讀,各種矛盾紛至沓來。母親也隨大軍進了城。這個昔日“打工妹”,如今變成了老太婆。母親多半在開“麻木”(載人三輪摩托車)的三哥那兒住。她是個不言苦,不言累,不添亂,不貪閑的人。
有一天,我去探望母親,穿窄巷、拐彎抹角地找到了出租屋。見三哥一家五口蝸居在一間屋里,還加母親在旁邊搭了個鋪。一樓,又潮濕,又陰暗。母親在見雨就漏的陽臺上放了一個破煤爐子,一個砧板,一把菜刀,幾個碗碟,幾雙筷子。一點豆腐干和咸菜攤在案板上。佝僂著,火怎么也生不旺。見狀,我負(fù)罪感油然而生:這進城不是讓老母受二茬罪嗎?我不是高高在上借故工作忙而在眼皮底下忽略了母親的存在嗎?我許了愿而未信守算是個人嗎?我不應(yīng)該在母親面前好好贖罪嗎?我愧疚,我自責(zé),我汗顏,愿將天下所有責(zé)罵的詞匯都用在自己頭上。
愧疚自省,我很快將母親接到了我身邊,作好了安頓。也很快,我?guī)ш牻M團實現(xiàn)了“三個一”的前兩個一。母親說:“噢,到了一次首都,心滿意足了。”特別是瞻仰毛主席遺容和觀看天安門升國旗,她更是精神頓添,五更而起,快步如飛。
現(xiàn)在,母親雖到耄耋之年,但仍不健忘。兒、孫、重孫一串四五十人,每個人的年庚八字,她都耳熟能詳;每個人的性格愛好,她都了如指掌。哪兒遇到什么疑惑,她也能略施小計,支上一招。每當(dāng)過節(jié),我們圍爐夜話、坐擁而歡的時候,總有褒贊和戲謔:母親是我家的“政治家”,教我們認(rèn)形勢,識時務(wù)。母親是個“文學(xué)家”,經(jīng)常出口成章,妙語連珠。母親是個慈善家,總是教我們積德行善,舍己為人。一句話,她是我們大家的“大家”。
閻維文的《母親》,旋律動聽,但不適合我。我家沒有折疊傘,放牛或出工時,母親幫我穿的是蓑衣,戴的是斗笠。
賢者有言:世界上有兩件事不能等:一孝道;二行善。
今年,母親八十壽辰,我將深深地鞠一躬,去實現(xiàn)第三個“一”:坐郵輪,觀大海,遂心愿。
(責(zé)任編輯 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