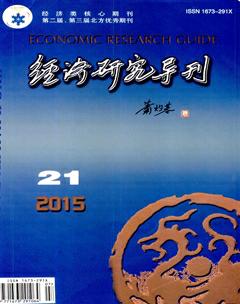聯邦主義對戰后歐洲一體化的影響分析
張自楚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廣州 510420)
聯邦主義源自古希臘和歐洲中世紀的政治思想理念,它本身既是一種理想也是一種制度。作為觀念形態的聯邦主義,表現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民族主義,主張建立權力集中、統一的民族國家[1]。作為國家政治組織形式的聯邦主義,是指政治上介于中央集權和松散的邦聯之間的一種制度,統一在聯邦內的各邦是曾經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擁有自主權的國家[2]。聯邦主義也是一種一體化的政治理論,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聯邦國家。聯邦主義對戰后歐洲一體化有何影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本文將分析聯邦主義對戰后歐洲一體化產生影響的主要表現及其主要原因,并就聯邦主義對歐盟未來的影響進行展望。
一、聯邦主義對戰后歐洲一體化產生影響的主要表現
(一)聯邦主義為歐洲派人士提供了思想基礎
1795年康德發表的《永久和平論——一個哲學方案》提出了以歐洲聯邦形式實現永恒和平的思想,成為現代聯邦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一。康德主張通過建立一個體現聯合起來的權力和意志的聯邦來避免戰爭、實現歐洲的永久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聯邦主義對許多歐洲派人士,如法國的莫內、舒曼、聯邦德國的阿登納、比利時的斯巴克等產生了重要影響。聯邦主義者們認為:主權國家已經衰老過時,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在他們看來,西歐國家由于市場狹隘、投資機會有限,因而缺乏生命力。在政治上,民族主義會產生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傾向,因而是反動的。民族主義一是在國內往往導致極權,二是在國際間容易引發沖突和動蕩,因此他們號召成立某種超國家性的機構,以避免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產生[3]。戰后初期,聯邦主義運動在歐洲迅速開展起來。1946年,歐洲聯邦主義者聯盟在巴黎成立,50來個聯邦主義運動組織共同為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歐洲聯邦而積極活動。其中既有學者、思想家,還有許多主張聯合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莫內和舒曼等人的主張都被視為聯邦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聯邦主義者們主張先在西歐建立一個歐洲聯邦或歐洲合眾國,然后把蘇聯和東歐包括進來,繼而實現整個歐洲的和平與民主[4]。
(二)聯邦主義推動了歐洲共同體的建立
在聯邦主義思想影響下,經過莫內、舒曼、阿登納、斯巴克等聯邦主義者的大力推動,20世紀50年代,歐洲一體化正式啟動。1951年4月18日,法、德、意、荷、比、盧六國簽署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根據條約,成員國將煤炭和鋼鐵的生產經營權轉交給煤鋼共同體,并成立了一個超越各國政府而享有特殊權力的高級機構。它的建立標志著歐洲國家已經開始通過讓渡部分國家主權來實現國家間的新型合作,這一制度創新是聯邦主義在戰后歐洲的一個具體體現。煤鋼共同體的成功運作堅定了歐洲政治精英們推動一體化的決心。1957年3月25日,煤鋼共同體六國首腦又正式簽署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至此,歐洲一體化進程擴展到了所有經濟部門。1965年4月8日,六國又簽訂合并條約,條約于1967年7月1日開始生效。根據條約規定,三大共同體將其組織機構合并,建立了統一的部長理事會和共同體委員會,三大共同體統稱為歐洲共同體。歐共體的建立是戰后歐洲一體化的重大成果。
(三)聯邦主義促進了歐洲聯盟的誕生和發展
聯邦主義在爭取實現歐洲聯盟的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100多位歐洲議員組成的跨黨派“爭取歐洲聯盟聯邦主義者集團”,努力推動歐洲聯合向縱深發展。從1985年起任共同體委員會主席,被稱為“羽翼已豐的聯邦主義代言人”的雅克·德洛爾也大力推動共同體改革,將實現歐洲聯邦作為目標。1993年歐洲聯盟建立后,依然存在著要求以聯邦主義為取向,進一步加深聯盟改革的呼聲[5]。1999年1月1日,歐元在由11個歐盟成員國組成的歐元區內正式啟動,這意味著歐元區11國將貨幣發行權和金融調控權讓渡給了歐盟。歐元區成員國自愿讓渡貨幣主權,將其轉移給歐盟,使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具有了聯邦主義因素。《里斯本條約》對《歐盟憲法條約》核心內容的保留,說明歐盟在以深化權力改革為目標的制憲方面得到了肯定和延續[6]。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2010年歐盟推出的“歐洲學期”機制,在鞏固財政紀律和加強經濟政策協調方面實現了創新[7]。2013年,除英國和捷克之外,歐盟25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正式簽署了《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與治理公約》,強化了歐盟對成員國的財政監督與約束[8],使歐盟向著財政聯邦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聯邦主義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
(一)聯邦主義是歐洲一體化的思想淵源之一
康德所構想的聯邦通過以下三個步驟建立:第一,通過簽訂和平條約處理國家間的爭端與沖突;第二,在歐洲建立統一的共和體制;第三,在歐洲建立聯邦的基礎上建立世界聯邦,成立國際政府,以此來避免戰爭、維持和平。康德的聯邦主義理論,推動了一體化理論的發展,激發了歐洲人民建立歐洲聯盟和歐洲合眾國的熱情并指導了他們的實踐。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的庫登霍弗·卡勒基領導的泛歐運動和法國總理白里安提出的“白里安計劃”被視作聯邦主義思想的實踐。白里安在1930年5月《關于組織歐洲聯盟體系》備忘錄中,陳述了建立歐洲聯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聯邦主義者斯皮內利和羅西起草了帶有明顯聯邦主義色彩的《文托泰內宣言》,號召人們將抵抗運動與創造自由統一的歐洲聯邦結合起來,永遠消除歐洲的分裂和戰亂。歐洲各地的抵抗運動組織也紛紛呼吁在戰后建立以超國家的政府、單一的聯邦軍隊以及聯邦最高法院等基本框架為核心的“歐洲聯邦”,以消除歐洲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隱患。在此背景下,戰后歐洲聯合運動發展了起來[9]。
(二)聯邦主義促使歐洲人民對民族主義進行反思,為歐洲國家避免戰爭、維護和平提供了理論基礎
民族主義的演進歷程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即組成國家形態階段、強制消滅其他民族階段、重新發現自我階段和自然消亡階段。一般認為,二戰后歐洲民族主義處于民族主義發展的第四階段。該階段的民族主義已非原來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處于向洲際主義轉化之中的民族主義。而洲際主義既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又在洲際范圍內繼承了民族主義的排他性[10]。這就從客觀上對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歐洲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表明,歐洲各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情感已開始走向衰退,其功能已開始出現衰落的勢頭。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的經歷沖擊了人們對民族主義和主權國家原則的迷信和崇拜,促使人們思考歐洲的新出路。聯邦主義為歐洲國家避免戰爭、維護和平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歐洲中心的國際格局,歐洲列強都被嚴重削弱了,美國和蘇聯代之而起成為超級大國。戰后不久,冷戰又使歐洲成為美蘇對峙的前沿陣地,在此背景之下西歐既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也需要聯合起來求生存、求發展。經濟復興和聯合成為西歐國家追求生存和發展的現實選擇。因此,聯邦主義能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影響、推動其發展,也是歐洲國家在經歷了二戰的創傷后,為避免戰爭維護和平而產生的必然要求。
(三)聯邦主義有利于歐盟及其成員國保護其共同價值觀、改革歐盟的社會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
2013年4月22日,布魯塞爾智庫舉行了主題為“歐盟:走向聯邦還是走向分裂”的第四次年度對話。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發表講話,強調歐洲正需要努力從民族國家邁向聯邦制。對于聯邦主義的態度,歐盟委員會的牢固信念是一種傳統,如果對歐洲一體化三心二意,就只會給逆潮流者以機會,就只會是向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妥協。巴羅佐指出,現如今“聯邦主義”這個詞之所以敏感,是因為多數人對此概念存在猜疑和擔憂,他們擔心在中央集權聯邦制度之下,各成員國家會黯然失色。特別是,大部分歐盟成員國曾經為了爭取自由獨立而長期戰斗,因此他們厭惡中央集權,不愿成為一個聯邦層面之下的成員。對此,巴羅佐強調,聯邦制度不是要建立一個凌駕于各國之上的超級國家,而是要建立一個成員國家組成的民主聯邦。在聯邦主義制度框架下,歐盟國家才能一起應對共同的問題,通過主權的分享,每個國家、每位公民才能更好地駕馭自己的命運。這樣,歐洲人才會為他們自己的國家驕傲、為歐洲整體以及歐洲的共同價值觀而驕傲。巴羅佐還闡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聯邦制是一種政治承諾:無論有多么嚴峻的挑戰,都要找到應對的政策。例如,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歐盟制度設計中的問題凸顯了出來。但是,歐盟修訂和出臺了一系列法令和規章以彌補經濟治理方面的不足,使歐盟擁有了更大的權力,歐盟成為更強有力的角色。因此,從制度上看,歐盟現在的一體化程度比以前更高了。但是,由于在高層的決策和實施之間存在著矛盾、歐盟公開聲明的原則和實際履行的政策之間有差異、各國公眾輿論不一、政治爭論仍然主要圍繞著國家利益而進行、政治心態往往落后于現實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歐盟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11]。
三、結論
戰后歐洲一體化歷經曲折,從歐洲共同體發展到今天的歐洲聯盟,成員國之間始終圍繞著如何對待國家主權、如何協調成員國與一體化超國家機構間的權力均衡、如何調解成員國之間的利益以及如何應對外部挑戰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爭執和妥協。聯邦主義有利于加強歐盟層面的超國家性,其主要目標并非尋求權力完全向歐盟機構的轉移和集中,而是通過歐盟內部結構的調整優化、使得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職責權限重新平衡,使歐盟的機構運轉更加有序、歐盟的決策更有效率、提高歐盟的民主合法性、加強歐盟對外政策的統一性和連續性,從而提升歐盟作為一個國際行為體的競爭力和應對挑戰的能力。當然,歐洲一體化進程也表現為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兩種理論的交鋒:究竟是在加強政府間合作的同時繼續堅持國家主權原則,還是進一步加強歐盟的超國家主義因素。也就是說,歐盟到底是應該向聯邦發展還是向邦聯發展,也一直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爭論的焦點[3]。
從戰后歐共體的建立發展到今天,歐盟已經擁有了一系列不可否認的聯邦制元素:擁有以提升歐洲整體利益為責任的超國家主義機構——歐盟委員會;擁有通過直接選舉產生且立法權在逐漸增加的歐洲議會;還有獨立運作的歐洲中央銀行以及判決具有約束力、法律效力在各國法律之上的歐洲法院。這些機構都具有超越國家的權力,并且其權力還在不斷擴大。其中,歐洲中央銀行和歐元這兩個超國家性事物的蓬勃發展突出代表了歐盟經濟與貨幣聯盟發展的巨大成就[11]。當今國際形勢紛繁復雜、瞬息萬變,聯邦主義可以為歐盟創造有利條件,更好地維護其共同價值觀、改革歐盟的社會經濟模式,幫助歐盟實現其遠大目標。
[1]Brent Nelson,European Uni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4:235-240.
[2]劉泓.歐盟與歐盟屬下的民族國家[J].世界民族,2004,(3):4.
[3]房樂憲.聯邦主義與歐洲一體化[J].教學與研究,2002,(1):64-85.
[4]姜南.淺析戰后歐洲一體化理論[J].史學理論研究,2013,(1):85-86.
[5]黃正柏.戰后歐洲聯合中“聯邦主義”思潮的初步考察[J].世界歷史,2000,(5):5-6.
[6]王從峰.歐盟立憲的本質探析——兼評《里斯本條約》的批準[J].當代法學,2010,(2):72.
[7]周茂榮,楊繼梅.“歐洲學期”機制探析[J].歐洲研究,2012,(3):17-27.
[8]應霄燕,趙建芳.歐債危機以來歐盟的改革及其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J].當代世界,2013,(9):58.
[9]李世安,等.歐洲一體化史:第2版[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4-12.
[10]劉泓.歐盟與歐盟屬下的民族國家[J].世界民族,2004,(3):3.
[11]徐奇淵.歐盟:走向聯邦還是走向分裂——布魯塞爾智庫對話(2013)紀實[J].國際經濟評論,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