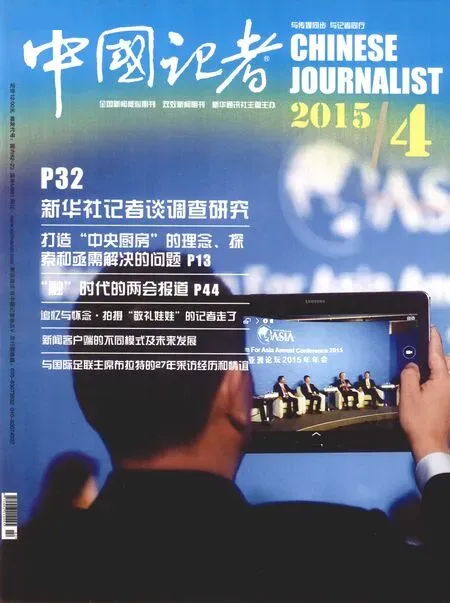90后務工者:炫酷外表下的脆弱內心 —— 一名攝影記者對90后進城務工者群體的關注與思考
90后務工者:炫酷外表下的脆弱內心
—— 一名攝影記者對90后進城務工者群體的關注與思考
□ 文/李震宇
提要:環境肖像之所以能打動人,也許并不在于刻意追求的攝影技法與視覺效果。對拍攝群體內心世界的描摹,是攝影記者邁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本文作者講述了他探尋90后進城務工者內心世界的過程。
關鍵詞:環境肖像 90后進城務工者 攝影思考
每年春節后,各地企業陸續開工,來自全國各地的進城務工者也在此時涌入城市。在勞動力市場的門口,企業主舉著牌子張貼著招工信息,這些牌子大多是從包裝箱上撕扯下來的牛皮紙,形狀不一,上面手寫著幾行蹩腳的漢字:需求工種,每月工資,是否包吃包住等等,一目了然,經常還能看到幾個錯別字夾雜其中。求職的進城務工者往來穿梭,反復比較,與企業主討價還價。這種最原始的勞動力交易方式,仍在發達城市天天上演。
從2012年起,我開始關注90后進城務工者這一新興群體。這些年輕人早早地走上商品經濟的流水線。這一代人選擇用夸張的形象來標新立異,去極力迎合大城市。然而,在老家人眼里,這些“農二代”花枝招展,脫離了與土地的聯系,不再是農民;在城里人看來,他們骨子里卻透著鄉土氣息,不折不扣的“鄉下人”, 依然無法順利融入城市文明。這個新群體,估計有4000萬人。
也許,青澀的面孔,時尚的穿著,夸張的發型……是普通人對這一群體的模糊印象。但,當你拿起相機深入這個群體后,就會發現,其實在那些炫酷的外表下,卻藏著一顆顆脆弱的心。
“古惑仔”文暉:抽煙解解悶,不敢抽好的……
2012年4月11日,杭州歷史博物館重建工程接近尾聲,我帶著相機來探營。采訪結束后,我準備回報社發稿,突然發現博物館門口,一位打扮“時髦”的小伙子正在修剪新種下的樹苗。小伙子染著一頭黃發,嘴里叼著煙,耳垂上戴著閃亮的飾品,穿著一件衣領、袖口上都已磨破的阿迪達斯運動服。走近一看,小伙子胸口還刺著紋身,圖案很奇怪,有點“古惑仔”的味道。(圖一)
我告訴他,我是攝影記者,覺得他的形象很酷,能不能拍張照片。他愣了一下,不知所措,我再次表明來意。小伙子與旁邊的工友尷尬地笑了笑,顯得有點害羞,“你去問我們老板吧,去問他。”他找了個理由回絕了我。“你們老板在哪,我去找他。”我堅持問。“在后山上,你自己去找吧。”
對于我的拍照要求,老板很爽快地說:“沒問題,你肯定拍得到!”我們回到“古惑仔”干活的地方,他仍在這里守著。盡管老板同意,但面對鏡頭,小伙子仍顯得有些害羞,左躲右閃。為了緩和氣氛,我跟他聊了起來。小伙子叫文暉,廣西百色人,1992年出生,初中沒讀完就綴學了,在杭州一家園林公司打工。我悄悄問他收入有多少,他說不多,就2000多塊,剛夠吃喝。“那你還抽煙?”我問他。“沒辦法,無聊嘛。”文暉說,一個人在杭州,抽煙能解解悶,不敢抽好的,沒錢買。最后,小伙子勉強同意讓我拍照,可等我快門剛落,他就逃開了,僅此一張。
被鏡頭嚇跑的袁方軍:不想干了,要離開,但去哪兒?
2012年12月19日,我走進義烏一家制襪工廠,尋找合適的采訪對象。在車間里,一位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吸引了我的注意。他胸前系著白色圍裙,站在工作臺旁邊,熟練地將身邊堆積如山的絲襪半成品套在模具上進行翻襪操作,身材高且瘦,可能是站累了,大腿靠在工作臺邊支撐著自己,從側面看整個人形成一個“S”形,極富視覺感染力。
多年積累的職業敏感使我舉起相機對準這個小伙子。讓我沒想到的是,可能是動作過快,小伙子看到鏡頭對著他時,竟嚇得大叫一聲,趕忙丟掉手中的活,飛步離開了工作崗位,把周圍的工友都逗樂了。我問,他跑哪去了?旁邊的工友說:“你去廁所找找,他朝那邊跑過去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了過去,結果小伙子真的跑到廁所里,把自己關在里面不肯出來。
我為自己突兀的行為懊悔不已,這么理想的采訪對象,我不愿意輕易放棄。隔著門板,我輕聲告訴他我的來歷。他說:“你不要拍我,難看死了。”我苦笑了一下,慢慢開導他。就這樣,我們在廁所里隔著板聊了起來。這是一家典型的小作坊企業,燈光昏暗,條件簡陋,廁所自然好不到哪去。在異味中,我與他推心置腹,意外地發現這位小伙子竟還是老鄉,都是湖北人,他來自恩施。有了這層關系,我們的談話也越來越順利,小伙子叫袁方軍,1993年出生,初中畢業后,就跟著叔叔來到浙江義烏打工,已經換了好幾家工廠,目前在這家制祙廠做翻祙工,月收入2000多元。
小袁開了門,走出來。他低著頭告訴我,他并不喜歡這里,每天不斷重復的工作,枯燥無味,此外還要面對管理人員的指責與監視,稍有失誤就扣錢,這些都讓他對前途感到灰心。沒有多少年輕人愿意干這個工作,因為缺少可以傾訴的同齡人,小袁逐漸變得沉默寡言。他說,不想干了,要離
開,但去哪兒?他說,他不知道。“我沒讀過什么書,不像你們,可以做記者……”

▲圖1

▲圖2

▲圖3
最后,我拍到了這樣一張照片(圖二),依然是那個“迷人”的S形,小袁看著我的鏡頭,嘴角似乎流露出一點點微笑,是對現實生活的無奈?還是自嘲?
與四個“洗剪吹”一起找工作
《與四個“洗剪吹”一起找工作》這張照片在微博上流傳很廣(圖三)。2012年2月15日,義烏市勞動力市場,李恩銀等四位來自貴州農村的年輕人,頂著夸張的“時髦”發型找工作。網友們在轉發時留言:“這不是大陸版的洗剪吹四人組么?”在留言里也有祝福:“農村孩子不容易,大家多給點理解吧。”
那是我連續第三天守在義烏市勞動力市場的門口遇到的采訪對象。內行都知道,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出照片的好地方。每年春節后,當地企業陸續開工,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來自全國各地的進城務工者也在此時涌入城市。我站在臺階上,廣場上黑壓壓一片。幾簇鮮艷的小黃點突然出現在我的視野里,在人群中穿梭前行,李恩銀和他的同鄉好友來到這里找工作,夸張的發型和“時髦”的打扮,讓這幾個小伙子在求職人群中顯得格外另類,職業的敏感性再次讓我迅速拎起相機奔向目標。
在他們面前,我簡要說明來意,他們盯著我手中的相機,怔了一下,彼此望著對方,都不知道說什么,臉上擠出尷尬的微笑。李恩銀(右二)顯然是他們的“頭”,他略帶懼色地對我說:“能不能,不要采訪我們,我們什么都不懂……”做攝影記者經常會碰到這樣的情況,我不放棄,與他們耐心交流,和他們一起看信息找工作,邊走邊聊。漸漸地,他們與我熟起來。李恩銀告訴我,他們都來自貴州都勻,坐了幾十個小時的火車,剛從義烏下車就趕到這里。四個人都出生于1993年,從小一起長大,今年19歲。初中畢業后,他們在家里呆不住,就一起出來打工賺錢。千里之外的義烏是他們的第一次遠行。
我問他們,為什么染了個這么夸張的發型?李恩銀笑了笑說,說不上為什么,這個,好像很潮吧。我繼續問他,你希望找個什么樣的工作?他說不知道。他們沒有技術,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他們只剩下年輕和敢闖。我決定陪著他們找工作,記錄青春與現實如何相遇。
在勞動力市場外,舉著招工牌的企業主沿著通道兩旁站成兩排,求職的農民工密密麻麻地將中間“填滿”,我們順著人流慢慢向前挪。李恩銀和他的小伙伴看中了一家服裝廠的工作,月薪2800到3500元,而且包吃住。
“這樣,我一年就能攢下3萬塊,夠老家好幾個人的收入了。”李恩銀盤算著。我看了看招工牌上的信息,這是義烏的一家內衣廠,老板需要熟練的擋車工和裁剪工。我問老板:“你們這里新手招嗎?”這位老板看了我一眼,又瞄了瞄他們四個人說,“學徒也可以,1200一個月,押金1200,要不要來?”
“還要交押金,我們沒這么多的錢!”完全沒有打工經驗的李恩銀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那當然,你學會就跑了怎么辦,我不是虧大了?”老板用他特有的生意經回復。李恩銀的確沒有這么多錢,從老家出來,車票是他們最大的開支,剩下就沒多少了。他們得趕緊找到工作。盡管眼前有著成千上萬的崗位,但他們這樣的新手沒有任何挑選的資本。最后,他們還是挑了家招學徒的工廠,月工資1200元,不用交押金,經過幾輪挫折,他們對這個結果很滿意。
臨走時,我請四個人在勞動力市場附近的小店吃了頓飯,這是一家很廉價的餐館,專門針對勞動力市場的打工者,菜價從幾塊到二十幾塊不等。盡管十分簡陋,他們仍很感激。這是他們從貴州出來后吃的最豐盛的一餐,火車上就啃了幾塊面包。
有限的教育背景,微薄的經濟收入,殘酷的生存環境以及逼仄的未來發展,讓這些年輕人沒有能力或沒有意識提升自我。偌大的城市生活和文化排斥了他們的父輩后,再一次將厚厚的隔膜矗立在他們面前。農村故鄉,他們不想回去;光鮮城市,他們難以立足。
“他們還是看不起我,覺著我既傻又土。”一位90后務工者這樣對我說。至今,我仍在關注著這個群體,希望我的照片能喚起公眾對他們更多關注。(作者單位: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圖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