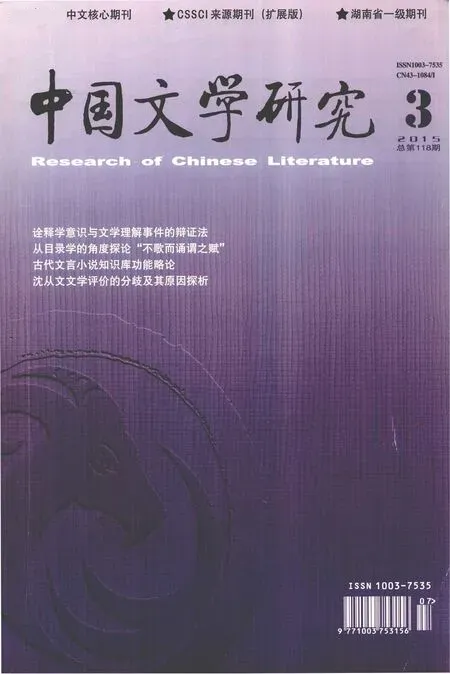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情景合一”:蓮花品質與松樹風格——湘漓文化特質初探
陳仲庚
(湖南科技學院 湖南 永州 425100)
“湘漓文化”是以湘水和漓水為主流、以湘桂走廊為大致范圍,融山性文化與水性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于一體的文化形態。這是近幾年來湖南永州與廣西桂林的學者共同探討的課題。這里有橫亙華南的五嶺山脈,是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分水嶺;秦始皇修靈渠,將湘江之水“湘漓分派”,又連接了湘江和漓江;漢武帝設零陵郡,轄永州和桂林。共有的山水,形成了共同的生產生活方式;曾經共有的行政區劃,形成了相互認同的文化心態。這里還是人文薈萃之地:楚文化、百越文化、嶺南文化在此交匯,來自北方的華夏文化與土生土長的南蠻文化在此聚集,湘學與桂學也在此交叉融合——這樣的山水,這樣的人文,定然會形成獨具特質的文化,本文意欲對此展開初步的探尋。
一、山水凝成的哲學底蘊
湘漓文化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條支脈,對其特質的探尋,無疑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大背景。大致來看,中國文化具有山水凝成的文化特征。
從地理類別看,中國主要是大河大陸型的地理環境。大河是水,大陸也可以說是山,山水相凝,衍生出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古代文明,正是利用河谷平原的優勢,率先在黃河、長江流域開放出燦爛的花朵。它選擇了一條既不同于海洋民族(如希臘、羅馬人),也不同于游牧民族(如古代阿拉伯人)的發展道路,一開始就以農業經濟作為文化發展的基點,最終演進為一種高度發達、極端成熟的以農為本的文化形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河谷平原的優勢,正是在山的幫襯下形成的:水是大山輸送的,肥沃的平原土地也是由大山帶來的。尤為重要的是,山還是人們生存生活的保護屏障,中國古代的城市,幾乎無一不建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對傳統社會的國人而言,山是心靈的依靠,水是外物的利用;所以山狀“仁”,水擬“智”。由此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山水—人生”哲學。
中國的哲學,從一開始就將人與自然看成是一個整體:人從自然中產生,自然向人生成。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在孔子看來,山和水都不是純自然的,它們的某些特點和秉性,也正與人類的某些特點和秉性相統一,錢穆對此解釋說:“水緣理而行,周流無滯,知者似之,故樂水。山安固厚重,萬物生焉,仁者似之,故樂山。”大抵是說,山的特點是厚重堅忍,與仁者相似;水的特點是靈動變化,與智者相似。這種解釋,也正是運用“道法自然”的方式來解釋“仁”和“智”的內涵。也就是說,在人與自然相統一亦即“天人合一”的問題上,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是高度一致的。
雖說在天人合一的問題上儒家與道家高度一致,但在對山水的重視程度上則是各有偏重的:儒家更重視山,與之相應的是仁;道家更重視水,與之相應的是智。因此,大致地進行區分,儒家可說是山性哲學,道家可說是水性哲學。
首先,從陽剛與陰柔的對比來看,儒家更多陽剛之氣,偏重于山的特征;道家更尚陰柔之性,偏重于水的特征。儒家心中充滿“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為人生理想的實現而奮斗不息,《周易大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很能代表儒家所主張的人生態度,也是其學說的一個基本特征。道家則貴柔守雌,強調無為不爭,特別崇尚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第八章》)道家所持有的“清心寡欲,見素抱樸”心態,希望退回到“小國寡民”、“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社會理想,與儒家剛健有為、奮進不止的精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從恒常與變動的對比來看,儒家看到的是穩態的東西,是“經”,是“常”;道家眼中的事物則是變動不居的,沒有質的穩定性。在社會歷史的發展方面,儒家看到的是“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荀子·無論》),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循環往復(《漢書·董仲舒傳》)。即使有變動,也只是屬于不可動搖的“常”的補充而已,孔子因革損益的思想,就是這種思維的結果。在人生意義和價值方面,儒家追求精神上的永恒,試圖“為萬世開太平”,這也是因為堅信人生有其恒定的內在價值,而且這種價值不會因社會變遷、人生際遇的不同而消失。道家感嘆人生的短暫和變動不居:“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莊子·知北游》);“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莊子·秋水》)。道家為人世的變化而悲哀,以其為不常。他們認為唯一恒常的東西就是“道”,而正是在“道”的永恒性對比之下,更顯出人世、人生的短暫和變動不居,這與儒家哲學的思維趨向恰好相映成趣。
再次,從重“仁”與崇“智”的側重來看,儒家強調“利天下而弗利己”的群體之仁;道家強調“保身全生”的個體之智。《論語》說:“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這是儒家仁學的具體體現;同時也說明,儒家心目中的“人”,是以體認、實踐“仁”德為人生旨趣的。仁的實現,在于主體修養的升華,然后推己及人,或者說是從一般意義的人我關系的協調來實現仁。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一種人際關系學”。尤為重要的是,這種人際關系學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而是以犧牲個體服從群體為前提的,《唐虞之道》中說:“利天下而弗利(己)也,仁之至也”。“利天下”就是維護群體利益,“弗利己”自然要犧牲個體利益,這是最高的“仁”,也是最高的人生價值。道家則是另外一幅景象,《老子》中說:“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莊子》強調“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養生主》)。很顯然,老莊所重視的主要是一種人生的智慧,它以確保人生的“無尤”、“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為價值目標,是一種個體之智。也可以說,個體的生命價值和精神自由,在道家哲學中具有至高無上性,與儒家的群體至上理念,形成了必不可少的互補。
儒家哲學肇源于黃土高原,沿黃河兩岸匯聚到泰山腳下,凝結成山性哲學;道家哲學起始于漢水上游,隨漢水南下匯集到長江中游,激蕩為水性哲學。兩種哲學隨著南北文化的交流融通,與南嶺山脈、湘漓流域的山水相結合,便形成了獨具特質的湘漓文化。湘漓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周敦頤,正是高度融合了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才開創出影響至今的濂溪理學。
二、南北匯通的人文源流
在湘漓文化特質中,不僅有南北山水凝成的哲學底蘊,更有南北匯通的人文源流,其最早的始源,無疑是被稱為“中華文明先祖”的舜帝。四千五百年前的“舜帝南巡”,無論是對中國的歷史或文化史,都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它不僅帶來了民族大融合,也帶來了文化的大匯通。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司馬遷這一段話,為舜帝其人的真實性和傳奇性提供了權威證據,舜帝遂成為南嶺山脈的永久符號,湘漓流域的不朽名片。
舜帝南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歷史上雖有“南征”、“避難”等不同說法,但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是為了“德服三苗”。舜帝的此次南巡,我們從文化典籍、民間傳說乃至于歷史遺跡中,找不到帶兵打仗、戰爭硝煙的痕跡,相反,關于舜帝奏《韶樂》、歌《南風》的留存記載和痕跡倒是屢見不鮮。章太炎《古經札記·舜歌南風解》云:“舜南巡蒼梧,地本屬楚,其歌南風,蓋即在南巡時,闕后楚之《九歌》九章,當即南風遺音,故有《湘君》、《湘夫人》等篇,即用舜律,而又詠舜事也。且夷樂亦惟南音最合。”楊東晨還據此認為“舜帝南巡,當有親自去體察南方民風歌樂之意”。除了歌《南風》,就是奏《韶樂》,《春秋繁露》云:“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韶樂》是舜帝所創,來自于北方。舜帝演奏《韶樂》的地方,至今還留下了韶山、韶關等地名。舜帝就這樣奏著《韶樂》、歌著《南風》,走遍了南方數省,最后將自己的遺體也留在了南方九疑山。
根據徐旭生先生的考證,自炎黃時代開始,中華大地形成為三大部族集團,即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南蠻集團。顧劼剛認為,堯舜禪讓說是東西民族混合的結果。晁福林認為:“部落聯盟領導權的禪讓制是古代早期國家構建的重要標識。關于堯、舜、禹之間的領導權的傳遞,《尚書》所載言之鑿鑿,無可質疑”。既然國家權力的禪讓只在東西部族之間傳遞,也就意味著南蠻部族的權利并沒有在國家的權力中得到體現。而南蠻部族既有山川之險,又有眾多族支,“九黎”、“三苗”之稱就是族支眾多的表現。在他們的權利沒有結合進國家而又要讓他們服從于國家的權力,并讓他們心服口服地與北方的兩大民族融合為一體,這確實是武力很難解決的問題。蔡靖泉先生對此進行解釋說:“武力征伐不能服眾,行德喻教方可化民。虞舜棄力征而以德化三苗,足顯其明哲賢能之‘圣’。虞舜在南國的行德,即如《南風歌》所云的‘解吾民之慍’、‘阜吾民之財’;虞舜在南國的喻教,也即‘慎和五典’,使苗民‘移風易俗’,明‘五常’之義,由野蠻走向文明。”正因為如此,所以舜帝南巡一路宣講著道德教化,同時伴隨著音樂熏陶,并以自己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最終“勤民事而野死”,還將自己的圣體也留在了江南九疑;再加上二妃的淚灑斑竹、殉情瀟湘,他們的事跡使南方的九黎、三苗大為感動,最終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來自北方的王權,三大部族終于“混合”為一體。可以說,如果沒有舜帝的南巡,中華民族的大融合、中國大一統國家的形成,都是很難想象的。
舜帝作為千古圣人,因為藏精九疑而使舜帝精神與山之特質合二為一;舜之二妃南來尋舜不遇,投江殉情,成為湘妃、湘夫人,又使二妃之情與水之特質合二為一。因此,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九疑山算不上高大,但它重于昆侖;瀟湘水算不上深遠,但它蓋過長江。此后的歷朝歷代通過連綿不斷的祭祀和唱誦,舜帝精神不斷地得以強化,對九疑山及其湘漓地區產生了尤為重要的影響。
嗣后,文人墨客對舜帝精神的唱誦也對湘漓文化特質的形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文人的唱誦,最早是屈原,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舜帝精神的追尋和贊頌,二是對湘漓流域古老民歌特別是《湘君》《湘夫人》等篇什的收集整理。章太炎認為“楚之《九歌》九章,當即南風遺音,故有《湘君》、《湘夫人》等篇,即用舜律,而又詠舜事也”。這一方面說明了屈原對“南風遺音”的收集整理之功,為中國文學保存了一種古老的文體,使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標一幟;另一方面,因“舜律”、“舜事”的影響力,又開啟了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傳統,使舜帝與二妃的愛情故事成為千古絕唱。因此,舜帝作為千古圣人,不僅是后世文人實現政治理想的最高典范,也是實現家庭理想的最高典范。
舜帝是北方人,屈原是南方人,他們二人跨越時空的交流,其本身就是南北薈萃。屈原之后,另一個對湘漓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北方人是柳宗元。
宋人嚴羽曾說:“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從遭讒受逐、滿腔悲憤的角度說,柳宗元與屈原的遭際相似,情感抒發相似,政治理想也相似。柳宗元曾寫過一篇《舜廟祈晴文》,其題下韓醇注曰:“(此文)公在永州代其州刺史作”。作為罪臣的柳宗元,在永州時的行動受到限制,九疑山雖近,卻不能親自前往祭舜,代州刺史寫一篇祭文,也算了卻一個夙愿。在祭文中,柳宗元歌頌舜帝的“勤事南巡”,“宜福遺黎”,重點關注的是舜帝對黎民百姓的福祉,體現了柳宗元一貫的民本思想。
作為思想家的柳宗元,其特有貢獻是對中國民本思想的提升;作為文學家的柳宗元,其特有貢獻則體現在山水游記上。柳宗元的文章,多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風格峻峭,自成一路。而山水游記則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柳宗元自己說:“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愚溪詩序》)清人劉熙載評論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藝概·文概》)因此,柳宗元筆下的山水,蕩滌天地萬物,囊括自然百態,在贊賞山水美的同時,也熔鑄了自己的血肉靈魂,這是一曲物我交融、“情景合一”的多彩華章,我們在欣賞其藝術美的同時,也不難感受山水凝成的哲學底蘊。
三、“情景合一”的人格秉性
從中華大地的特有山水,到山水凝成的哲學底蘊,再到南北薈萃的豐厚人文,說明上天特別眷顧湘漓之地,先祖十分恩澤湘漓之人。那么,湘漓人自己該如何作為?文化特質的形成,是人類自身努力的結果,或者說是人類人格秉性的文化顯現。湘漓文化特質,自然也與湘漓人的人格秉性相關。而湘漓人的人格秉性,也恰如湘漓文化的人文源流一樣,具有南北匯通的特征。例如,作為湘漓人的梁漱溟曾對自己的家庭有一個說明:“在中國來說,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論在氣質上或習俗上都頗有些不同。因此,由云南人來看我們,則每當我們是北方人,而在當地人看我們,又以為是來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實兼有南北兩種氣質,而富有一種中間性”。應該說,梁漱溟“一家人”所代表的,正是湘漓人的共有特征。
湘漓大地雖然是舜帝的藏精之所,秦始皇開拓南方留下了千古工程靈渠,但南方畢竟是蠻荒之地,唐以前文化的發展遠落后于北方。到了唐代,在元結、柳宗元的影響下,教育、文化才發展起來,到了宋代則蔚為大觀,出現了能確立湘漓文化特質的代表人物。
宋代的代表人物無疑是理學大師周敦頤。周敦頤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堪與孔孟比肩。《宋元公案》中曾這樣評價周敦頤:“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清大儒輩出,圣學大昌”。也就是說,周敦頤是繼孔孟之后昌興“圣學”的開山之祖,從南宋開始,人們就認為他“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并被稱為“道學宗主”;道州、九江、南安等地紛紛建濂溪祠堂祭祀;宋寧宗賜謚號為“元”,理宗時從祀于孔子廟庭,成為“亞圣”孟子之后的“三圣”。
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兩篇經典之作讓人百讀不解又百讀不厭。一篇是老子《道德經》,短短五千言,人們解讀了數千年,到現在仍是新注、新說不斷;另一篇就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更是精簡到只有三百多字,人們解讀了數百年,似乎還很難讀出個大概。可以說,這兩篇經典,集中了人類的最高智慧和最深邃的思維。
孔孟開創的儒學,到周敦頤的時代已經流傳了一千多年,碩儒名彥濟濟,為什么多無創見,而周敦頤卻能別開生面?有人說,是道州的山水滋養了他,更有人說,是道州月巖的特有地貌讓他直觀地感受了陰陽的變化,所以才有“陰陽動靜,萬物化生”的《太極圖說》。周敦頤的思想成就自然離不開他所處的山水、人文環境的滋養;但同樣,周敦頤也是在與別人同樣的環境下,開創了新的理學。
在一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儒、道兩家互為補充,卻又一直是分流并進的。到了周敦頤這里,形成了交叉匯流:他吸取道家學說,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綜合探討宇宙本原、萬物生成、人性倫常等問題的理論體系。或許,從人格秉性與文化特質的關系而言,他的人性論觀點對我們更有啟發性。
周敦頤將人性分為“五品”: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再加上中。但剛、柔、善、惡都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中,“惟中者也,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圣人之事也”。“中”是什么?宋明理學家喋喋不休地討論了多少年。其實,看看周敦頤自己的愛好和行為就可以明白,“中”就是“蓮花品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后人贊賞周敦頤所描述的蓮花品質時,注重的往往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而忽略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其實,前者只是表現,后者才是本質。“中通外直”也就是“中”、“中節”,是周敦頤所堅守和提倡的做人原則,與堯舜的“正大光明”之德、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柳宗元的“教孝弟,去奇邪”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才是“天下之達道也,圣人之事也”。事實也是如此,周敦頤一生為官清廉,盡心竭力,深得民心;為人光明磊落,正直無畏。周敦頤在南安任司理參軍時,有一獄囚法不當死,但轉運使王逵卻決意殺之,眾官雖覺不當,但都不敢出面講話,惟周敦頤據理力爭,王逵不聽,他便棄官而去,氣忿地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宋史·道學一》本傳)在他的感染下,王逵最終放棄了原來的意圖。這就是周敦頤為人做事“中通外直”的具體表現。“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周敦頤的設問,正是希望形成一種共有的人格秉性,以確立一種群體認同的文化特質。
物我交融的蓮花品質,既確立了周敦頤的理論價值,也確立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兼容儒道,既具有高度的“水之智”,也具有強烈的“山之仁”。“山”與“水”的共通作用,鑄就了周敦頤的“三圣”地位,為湘漓文化特質的豐富內涵提供了第一個典范。
周敦頤之后,歷史長河又流過了近千年,我們從當代湘漓人中可以找到第二個典范,那就是梁漱溟。
梁漱溟說自己一家人“兼有南北兩種氣質”,而這種氣質的具體表現他也有一個介紹:“吾父是一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他做學問沒有過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見長。他與我母親一樣天生心地忠厚,只是他用心周匝細密,又磨煉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較能干許多。他心思相當精明,但很少見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無疑,梁漱溟的父親是一位很平凡的人,但唯其平凡,更能體現湘漓人的人格秉性;更因在平凡的人生中有著不平凡的氣質,進而影響了梁漱溟,形成了他的偉岸人格。
梁漱溟被國外的學者論定為“最后的儒家”、“中國的脊梁”。他一生的奮斗目標是“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踐行的則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審美人生。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外來刺激,固可以無時而不樂”。梁漱溟無疑是有道之士,盡管一生坎坷,“波譎云詭,卻不改威武不屈的傲骨,剛直不阿,仗義執言,人格偉岸”。這正是蓮花品質的真實寫照,他不僅弘揚了周敦頤的思想和學術傳統,更是弘揚了周敦頤的人格秉性。
能體現湘漓文化特質的第三個典型應該是陶鑄。陶鑄推崇松樹,在他的散文《松樹的風格》中,作過這樣的描述和評價:“你看它不管是在懸崖的縫隙間也好,不管是在貧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種子,它就不擇地勢,不畏嚴寒酷熱,隨處茁壯地生長起來了。它既不需要誰來施肥,也不需要誰來灌溉。狂風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沒它,嚴寒凍不死它,干旱旱不壞它。它只是一味地無憂無慮地生長。松樹的生命力可謂強矣”;“要求于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這就是松樹的風格。魯迅先生說的‘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也正是松樹風格的寫照”。陶鑄為人做事,堅持“不惟上,不惟利;只惟實,只惟民”的原則,用自己一生的實踐,豐富了松樹風格的內涵。
作為松樹風格的踐行者,他“要求于人的甚少”。建國初期,干部工資標準定級時,他的工資關系本來一直在軍區,聽說部隊工資高于地方,便讓秘書把他的工資關系轉到地方,并對秘書說:“在個人待遇上,還是就低不就高好一些。沾公家的光多了,個人的光彩就少了。”他是這樣對待自己,也是這樣教育家人。1969 年9 月,他被打倒又病入膏肓,女兒陶斯亮從東北農村回來看他,他特意填了一首《滿江紅·贈斯亮》,教導女兒:“不為私情縈夢寐,只將貞志凌冰雪。羞曇花一現誤人歡,謹防跌!”
另一方面,作為松樹風格的踐行者,他又“不畏嚴寒酷熱”。陶鑄性格耿直,敢放炮。“文革”初被調到中央,成為政治局常委中的“四把手”、國務院副總理,集黨政軍實權于一身。這樣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向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開頭炮”。他卻回答江青說:“我的炮彈早就打光了,做人要講良心,不能落井下石。”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革命,促生產”上,幫助周恩來想方設法維持工廠、農村的正常生產。最終與江青等人發生激烈的沖突,成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最后孤獨寂寞地死在“緊急疏散”地合肥,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連名字也改成了“王河”。作為一顆政治明星,陶鑄的名字迅速地劃過夜空,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作為松樹風格的踐行者,他化為一棵傲然挺立的勁松,郁郁蔥蔥,蔭護后輩,激勵后輩,永不枯朽!
蓮花是水性植物,但“中通外直”,具有山之“仁”性;松樹是山性植物,但“隨處茁壯生長”,卻也具有水之“智”性。蓮花品質與松樹風格的結合,兼容山性與水性;再與湘漓人之人格秉性“情景合一”的人生實踐結為整體,或許這就是湘漓文化的基本特質。
〔注釋〕
①筆者對舜帝與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曾有過專文討論,見《舜歌<南風>與中國民本思想之源流——中國民本思想發展演變的三個節點》,《中國文學研究》2011 年第2 期,可參閱。
〔1〕錢穆.論語新解〔M〕.上海:三聯書店,2002.
〔2〕李錦全.儒家論人際關系的矛盾兩重性思想〔J〕.中州學刊,1987,(5).
〔3〕荊門市博物館編輯.郭店楚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楊東晨.帝舜家族史跡考辨〔J〕.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1).
〔5〕顧頡剛.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A〕.呂思勉、童書業·古史辨:第7 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晁福林.關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一個理論思考〔J〕.中國歷史研究,2010(6).
〔7〕蔡靖泉.舜歌《南風》與舜化南國〔J〕.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1).
〔8〕馬東王.梁漱溟傳〔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9〕王東林.梁漱溟問答錄〔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0〕(美)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M〕.王宗昱、冀建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1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A〕.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12〕潘琦主編.廣西文化符號·梁漱溟〔A〕.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4.
〔13〕黃承先.陶鑄的故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