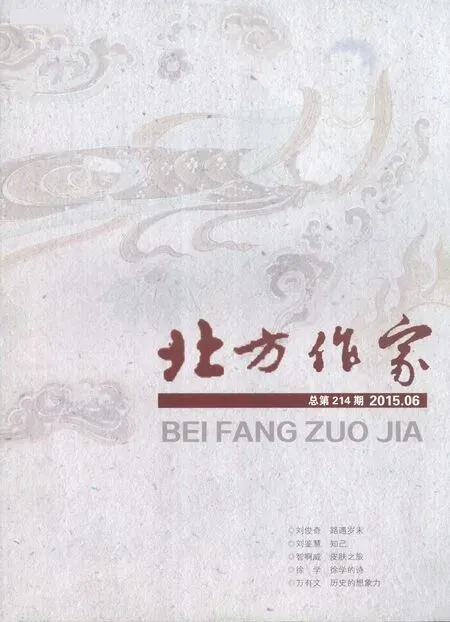父親的小耳朵母羊
甘肅甘州 曹國魂
父親的小耳朵母羊
甘肅甘州 曹國魂
院子很大,原計劃是四合院的。上房是父親的住居,兩個偏房,二哥站西,我站東。90年代末二哥搬了出去,進了城,西偏房閑置著。06年父親去世,我們搬進了上房,東西兩偏房徹底成了閑房子。前年夏天讓連襟在大門兩側搭了兩間彩鋼棚,堆放煤塊和停放車輛。空域的地方碼著喂牛的飼料。牛飼料里攙著香精,引來成群的麻雀和斑鳩偷吃飼料。
有了牛飼料里散發出的香氣,院子里總有一些鳥兒起起落落,這些鳥中無論嗅覺還是個頭,喜鵲是最最強最壯的。它們一旦瞅準,一只喜鵲會嘰嘰喳喳叫來一大群喜鵲共享。喜鵲常常從地上飛起來就落到了我的屋檐,我一再驚嚇它們,它們佯裝要飛起來的樣子,扇一扇翅膀而已,根本沒有想飛遠的意思。
喜鵲的叫聲往往會找來其他的鳥,亦或是后院的羊群。后院的羊群會用蹄子使勁拋腰門,咣咣作響,似是有人用拳頭用力捶,那樣的響脆。我的羊群中善于使用這伎倆羊,數那只小耳朵母羊。
父親是2006年冬天去世的。父親去世的時候留下的兩只母羊,父親在世時就說,路上有收羊皮的,叫來打個價,把那只小耳朵母羊賣了。
我盤問父親,小耳朵母羊老了嗎?
父親說,母羊倒是還能下崽,就是太奸了,養著也是惹禍的主。
當每次我領來回子的時候,父親又左右推辭,常因價格不適而食言,收羊皮的回民無論往上添多高的價格,父親還是不滿意。我知道,即便回民給小耳朵母羊一個牛的價格,父親也舍不得賣。
立夏過后,田埂上的冰草和芨芨草都長得很茂盛了,父親不是去急著割草,而是緩緩地把羊毛剪了,讓羊美美的在陽光下下睡上一下午,父親才才去割青草。父親割草很講究,把草里的苦豆和臭蓬勃白刺都撿出來,不讓羊吃。都說羊吃百草,父親每次割上一架子車青草已經汗流浹背了,汗水透過父親身上的汗衫泛著鹽漬,白花花的一圈一圈的,像是小耳朵母羊背上的幾坨花色。大中午的,父親喚我去往回來拉草。正午的陽光夠毒的,我有些不情愿的抱怨父親,早上不割,偏偏中午割。父親一邊收拾埂上割好的青草,一邊嘟囔著,誰不知道早上青草上有露水,羊吃起來牙酸,吃一會兒就不吃了,而且吃了就會引起胃脹,想要了羊的命吧。對父親的執拗我也懶得叫真,任憑牛虻瘋狂的往我短褲下面的小腿上猛烈攻擊,我拉著父親割來的青草,沒好聲氣接著我的讀書程序。而父親此時,把后院掃出一片干凈的地來,一小撮一小撮的把青草均勻的撒在魚肚皮一樣的地面上,打開羊舍的門,那群羊呼啦一下就把父親和柵門推搡到墻角,父親嗔怒的罵一句:這貨遭瘟的,挨刀的。父親知道,只有上了膘份的羊才有勁,才肯吃草。父親是在疼罵他的羊。
父親的羊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品種本土羊種,有清一色的白,也有黑白相間的,更甚者有幾只身上長紅毛的羊。但不知什么時候,父親的羊里出生了只耳朵很小的母羊。父親也記不清是誰的騷羊(公羊)配的種。夏天過去了,羊群積攢了一身的膘份,母羊開始發情。發情的母羊不明顯,只是一邊吃草一邊巡視四周,咀嚼草的空兒叫喚,父親開始收拾他的羊鞭和勾鐮。
秋天的莊稼,蕎麥澆了二水,正是開花灌漿期。棗樹上的棗子泛著綠色的光澤,略微有幾個紅眼圈,像是哭紅了眼睛的女人。秋分糜子寒露谷,糜子和谷子的頭抬的比走在羊群前面的小耳子母羊的還高,這時的莊稼對秋天不謙虛,不屈服的樣子。父親和莊子里的幾個同齡者一大早就趕著羊群出去,茫茫的戈壁,白花花的羊群吸納著秋天的晨曦,為防止羊群撒野,前面得有個領羊的,高高舉著羊鞭,恫嚇它們。走在最后的不是虧奶的小羊羔,就是剛剛下了羊娃子的母羊,拖著疲乏的蹄子有心無肝花的走著。
走著走著,一只羊突然竄出羊群,狠狠地在莊稼上采上一嘴。只聽得嗨的一聲,羊鞭實實落在羊背山,沉悶的一聲。秋天的羊長厚了毛,像是我們穿上了秋衣一樣,落在它們背上的鞭子根本不知道有多疼。記性很好的羊,過一會那只羊還是偷偷再去做一次。
那只羊就是父親的小耳子母羊。
小耳子母羊是那年冬天下的。我記得那是冬至的日子,半夜里后院的狗不停的嚎啕,傳來鐵鏈子急速的拉扯聲。父親一骨碌從炕上爬起來,說是羊下羔了。那是一只年邁的老母羊下的,很順產,父親說,就是耳朵有些小。的確,那只母羊羔子的耳朵格外比其它羊的小多了,不細看還以為沒有長耳朵。耳朵如同兩只湯匙扣在羔羊的額角上的,藏在毛叢里。
一年的光景小耳朵母羊都發育成一只傲立群羊的母系統治者了。它憑著耳朵小聽力強的優勢,帶領羊群呼啦啦一陣子朝西,呼啦啦一下子向東,整個后院不得安生。而且,我們一說話它就叫喚起來。惹得其他羊也跟著咩咩地叫喚。父親每次進后院都要手里攥一條木棍,迎上前的小耳朵母羊看見父親高高舉的木棍撒腿就往后跑。碩大的尾巴摔得老高老高,一對羊奶子搖搖晃晃錯落有致的擠在它的兩條長腿當中。
父親說,這挨刀的有羊娃子了。
下了羊娃子的小耳朵母羊比以前溫順了許多,它時常依偎在羔羊的身邊,舔舐著羔羊的身子,羔羊雙膝下跪使勁頂著它的乳房,它閉著眼睛嘴里反芻著,嘴角流露出白白的泡沫,帶著青草味。吃奶的羔羊搖著尾巴,小耳朵母羊咩咩地嗅著羔羊的后身,辨別氣味的同時像是在溺愛著這只幸福的羔羊。
第二年春天,父親說,今年你舅舅閑著沒事攆著一群羊放,十只羊是放,一百只也是放,不行把咱家里的那幾只羊代給你舅舅放去。
舅舅第二天來看我們家的羊群,臨走時對父親說,姐夫,要不我明天把羊群趕過來在你們附近放,把你家的羊攆到我羊群里來吧。
舅舅家有騷羊,我們羊群在舅舅家的幾個年頭了,父親也沒過問過繁殖了多少只。羊毛舅舅剪了算是放羊的工價,舅舅同意不同意都在潛意識里相抵了。舅舅每年春節來一次,上正月別的不談,就說我們家的羊又添了幾只羔子,幾只公的,幾只母的。那只小耳朵母羊好胚子,就是一下一個母羊。
父親有心無心聽著。
父親起初給舅舅代養并不是圖繁殖,而是不要把羊群斷了。家鄉有習慣,凡是家里有老年人的都得年年準備下一只大羯羊(閹了的公羊)。老人死了第二天晚上請上道士誦經超度,要在紙籠下哭紙。哭紙時后輩們圍著紙籠轉圈,最后將大羯羊拉過來,事先和收羊皮的回民說好皮子價格。主喪者先要用清水將羊的臉洗凈,在羊頭上焚燒一疊黃表紙,把這只大羯羊當成亡靈給回報所有哭紙的人,在地上下跪的都是誰誰誰,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外甥女婿親戚友朋的。此時,如果羊循環四周一圈,抖抖身上的皮毛,算是“領”了,意思就是亡靈應驗,魂已附體,同意哭紙。如果羯羊不抖擻身子,主喪者舀來一盆冷水,剝開羊身上的毛順勢將冷水淋進去,羊禁不住打個寒顫就會全身抖擻。有時候招數使盡大羯羊也不抖身子。主喪者給羊回報哪個兒子或是孫子因路途遙遠,趕在入土之前就會到來,云云。有時就怪,羯羊竟然會哆嗦一陣子,全身抖擻。緊接著,主喪者開始宣布,哭紙開始。
就這樣,一只大羯羊成了亡靈的化身,后成了殉葬品。它的肉第二天用來招呼送葬的親戚友朋,羊皮被回民捶打后卷起來帶走。
父親的身子一年不如一年,尤其兩眼,畏光。當了一輩子農民,養了一輩子羊,父親常說,頭下無論無何都得個領頭的羯羊,不然到時候哪兒找只大羯羊呢。
因為羊在舅舅家一直沒有繁殖下大羯羊,父親把羊群從舅舅家趕了回來,閑著沒事父親就趕著羊群和莊子上其他放羊佬到村莊南面的戈壁灘上。那里有蓬蒿、駱駝刺、沙蔥、荊棘等沙漠植物,雨水多的時候它們很茂盛。偶爾父親還會帶來一團頭發菜,能買幾包水煙。
那年冬天,舅舅因和一個精神病發生口角,不幸被精神病人用亂棍打死,哭紙的那個晚上,我分明看見領頭的大羯羊長著一對很小很小的耳朵。我把這事說給父親,父親微微一笑,你舅舅一輩子了是個啥人我比你清楚,不要人面前再提及這事。
嗯,我答應了父親。
曹國魂
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高中文化程度,迄今在《星星詩刊》《飛天》《散文選刊》《散文世界》《西部作家》等雜志報刊發表詩歌散文小說若干,系甘肅省作協會員,文學雜志《黑河水》小說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