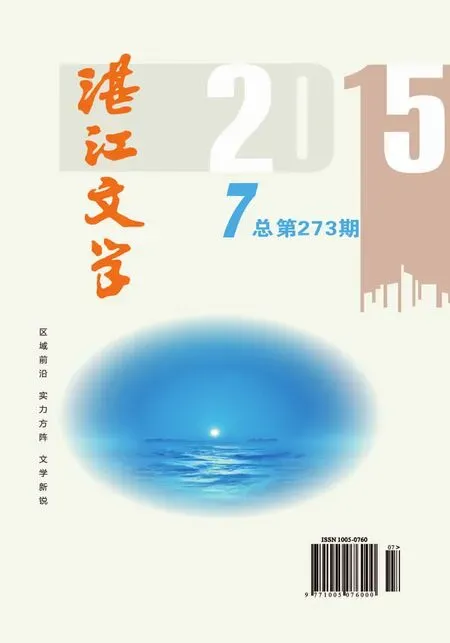鄉土情懷·詩意民俗
——讀組詩《村莊在天空下游蕩》
※ 余 墨
我相信很多人心底里都有著一份鄉土情懷,即使他們沒有在鄉下生活過,但也會在某個時候想起祖輩、父輩的鄉下,想起家族的根在哪里。在湛江,雷州人算得上是鄉土情懷最厚重的一群。他們對自己鄉下的歷史、文化、風物乃至一簞食一瓢飲都津津樂道眉飛色舞,只差說“世界都是雷州市大”。陳通是雷州人,在湛江市區生活了30多年,他那份鄉土情懷至今還和他的老鄉們一樣深厚。這,有詩為證——《村莊在天空下游蕩》組詩。
陳通這組詩打動我,首先就是其中的鄉土情懷。從《村莊在天空下游蕩》里,我體驗著“村莊像黑山羊一樣/在山坡上游蕩/山鷹在天空滑翔/聽到種子發芽的聲音”,但是,“山羊,山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這只“黑山羊”有點詭異,卻是他懷鄉的憂郁。“花溪,屬于一條女性河流/日夜用柔情與男人纏綿”——在《花溪流過花橋》中,故鄉是一幅畫,小橋小溪、荷花池塘,“橋下瀲滟波光/映出童年時光”和“天天流過父老肩膀”的溪水,互相映襯,能讓人品味到鄉村生活純天然不含“添加劑”的質樸。這兩首詩,一首是憂思閑愁,一首是真情實意,卻都有著相同的意旨。但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儺舞穿越稻田》和《元月十四的令箭》,原因是詩中有數千年沉淀的民俗。詩和儺舞,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需要專家們去研究。東漢時的大學問家何休說:“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和儺舞應該是一母所生的雙胞胎。盡管在今天看來儺舞帶有迷信色彩,但這是一種有數千年歷史的民俗,何況農耕文化本身就是靠天吃飯文化。黑格爾說,存在即合理。我們也應合理地看待儺舞。我之前雖然多次看過湛江的儺舞,但只有陳通這兩首詩才讓我看到了詩意的民俗。《儺舞穿越稻田》以“陽光嗶剝作響/田野貫穿金黃”起句,時而是猙獰時而是溫柔的面具、掉進深井的古巷、夜色和考兵、指若蘭花和五雷巨響……一個接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形象疊加,使我有點喘不過氣的感覺,直到結句“每場雨,終歸令朽木/長出新鮮的木耳”,我才長舒一口氣——嗨!沒事了。異曲同工的《元月十四的令箭》,“一隊虎賁深夜悄悄集結/衣衫不整,腳上有泥/小腿鍍著銹色/疑似青銅的顏色……他們或從商代跋涉而來/務必在拂曉前到達”,這樣的句子能把人牽引到雷州鄉下,進入春耕前的祭祀儀式氛圍中,雖然我也搞不明白為什么“元月十四的行軍路線/是世代相傳的最高機密”。世上有很多事其實無須都弄得一清二楚,只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就“是知也”啦。尊重民俗這種古老文化,從中悟到說得清或說不清的感受,即是“道可道,非常道”。
陳通詩寫得好,但產量很少,弄得我每次讀到他的詩都像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生怕碟子里的茴香豆被人搶了去。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換成大白話,是詩可以抒寫個人情致、觀察社會、交朋結友,還可以發發牢騷。興、觀、群、怨加上高明的藝術技巧,那就更讓人印象深刻。這組《村莊在天空下游蕩》,有的詩句不夠凝煉,虛的東西稍多,全詩的感染力也因此減弱。不過,古今寫詩煉字入魔的人不太多,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一個,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也上了榜。現代有幾人做得到?所以不能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