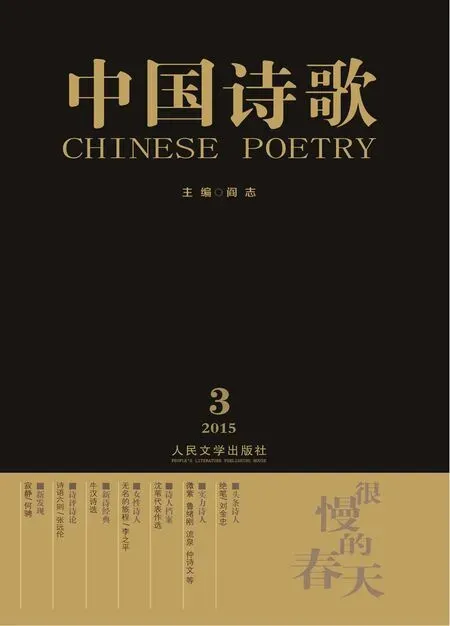詩學觀點
2015-11-15 00:33:15韓玉
中國詩歌 2015年3期
□韓玉/輯
詩學觀點
□韓玉/輯
●張德明
認為新世紀以來,圍繞中國地理而生發的詩意言說和藝術詮釋,已然構成了中國新詩中極為重要的審美景觀。地理是一種集自然景觀和人文風貌于一體的特定空間,地理詩意的彰顯,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空間美學的建構。不管是對現實空間的描摹,還是對歷史空間的述說,以及對想象空間的構筑,詩人都必須將詩意的呈現放在首要的位置,努力用富于藝術性的筆法將這些空間精彩地打開,神奇地照亮。通過對這些地理的藝術闡發和詩性彰顯,中國新詩的空間美學,才可能會被逐步構建起來。(《新詩空間美學的構建——讀〈云朵打開遠游的翅膀〉
》,《星星
》,2014年11月上旬刊)●楊亮
認為“交流詩學”實際上是女性主義詩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敘事性詩學實踐中的一種性別化特殊表達,它一方面指性別意識的轉變,兩性關系由對抗走向對話;一方面也標志著女性主義詩歌詩學觀念走上了“敘事性”綜合創造的演化階段。“交流詩學”的形成,在豐富了藝術表現手法之余,也拓展了女性主義詩歌的藝術疆域,提升了其精神氣度,使其從狹隘的二元對立性別立場中走出,具有普泛性色彩的人類經驗重新回到女性主義詩人的文學思考范疇中,女性主義詩歌也由感性沖動回歸至理性的詩體建構。“交流詩學”的形成標志著女性主義詩歌的成熟。(《性別視域下的“交流詩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性別化敘事詩學思維的形成
》,《文藝評論
》,2014年第11期)●解非
認為左岸先生的詩歌以人為本,以情為本,品讀他的詩作總會被他的情緒所感染,被他的真情所感動,也總是會從他流暢而舒緩的詩句中體會到詩歌的美學品格和詩人的人格魅力。一個詩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賦予作品一種不平凡的使命,使詩歌具有精、氣、神,這是非常不易的,也是神圣的。他的詩歌就像他的人一樣,默默地書寫著對人生、對親人、對愛情、對朋友的誠摯善良的情懷,將情感的根深深地扎在北方廣袤的大地深處,在風中恣意地展示著一個北方漢子的豁達與滄桑。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也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更是一個撫琴而歌的獨行者。(《左岸詩歌以及評論
》,《詩選刊
》,2014年第11-12期)●趙四
認為詩怎么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對抗的產物,這是使詩維持住自己內部張力的最簡單便捷也始終是最有效的方式。曾經是意識形態的壓抑,使詩的主導聲音是反意識形態的。如今是混亂的塵囂噪音,各種各樣的,商業的、低俗媚世的、隱蔽意識形態的、只為表現表演欲的……所以與之對抗的是擁抱梵音的理想。即便人類從來沒有產生過完美的梵音,但也一直懷抱著對這聲音的夢想。詩,當今的詩,尤當去建設這個聲音,一種巨大的靜音效果的聲音。(《尋找一種個人聲音詩學的可能性及其他
》,《作家
》,2014年第11期)●張遠倫
認為鄉村文明式微,曾一度讓詩人哀嘆,而隨著城市化的快速前進,詩人們嘗到了這種革命性元素的甜頭。這種革命性,帶來的是破壞力和建構力。在強大的破壞力里,詩人獲得了不一樣的詩歌寫作資源。那些冥想與追憶、撕裂與疼痛、命運的提前和重置、生活的速度和重量,都讓詩歌產生了越來越寬的可能。詩人面對鋼鐵的冰涼產生的抵制,恰好讓詩歌具有強力摩擦的熱度,而詩人用迷醉、頹傷、游戲、逸樂等詞語對現實進行順應的時候,恰好讓詩歌復制了《詩經》般野性和放大的唯美。詩歌再一次拯救了和復蘇了故鄉,故鄉是古老地存在著的,正因為古老,故鄉才具備詩意的恒遠。(《鄉村文明的式微與古老的還鄉
》,《紅巖
》,2014年第6期)●畢光明
認為詩性是一種思維方式,它保留著人類對世界的初始經驗,結合了心靈與精氣,以強旺的感受力與生動的想象力,創造出主客渾融的感性世界。在這一感性世界里,寄寓了人類的生存的根本訴求,因而作為思維方式的詩性對人來說具有本體意義。詩人用它具有原始性的思維創造了充滿動感和交互性而又秩序化的意象世界,囚禁于肉身的躁動的靈魂,惟有在這個世界里才得以休憩。詩歌不僅自度還能度人,詩人儼然超拔俗世成為指點迷津的靈魂牧師,這也是所有現實中人需要詩歌和社會需要詩人的理由。(《留住詩性的根——評揚茲舉詩集〈盛裝的音符〉
》,《創作與評論
》,2014年11月下半月刊)●耿紀永、張潔
認為長期致力于英美現代派詩歌翻譯和研究的袁可嘉,在對葉芝的譯介中通過對譯詩的選擇、闡釋以及具體的翻譯策略對葉芝加以改造,體現出他所構建的“中國式現代主義”的詩學觀念對葉芝翻譯的操縱。在譯詩選擇方面他更青睞葉芝轉型為現代派后所寫的詩;在譯詩闡釋中批判葉芝的“貴族主義”,對其詩中的神秘主義采取回避的策略,并試圖通過強調與突出等翻譯策略來強化葉芝詩歌的“現代主義”藝術手法。袁可嘉的“中國式現代主義”的首要目的就是“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定性,它就不可能發展為西方式的現代主義,而只能是中國式的現代主義。(《詩學觀念與翻譯操縱:袁可嘉的“中國式現代主義”與葉芝譯介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
》,2014年第3期)●謝海長
認為華茲華斯通常被認為具有“反科學”傾向,然而對華茲華斯作品做了整體細讀后卻發現,他對科技發展及運用現狀的評價是辯證的:既頌揚蒸汽輪船和鐵路等科技成就,又揭露科技濫用所引發的有害后果;既崇尚有助心靈提升的“大寫科學”,又貶斥僅應用于物質性生活的“小寫科學”。華茲華斯認為詩人既要像科學家一樣奮發有為,又要貢獻“神圣精神”去援助物質性或工具性科學,實現其“穿上血肉豐滿的衣裝”的“形變”,讓詩與科學共生共榮、協同造福人類。(《論華茲華斯的詩與科學共生思想
》,《外國文學評論
》,2014年第4期)●張少揚
認為圣童在《形而上本體詩學》一書中所提出的“客觀詩本體”的概念,從全新的角度將“詩學”重歸純粹哲學領域,打破了“詩學”只是一門涉及詩歌寫作技藝理論的學科的一般性觀念。在圣童的界定中,人的主體意識不再是“詩學”的研究對象,“詩學”所研究的當是隱于詩人詩歌作品背后的存在問題——而這一客觀世界的存在具有徹底自在和完全自為的屬性。“客觀詩本體”指涉的是人的“靈魂”的“善”的“屬性”,這直接關乎了人類整體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關乎人當如何看待世界,看待生存的價值、生存的意義——一言以蔽之,人當怎樣生活的問題。(《客觀詩本體:一種新的詩學理論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李亞偉
認為詩歌的閱讀和認可從來都有滯后的特性,人們只讀前朝詩歌,只了解和認可定性了的前朝詩歌。不管你多聰明,你只要不是當朝詩歌中的作者,你就只是一個普通大眾,你對詩歌的了解比普通大眾的程度高不了哪兒去,你最多只能讀懂部分當代詩歌。通常的情況下,最先進的文化需要一段小小的時間與生活磨合才能引領生活,最前衛的詩歌、藝術也需要一段小小的時間對社會審美挑釁才能被審美。(《詩歌是世上最珍貴的東西——關于當代詩歌的評價及詩人的身份問題
》,《揚子江
》,2014年第6期)●辛笛
認為大陸要重新談論現代派,重新學習現代派,其實是一個螺旋上升的狀態,二者一方面不可割斷,另一方面又不能重演。在時間、空間、條件都不一樣的情況下,談論現代派就是要把現代派的優點吸收到現實主義的傳統中,吸收西方的好的方法。同時,詩歌創作還應該做到兼收并蓄,各方面的詩的風格,都應該能夠讓它繁榮起來,只要我們寫得好,就可以存在,作品多起來,好的作品就會來了,要“多”中求“好”。(《論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詩——1981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
》,《現代中文學刊
》,2014年第6期)●利兵
認為安妮·塞克斯頓的創作生涯一開始就與她的心理疾病不可分割,詩與治療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某種神秘的聯系。詩人需要這種私密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在現實中失落的生活的希望,從詩歌中重新找回。詩歌和治療一樣給無意識提供了話語方式,給詩人封閉的自我提供了一條交流和傾訴的渠道。此外,寫詩不僅是詩人內心治療的需求,而且反映了社會環境對精神世界的扭曲,詩歌在反思個人的同時也在反思時代。詩人這一職業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它能啟發讀者,救贖心靈。(《安妮
·塞克斯頓與詩歌治療
》,《外國文學動態
》,2014年第6期)●沈奇
認為一個時代之詩與思的歸旨及功用,不在于其能量即“勢”的大小,而在于其方向即“道”的通合。現代漢語語境下的百年中國之詩與思,是一次對漢語詩性本質一再偏離的運動過程。如何在急功近利的“西學東漸”百年偏離之后,重新認領漢字文化之詩意運思與詩性底蘊,并予以現代重構,是我們首先需要直面應對的大命題。當前,現代漢語之詩與思,在歷經百年的“與時俱進”后,已然深陷中西“夾生形態”(張志揚語)之矛盾處境,其“矛”也“西”焉,其“盾”也“西”焉,短期內很難自外于“他者”而獨樹于世界。(《“味其道”與“理其道”——中西詩與思比較片談
》,《文藝爭鳴
》,2014年11月號)●白連春
認為文學和世界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如果有人把文學和世界對立起來,硬要理清文學和世界究竟是什么關系,這便是一個錯的命題。實質上,文學與世界沒有關系,因為所有文學都是世界,因為全部世界都是文學。文學就是反映世界的。文學即世界本身。世界是白的,文學就是白的;世界是黑的,文學就是黑的;世界是和平的,文學就是和平的;世界是幸福的,文學就是幸福的。不論別人的創作與世界的關系如何,白連春認為自己的文學就等于他的世界。(《盡可能地還原生活的真實——與白連春對話
》,《莽原
》,2014年第6期)●馬永波
認為當代詩歌充斥著對個人化小情感的描述,這樣的詩歌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中只看到了詩人在溫室中自嘆身世的“私心”,詩歌缺乏了大的現實關懷和人類永恒的主題。詩人多習慣將以往的“邏各斯”分散在日常生活的點滴細節之中,在碎片中透露出若干生存信息。這么做,固然有讓詩歌卸下過重的意識形態負擔的好處,能讓詩人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生活中的經驗與體驗,但同時也帶來了詩歌瑣碎化和私己化的傾向。因此,倡導健康向上的精神高度與經驗深度的整體性寫作的難度寫作就顯得尤為重要。(《對難度寫作的再倡導
》,《詩林
》,2014年第6期)●李犁
認為經過百年的發展變化,中國新詩已經確立了自己獨立且耀目的詩學傳統。但是活躍和喜新厭舊的品性一直讓新詩處在前沿和動蕩之中,速變與速朽是新詩的特征,也是技術更新的動力。新詩在進化的同時,也在變異。過分的“詩言志”加上對世俗趣味的沉迷讓詩歌中的志向及理想越來越淡化,審丑在流行,低迷低俗以及茍且猶如詩歌中的陰霾在彌漫。詩歌需要熱愛和溫暖,需要氣度、高度和溫度。忌功利和世俗,堅守寂靜和狹義,是詩人原本就應有的品質。(《百年新詩需要堅守些什么
》,《詩刊
》,2014年11月上半月刊)●黃燦然
認為詩人應當接氣和安氣。接氣就是指一個詩人先要奮發,無論是出于抱負、野心、虛榮,還是別的,總之要精進,包括技藝的精進,要使自己的母語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這不應是由別人判斷,那會變成追名逐利,而應由自己來判斷。這個氣最初不是它來了你接,而是你努力讓自己夠得著它。這一步相當于建立自信。自信建立后便應是安氣,不斷接近自己心靈最內核的東西,這個時候要把接氣過程中的雜質全部清除。也就是說,要揚棄。總之,氣即是我們天性中的自然、清白、純潔、天真甚至幼稚、愚笨。(《黃燦然訪談:枯燥使靈魂長智慧和善良
》,《詩歌月刊
》,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