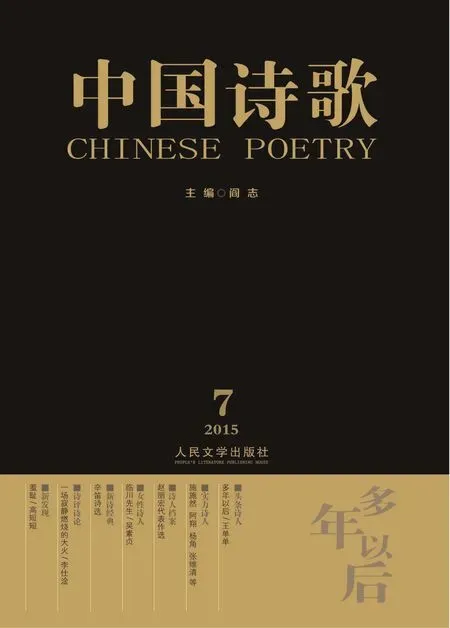一場寂靜燃燒的大火
——我讀靈焚和《靈焚的散文詩》
李仕淦
一場寂靜燃燒的大火
——我讀靈焚和《靈焚的散文詩》
李仕淦
靈焚,本名林美茂。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創作伊始,直至現在,林美茂給他所有的散文詩作品烙上“靈焚”這個惟一的統一命名標識。靈焚,顯然就是靈魂燃燒的意思,無論是林美茂的無意識流露還是有意識揭示,這場大火已經寂靜燃燒了二十多年時間。
這場大火,仍在繼續。這樣一場大火,我無法進入,我只能面對,甚至面對,也必須接受被火光灼傷的危險的挑戰……
一、火光中的駱駝和馬
火源也許起于一根骨頭的斷裂,或者是一滴血的飛濺,火焰的舌頭在夜晚吞吐著月亮之水四處舔吮伸縮,而在白晝裹挾著變形的太陽熊熊蔓延。火光中,我看見一匹駱駝和一匹馬:沙漠中緩慢前行的駱駝,沙漠之舟,負重之王。馬,有時是黑色,黑色的閃電,黑夜精靈;有時是栗色,比火焰更深,它就是火本身,火的種子;而有時是白色,雪域之上炫亮之光,降自天堂之雪,神秘天使,擁有一雙飛翔的翅膀。
透過火光,我還看見了駱駝和馬的眼睛和表情:溫馴、善良、謙恭、堅韌,深情、智慧、悲壯、超絕……這些詞匯構成這兩個意象的基本品質和特征。當然,這些還遠遠不夠,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駱駝”是現實生存的靈焚(即林美茂)的象征,那么,“馬”就是靈焚的精神存在,就是夢和詩歌。
1962年,林美茂出生于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故鄉坐落在福建沿海一塊鳥不撒糞的鹽堿灘上。在他成長的那個年代,貧窮不是勤勞可以改變的,而更為不幸的是,林美茂童年喪母、少年喪父,活著,成為他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個難題。年少不知愁滋味,林美茂在祖母的粗糧野菜喂養和倔強偏執的呵護中度過灰暗的童年和少年。在這一段灰暗的時光里,除了母親重病痛苦恐懼的呻吟和一顆因腥味而無法下咽的西紅柿之外,林美茂找不到更多的記憶,而一生沉默的父親臨終也只留給他沉默。
生活的磨難過早地降臨林美茂身上,另一種迷蒙的愿望就本能地在林美茂心中產生并隨著青春期的到來而愈發強烈:離開,甚至逃離。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改變自己,改變一切。當他意識到這一點,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的心和腳下的土地都隱隱地顫動了一下:“生活在別處”,生活本身告訴了林美茂,林美茂卻仿佛聽見一種來自深遠的召喚。
林美茂一邊種地養活年邁祖母、幼小弟弟,一邊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讀完中學。或許是命運的垂顧,抑或是命運的進一步捉弄,林美茂幾乎是在忍饑挨凍、同學們的救助中度過了兩年師專的大學生活(因為他必須掰下生活費的一半供弟弟上學,只好經常接受班上女同學們飯票的同情),而后被分配到福建山區的一家大型工廠工作。
在工廠期間,他開始創作,以散文詩的形式,其間發生了一場改變和影響了他整個人生和未來的愛情變故,原因就是他的過分貧窮。而后,林美茂再次“離開”(或者“逃離”),出國去日本。如果第一次接受畢業分配,是出于改變生活環境的一種潛意識的迷蒙愿望,那么這一次,與其說是現實生存的別無選擇,毋寧說是精神存在之于內心深處的一種對現實存在更為強烈的叛逆和自我放逐。出國潮只是形式,“生活在別處”的召喚才是本質,而直接促成的最大動因可能就是他的失戀。
貧窮、苦難,甚至悲劇,只有意識到時才真正存在。失去母愛,林美茂還來不及感受和體驗就成為一種先天的缺失,而兩心相悅戀人的突然背身離去,一場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毀滅性愛情把林美茂徹底推向天崩地裂的黑暗深淵:貧窮和苦難不算什么,深愛少女的變臉、愛的純潔性被一種世俗的偏見所玷污,而自己對這一切的抵抗卻是如此地蒼白、孱弱、乏力,林美茂幾乎絕望了。“生存還是死亡”,達摩克利斯之劍第一次懸在頭頂,黑暗深淵的浮沉中,林美茂抓著的惟一的一根稻草就是文學,就是散文詩創作。
不知誰說過,一個人一生前二十年的經歷基本決定了他人生的內容和本質,此后只是觀察和思考。1989年林美茂只身東渡,在異國他鄉的生存境遇,尤其是飽含屈辱辛酸血淚的心靈歷程,在他選入本書的一部分完成于日本的詩作,如《1990年東京情緒》、《語無倫次,或者病人日記》,和第三部分《詩外隨筆》(都帶有自傳的性質)的文字中,有著鮮活的記錄、深切的述說和深刻的思索。
然而,其中有兩個情景至今想起仍令我戰栗:去國臨出發前的夜里,林美茂給朋友們寫下一封幾近絕筆的信,他覺得朋友借錢給他出國是在他身上下賭注,如果找不到出路寧可出售器官也要對得起這份信任,信的最后一句話是“難酬蹈海亦英雄”。還有一個情景發生于在日本玩命打工一年多之后的某個黃昏。林美茂滿懷期待希望聽到友人能夠對他寄出的新作予以評價,當公用電話機瘋狂地吞掉一大把他用血汗換來的硬幣時,他失望了,朋友們不寫作了,也沒有興趣看他的作品。打完電話,蹲在公共電話亭邊,他感到自己被雷擊、被掏空、被淹沒、被吞噬,在東京街頭的暮色中,面對空曠蒼茫的黃昏揮淚不止。
那是怎樣的一個夜晚和怎樣的一個黃昏?十余年天涯飄泊歲月里究竟有多少個那樣的夜晚和黃昏?孤獨者悲傷的形象在異國他鄉浮動漂移的地平線上掙扎、搏斗、傾斜、倒下、漸漸沉淪的景象如劃破撕裂天空的閃電一次次擊中我的太陽穴。
“去國一夜數十載”,林美茂以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與意志,從過語言關開始歷經十一年讀完博士,終于2003年回國。如今他已經在講臺上站了五年,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有日本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愛知大學客座研究員等頭銜。他的十多年前出版的散文詩集《情人》,在2007年獲得了由中國現代文學館、《文藝報》、中外散文詩學會、河南文藝出版社聯合頒發的“紀念中國散文詩90年優秀作品集獎”。
背井離鄉又返回故土,林美茂的生存經歷是一個奇跡,更是一個怪圈。“生活在別處”卻總在渴望家園的回歸。我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是否又要“離開,或逃離”。我看到的是,寂靜燃燒的一場大火至今絲毫沒有熄滅的可能。火光中的駱駝,依然緩慢行進于沒有盡頭的沙漠,仿佛出現了零星稀疏的齒狀綠色植物,綠洲顯然還在遠方,那匹馬,翅膀生長得似乎已更為強壯有力,而飛翔的意志則更為堅定、自由的夢想更為遼闊。
二、現實生存苦難經驗之上的孤獨痛苦
現實苦難太深太重,林美茂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任何途徑解決,他除了自己,一無所有,他除了把自己交出別無選擇。于是他選擇了火,渴望焚燒自己而期望照亮現實生存的黑暗,所以,駱駝以“靈焚”為那匹馬命名。
當然,使靈焚徹底陷入黑暗的原因,不會只是現實生存的苦難和一場沒有防備的愛情變故這么簡單。“世界午夜”時間的到來,更確切地說,靈焚的“個人午夜時間”與“世界午夜時間”在二十世紀末的某一瞬間正好重合了,由此引發的巨大爆炸的沖擊波把靈焚推向了遠離光源中心的黑暗,并將越來越遠地墜入深淵。其實,這一世紀末的災難,不惟是針對靈焚一個人的,它是針對所有人的。問題的關鍵是,遭遇這場災難的時候做出怎樣的反應。
驚慌、恐懼、吶喊、呼救,喧嘩騷動、絕望沉默,醉生夢死、麻木不仁,或固守或突圍,或逃亡或流浪,或抗衡或反擊……。當現實生存苦難的經驗喚醒生命沉睡的理性思想,即當靈焚清醒地意識到生命于黑暗中的苦難遭遇是命定之必然,而其全部涵義只在于對“情人”——此一終極存在——的不可企及的追求時,靈焚擰著自己的頭顱和血淋淋的心孤獨上路:從《飄移》(1986/9/30—10/1)、《房子》(1986/12—1987/1)到《異鄉人》(1987/1/6)、《情人》(1987/3/6),靈焚突圍、逃亡,把自己拋向世界午夜的箭雨刀雪,偶像黃昏之后的、彌漫四月死亡氣息的荒原;靈焚抗衡、反擊,穿越破碎不堪的世界廢墟,直抵自己和整個人類的心靈極地,用骨頭吶喊,用血和嘴唇歌唱。
…………
以手加額,霜雪從心底漫卷而至。額上佝僂著無數男人和女人圣潔的肉體在呻吟。那個富足的股票經紀人餓死在神秘的塔希提島上,呼喚世界始終沒有回聲,晝夜成為一個空前絕后的謎。
就這樣閉著眼睛飄移!管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
——《飄移》
…………
血的吼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凄厲割著神秘的面頰禱告吶喊絮絮潺潺聲嘶力竭撕心裂肺——
啊啊!毛孔開裂的深淵無涯
呀嘻嘻嗬嗬嗬嗦嗦嗦——噼啪——!咔嚓咔嚓——嘩——咯吱咯吱——喂——嗷——嘎——啾啾啾!啾——嘿嘿嘿
天籟啊!
背——過——臉——去。
——《房子》
…………
我們需要一艘船,你的態度很堅決。
我們不是圍成一圈了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漸漸靠攏漸漸靠攏漸漸靠攏最后。
距離是一堆密不透風的石頭。
——《異鄉人》
我們認識的那一天就衰老了。我的臉頰深深下切,你隔著河床,眼角游動的一群追逐我浮萍一樣的老人斑。
這個時候,我說什么都是錯的,只好任你把自己撕得粉碎。
…………
——《情人》
靈焚在這些詩作中所呈現的黑暗、荒誕、撕裂、異化的現代人類生存圖景觸目驚心,而他力竭聲嘶、嗚咽欲絕、無淚失語的吶喊則令人靈魂戰栗,這只有一種來源:一口深深掘進黑暗核心的井,即生命的孤獨痛苦。現實生存的苦難經歷沉淀為孤獨痛苦的經驗,照見這一孤獨痛苦經驗的思想則進一步加劇了生命的孤獨痛苦,而被詩歌點燃的、巖漿一樣的激情使靈焚徹底燃燒。
這種孤獨痛苦是如此的具體、實在、親近,又是如此的虛幻、深遠、彌漫無邊。
靈焚的現實生存苦難是雙重的。物質生存在底線上的掙扎與生俱來,且從未曾有過停歇。貧窮,仿佛由生養他的那一塊土地所給予,又像影子一樣跟隨著他浪跡天涯。如果僅僅只是物質生存的困境,靈焚用他的血汗足以改變,問題是他不可能只停留于滿足物質生存的需求,他的夢想,“生活在別處”的夢想召喚他,牽引著他,他相信生存不是已然和命定的一種狀態,它一定有理想的可能。因此,可以說個人的貧窮苦難經歷在曲折漫長的歲月里早已幻化為土地貧窮的痛苦經驗,也可以說靈焚從一開始就無意識地走向了探尋此一“理想可能”之路,而后堅定不移。這一境況注定了靈焚要為他的夢想付出不僅僅是物質生存貧困的慘重代價,從而形成靈焚現實生存的第一重苦難:現實與理想對抗的不可平衡。
靈焚的第二重苦難,源于母愛的先天性缺失和青春愛情的過于短暫,也就是伴隨剪斷臍帶與嘗下禁果而帶來的對生命孤獨痛苦的覺察與清醒;它真正形成,則是一個時代變革動蕩裹挾而來的物欲泛濫對心靈精神的災難性洗劫(此一劫難無疑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性泛濫潮流的演進,加劇了世界后工業社會人類悲劇性生存的氛圍)。夢想的靈焚,甚至愿意放棄現實的物質生活而渴望換取一種“理想可能”的精神存在,然而他卻生不逢時,恰恰遭遇了技術至上與拜金主義時代,為物質性存在之精神匱乏所深深困擾,靈焚難以逃脫物質與精神存在的劇烈對抗。
現實生存的雙重苦難只構成靈焚生命孤獨痛苦的一個層面,還有一個層面,那就是始終困擾著他的虛幻、深遠、彌漫無邊的生命清醒,即靈焚在深刻意識到“要以全部的生命力量面對理性的清醒”時,抗衡與反擊刻骨銘心的“理性傷害”,依然只能抉擇詩歌。他以詩歌為刀盾,憤怒吶喊著突圍黑暗,一邊尼采式地宣言偶像的黃昏,自我個體的存在,一邊堂·吉訶德式地向現實世界瘋狂反擊,寧可粉身碎骨;他以詩歌為馬,并生長出翅膀,在逃亡、流浪中憧憬著自然風光的田園牧歌和個體生命的自由、幸福,血與火燃燒,渴望照亮世界午夜彌漫延伸的黑暗前景;他在詩中急速地飛翔,從自我個體生命的心靈雪峰切進人類心靈極地,寧可肉體成為灰燼而企望靈魂獲得升騰。靈焚相信詩歌,也只有詩歌可以拯救自己、拯救世界,可以重建宇宙秩序,可以返回家園。
然而,應該承認,人類不可承受之一切,詩歌難以擔當,人類所企望之一切,詩歌亦難以實現,更何況靈焚奔跑著竄進詩歌園地的時間是中國詩歌遭遇有史以來最大寒流的季節。當靈焚在突圍、反擊中頭破血流、傷痕累累之時,在飛翔的翅膀一次又一次折斷之后,他不得不接受令他心碎、悲壯而殘酷的現實——詩歌烏托邦的徹底破滅。如果來自詩歌外部的現實生存的雙重苦難是靈焚的生命之重,那么,來自詩歌內部的、在思想層次上的詩歌“可能性”的先天缺失與后天缺損所帶來的深刻的憂患、悲劇意識,就是靈焚的生命之輕,這一重、一輕,構成了靈焚生命孤獨痛苦的整體、全部。
靈焚的存在實際上就是現實/理想與物質/精神的對抗性存在,他的全部詩歌淋漓盡致地呈現了這一對抗性存在,生命的孤獨痛苦成為詩歌凸顯的主題,貫穿創作的整個過程。選擇詩歌來表現生命的孤獨痛苦,這是對所有曾經經歷的苦難的一再反芻、咀嚼,一次次揭開傷痕任憑鮮血淋漓,心靈搏殺,生存在太陽和月亮鮮活的傷口里。靈焚說:“對于我,幾乎每一章作品都是一場心靈苦難與掙扎的結局,同時也是開始。”大火一路蔓延,這一路也只有駱駝和馬可能在火焰中生存,只有靈焚可以使林美茂今天依然活著。
三、藍色,火焰在水中燃燒的透明
如果將《靈焚的散文詩》所收入的作品按其編輯順序相反的方向,即從后往前來讀,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直至現在,約四分之一個世紀,基本呈現了靈焚創作的時間軌跡、階段性變化與詩歌精神向度的沖刺。靈焚創作的整個過程的發展演變,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心理階段,或體現為四個心理時期:
黑色時期(約為1984年初前后→1986年底前后):
我把收入該書第二部的“沉思”、“紀念”、“心島”各輯歸入這一時期。從這些早期的作品中試圖捕捉到一絲快樂或輕松,幾乎是不可能的。苦澀、緊張、沉重、憂郁深長,潛藏著一股被強制壓抑的焦慮和恐懼,血在燒,火苗時或躥起。靈焚被籠罩于巨大的母性黑暗勢力中,從一開始就在黑暗中摸索、碰撞、滾打,無可逃脫,過早降臨的苦難,使他對個體生命存在的體驗尤為深切和敏感。
其時,中國的漢語思想正經歷著緊張的尋找出路的階段,很快地越過喧鬧的政治黃昏,仿佛一夜之間就接受了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看到全新的亮光照亮著自我的迷惘。對于靈焚也不例外,他吞下那個時期他所能夠接觸到的所有的新思想、新觀念。很顯然,二十世紀哲學與藝術的主流思潮深刻地影響了靈焚,從他的詩章中,可以聞到《野草》(魯迅)的芬芳,也能嗅出《惡之花》(波德萊爾)、《地獄一季》(蘭波)的氣息,可以看到薩特、加繆閃過的影子,而另一個向度,還可以看出臺灣現代詩人們“橫向移植”與“縱向繼承”成功對接經驗的啟示。
然而,詩藝的探索是次要的,盡管這些作品已顯示了靈焚散文詩的原創風貌并樹立起詩人較為完整的抒情形象,也足以構成對當時散文詩領域的審美突破。我要說的是,靈焚在這一時期完成了他作為個體生命的生存體驗與整體生命存在的理性自覺,使自我得以從生存與心靈的苦難中站立起來,以英雄(“船長”式的)的姿態直面現實,臨淵黑暗。在巨大母性勢力的籠罩中,聚集起一股父性勢力,如巖漿沸騰,激湍沖撞,他的生命蓄積著更為強大的能量等待爆炸和噴射。
紅色時期(約為1986年底前后→1987年初前后):
在短暫的幾個月里,靈焚寫出了《房子》、《飄移》、《異鄉人》、《情人》等一組具有史詩意味的地標性作品。可以想象,巖漿噴發的一剎那是時間的奇點爆炸,而事實是靈焚的“個人午夜時間”與“世界午夜時間”在這一時期開始的某一刻重疊,爆炸發生,巨大光焰中血和骨頭徹底燃燒,而后迅速墜入黑暗的深淵。這個過程極為短暫,但靈焚穿越了整個人類心靈史,在人類精神苦難歷程中,完成了從個體生命的存在體驗升華為人類整體生命的存在體驗的飛躍。在世紀末人類生存的精神廢墟上,悲憤、絕望地吶喊,于黑暗中渴望并熱切地呼喚家園的回歸與新世紀曙光的到來,史詩性宏大敘事構架著生命的整體參照,靈焚站在人類整體的生存高度,超越了政治社會批判,以歷史文化批判的視野重新審視、思考、書寫人類生存的圖景,對人類生存的終極價值關懷進行了“整體性言說”,他的散文詩,成為突入人類心靈恢宏精神史的爆破性行動。
王光明從這些詩作里,梳理出靈焚悲壯“突圍”中的一種基本“情緒”:困獸般的孤獨和無著落感。肖春雷說,這些詩作彌漫著尋找精神家園的悲壯性努力,他借用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的話——“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家園”,指出靈焚的散文詩表現的正是人的生存中的這個最高主題。
紅色,比黑色更黑,是黑色的極致狀態,由血的燃燒形成,是大火吞噬一切之后的黑洞現象。這場大火,靈焚點著自身燒毀了整個世界。
灰色時期(約為1990年前后→2007年前后):
收入該書第一部四輯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第三輯“守望這份無奈”和第四輯“一種嘗試”,構成靈焚灰色時期的創作景觀。
我翻遍了全書,沒有找到1988年和1989年的作品。這是靈焚準備出國和剛到日本的時間,有一千種理由可以說明他為什么中止了創作,但只有一種理由是確切的,那就是1987年夏天到來之前靈焚和他的世界已經燒為灰燼。灰燼包裹著沒有熄滅的火種(靈焚的“情人”——“一種尋求中的在者……一種不可靠近的終極之美,一種靈魂,一種歸宿性的精神指向”),伴隨著他漂泊在異國他鄉、天涯海角。《1990年東京情緒》和《語無倫次,或者病人日記》的章節,靈焚將之輯為“一種嘗試”,與其說是對詩歌形式的一種嘗試,毋寧說是靈焚之不死靈魂企圖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的一種嘗試。那時,他在異國他鄉境遇中的“死灰復燃”——面對大火之后死寂深遠的黑暗,“情緒波動”、“語無倫次”是可想而知的。但可怕的是火種不滅,靈焚的夢還在,思想給他以徹底的悲劇意識的“理性清醒”,而創作——成為他守候家園的無奈:不可棄舍,難以棄舍,而又無法拯救現實也難以馳騁夢境。
灰色迷茫,無奈而深深的隱痛,或許正是人類生存的常態?在“放逐——回歸”的流浪中,這種無奈的隱痛像一團蟻窩附吸在靈焚的靈魂深處,不斷地噬咬著他獲得平靜的夢境,使他在漫長等待的焦慮中時時驚醒。
對于靈焚,十余年靈與肉的分離以及由此帶來的深刻恐懼是殘酷的現實,然而,只有堅持和守候,等待血再次沸騰,火再次燃燒,以一種全新的方式。
藍色時期(約為2008年前后→現在):
這個時期的心理變化或許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在堅持與守候的“無奈”中,靈焚變換轉移審視、思考的經緯和角度,從《形而上問題》開始,宏大敘事成為背景而轉入“生命臨場體驗”,對現實、命運、世界的質問轉為對存在的思索與生命的審美,逐漸趨向純凈、透明。一種火焰在水中燃燒的透明,用火冶煉而出——黑、紅、灰依次后退淡遠,藍色火焰自水面升起,從天空鋪開披風,落下瀑布,清澈透亮中喚醒幽遠深邃。《心之翔舞》,肉體與靈魂赤裸著鳧入藍色水域,時間的節點(“在午后”、“向晚時分”、“入夜”)在這里恰恰消弭了時間的線性和界限,心,自由翔舞,血之火焰就是那汲水的星光,在宇宙中心、時間神秘中心寂靜燃燒。歷史文化作為潛藏的宏大言說背景,“現時”的尋求,生命存在的思索及其意義的探詢,在具體時空節點展開的體驗與審美中得以完成。沒有收入書中的許多作品,如《沖動》、《生命在一天中的幾個片斷》等,更為明晰地體現出這一追求的趨向。
藍色,靈焚之夢的顏色,自然和時間的本色。靈焚顯然已經走出黑色的痛苦憂郁、紅色的憤怒焦躁和灰色的無奈隱痛。而《風景如海》則顯示出浴火重生的靈魂重新面對世界和人生的從容、豁達與莊嚴。內心敞亮,心理走向清靜寬容——對自我的、他者的和整個世界的。這個巨大轉變,靈焚給我們以波瀾不驚的平靜表象,只有他自己知道其間歷經多少驚濤駭浪。或許,這是拯救的一種姿態?靈焚不相信神,但他卻以基督的寬容姿態來俯瞰人類和這個世界,潛藏著不易察覺而又自然流露的救贖情懷。從“宏大”轉為“細節”,從“永恒”轉為“瞬間”,換一句話說,以“細節”呈現“宏大”,以“瞬間”捕捉“永恒”,“形而上”與“形而下”互為對立生成,虛與實辯證的觀照、省思與揭示,這一時期,靈焚的追求絕不僅僅是創作姿態與策略的改變,其自我的變化升華也已絕非早期黑暗迷茫中燃燒的生命個體,更不是灰色守望中“等待的戈多”,人,在趨向永恒終極在者的追求過程中,已然作為自由的在者,“在思索中揚蹄,在審美中自足”。
四、貧民王子的“血的方程式”
從黑色到藍色,穿越荒原和寒冷極地,走過赤道,而后進入海水(天空),靈焚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火種不滅,一路孤獨痛苦歌唱,歌唱孤獨痛苦。
鹽堿灘上隨意生長的一棵無名植物,靈焚,這個貧困農民的兒子,這個“物質生活短暫的情人”,早期選擇了“詩歌王子”的前行道路,火的道路,赤道。且再聽一聽紅色時期的聲音,那痛苦哀傷的傾訴、那躁動憤激的述說、那悲壯雄辯的宣言,還有絕望的巫師般的咒語,那些歌聲從一團大火中傳來,只要我們輕輕一吹,我們手中的紙頁將呼地一聲點著,并即刻化為灰燼。
這個貧民的“詩歌王子”,從我們民族詩人的家族譜系中,還很難找到清晰的脈絡,他那些風花雪月的古典意象,仿佛不是他骨頭里長出來的,只是他飲露食花、臨流悲嘆時從腸胃里吐出來的,倒是那些變形的超現實幻象更像是他的嫡生。這個貧民王子,站在火光中,使我們看見了一些熟悉的身影,那些在赤道邊上或者就在赤道上行走的、佩戴著火焰桂冠的親切身影:梵高、葉賽寧、荷爾德林、雪萊、普希金,好像還有卡夫卡。他們一一走過大火,他們多么相像,猶如兄弟。靈焚跟在這一群兄弟后面,通紅著臉、撕扯著嗓子歌唱,不,確切地說,更多的時候是喊叫,是噴發。
一場大火,血燃燒,月亮與太陽燃燒。靈焚以其對抗性存在中的堅韌決絕和永不放棄的夢幻渴望,即駱駝和馬的神性,獲得了存在的尊嚴,從而讓我們看到黑暗中的一絲光亮;世界的午夜,在神性缺席的黑暗中,“荒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這微妙時刻,人回歸到自己的生活之中”——靈焚以西西弗神話所包涵的意義,在命運的限度內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讓我們對生命價值與存在意義的獲得依然充滿希望。
無論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對靈焚有多么深刻的影響,也無論靈焚奇崛怪誕、撲朔迷離的意象謎團,大火燃燒或云譎波詭的詩章叢林,及其象征、超現實手法與現代主義有著怎樣的淵源關系,但靈焚所作的努力,其精神向度的極限沖刺與詩藝探險鬼斧神工的境界,絕不是簡單的模仿能夠達成的。站在西方現代文明破碎不堪與東方文明衰微虛弱廢墟的十字路口,企望更深刻地印證現代人的存在本質,尤其是對被歷史所抉擇又為時代所忽視,無可回避和逃脫地卷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與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遭遇戰的一代人(六十年代生人),其靈肉撕裂、悲壯突圍、孤獨放逐,為尋找家園而掙扎、搏斗的慘烈心靈歷程的揭示,傳承與創新,靈焚得益于魯迅《野草》精髓骨血的滋養,和臺灣一代前行詩人在東西方文化撞擊合媾中“原質根性”對接成功經驗的啟示,更帶有一代人背負歷史使命奮力探索的深切印跡。
靈焚“血的方程式”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這個貧民王子,生長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詩經》和《楚辭》兩條大河喂養過他,儒道精神深埋骨血之中,通過他詩章中血液流淌跳動的清晰脈搏,已然讓我們把摸、傾聽到了他的歷史之思、時間之傷和文化之鄉愁。
靈焚作品兩個意象系列的沖突:古典與現代變形的幻象對應了靈焚對抗性存在的心理狀態,交織著愛恨、悲喜、善惡、美丑、時間與空間、駱駝和馬的矛盾糾葛、對立統一,“我”和“你”(“我”和“情人”、對象)、水和火(內心大火燃燒,而作品出現大量的水的意象)、生和死、靈魂和肉體、男人和女人、現實和夢幻的沖突與和解,來自他的心跳,他的呼吸,是血液流淌循環奔騰的節奏在語言詩句中自然而鮮活的呈現。這種節奏,即陰與陽、白與黑的二元對抗與和解,是老子和莊子于冥冥自然宇宙中最先聽到的萬事萬物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深奧曼妙的音律。在靈焚的作品中,小到一章,一章中的兩個小節,一個詩句的兩個意象,甚至一個意象的兩個涵義之間;大到一組,甚至全書各部分、各輯之間所形成的系統張力,都顯示了這一節奏靜止而又流動、開放而又封閉,首尾相接、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的特質,及其奇絕跌宕、簡潔諧美的審美效應。
節奏的產生先于語言,人類的全部宇宙觀都從對原始節奏的直覺中來,不同區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有著不同的節奏直覺,從而產生了不同的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和面對世界的不同理解。帕斯把詩歌節奏同宇宙和原型、陰和陽、結合和分解聯系起來,在其著名詩歌論著《弓與琴》一書的“節奏”一章中對比了不同文化的節奏觀:“在任何文化背景中都可以找到人類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在宗教、藝術和哲學的創造形式表達之前,這種態度總是通過節奏表現出來的:對于中國人來說就是陰陽;對阿茲特克人來說就是四重奏;對希伯來人來說就是二重節奏。希臘人把世界理解為對困難的斗爭或調整,我們的文化充滿了三重節奏……每種節奏里都包含了一個具體的世界觀……節奏,即形象和涵義,是人類面對生活的自發態度,它并不游離于我們之外:節奏就是我們本身,它就是為表現我們而存在的。它表現了具體的時間性,表現了不可重復的人類生活……”
陰與陽,這一節奏作為一種文化基因無疑流傳于我們的血液中。我在想,我們常說的“悟性”,或許就是感覺此一節奏的能力或智慧,“悟”,就是對節奏的傾聽,在傾聽此一節奏的直覺中獲得知性的敞亮。靈焚在談到他創作狀態的情形時曾說:我的詩歌創作往往起于突然冒出的一個意象性詩句,我寫下這個句子之后,根本無從知道接下來是什么……顯然,靈焚的靈感源于他的悟性,而他在不知道接下來是什么的停頓彌留時刻,就在傾聽,傾聽心跳、呼吸,傾聽自我(內在小宇宙)和世界(外在大宇宙)的神秘律動,由節奏統攝引領,展開“細節”和意象聯想、想象的魔法,使節奏、形象和意義同時存在于一個緊密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中,從而建構起他的散文詩自足天地,完成他的散文詩藝術的探險作業。
靈焚的創作極為習慣地捕捉時間的節點,換句話說,靈焚的作品中出現大量的時間節點,甚至為數不少的作品就是以時間節點為題。可以肯定這是靈焚創作中的不自覺現象,但在這里恰恰表現了具體的時間性,表現了生活的不可重復性,靈焚的這一“臨場體驗”——“深度時間”透視及“文本時間”對“肉體時間”的超越,使生命的審美和意義的表象于“瞬間”與“永恒”的對立中獲得辯證的揭示。而我要說的是,靈焚的這種不自覺現象的產生,恰恰由他的節奏直覺和節奏意識所致。
在創作的早期,這一節奏是自然的流露,而在后期則體現為靈焚有意識的自覺追求,他甚至將這一節奏特征從創作方法和技巧上進行了辨析界定,梳理出散文詩區別于詩歌和散文的美學原則。對抗性存在的沖突與和解,在這里不僅有靈焚的美學原則,更重要的是在這里包涵了他全部的體驗、感悟,觀察、思考,審美、揭示。關于靈焚和靈焚的散文詩,從不同的角度和向度諸多名家已有過精當而充分的評論,在這里,我如此強調節奏的作用,重視節奏對于靈焚的重要性,是因為,一方面,它對靈焚進行了一次文化基因的必要檢測,其結果很精確地詮釋和證明了靈焚的“血的方程式”;另一方面,我確信:靈焚所提供的散文詩藝術文本,是漢語思想、語言的一次具有拓荒性、開創性意義并卓有成效的嘗試,讓我們看到漢語詩歌現代性的光明前景。
五、詩歌幻象,駱駝和馬合為一體
面對熊熊燃燒的大火,落日黃昏輝煌的景象,我再次看見駱駝和馬的身影在火光中穿行,這一次,輝煌的光焰卻讓我于恍惚間產生疑惑:我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走進了靈焚和靈焚的散文詩?或者說,我的閱讀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靈焚和靈焚散文詩的“真實”?
最好的途徑當然是靈焚自己直接而明確的詮釋:
“那么,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有哪一片土地屬于自己故鄉呢?除了以無可奈何的微笑或者以停止判斷后極致的單純和天真認同家園;在每一個瞬間追逐生命的縱情表象;在同樣喪失了自己的他者中確認渴望著的自我,活生生的自我。我們已別無選擇,永恒已不存在。或者說這就是永恒,用盡可能對于感受和直覺來說屬于準確的語言表象生命與情感的意義,把生存的境遇展示得平靜與體認,絢麗而安詳。
所以,我以無垢的真誠擁抱文學,堅持著以散文詩記錄心靈的真實,思維的律動;嘗試著在這種述說方式——散文詩——中,每一次確定一種人稱的對象朝向,為自己的述說定位,然后在區別于散文的抒情與描寫中,展開理性、情感與審美的意象性細節,在這種細節群的疊合、鋪陳、提煉、收縮中凸現出散文詩區別于詩歌和散文的美學特征,呈現一種屬于散文詩的話語性審美體裁的建構。通過散文詩,構筑一座人稱、細節、諦悟的生命回響長廊。”
這段文字靈焚清晰地闡述了他的“思”與“詩”,引導我們走進他的世界——“人稱、細節、諦悟的生命回響長廊”,讓我們盡可能地接近他的“真實”。但我想說的是,這種理性的“述說”遠不及靈焚的作品和靈焚的生命存在本身來得鮮活生動,充滿奇異豐富的意味與復雜深刻的意蘊,從而使人產生趨近和進入的沖動和愿望。
大火中駱駝和馬的生存幻象,宣喻了靈焚的個體生命存在的奇跡所涵蓋的寓言性意義:在苦難生存的不幸境遇中,與悲劇性命運作艱苦卓絕的抗爭,以本能和血的呼聲回應生命的孤獨痛苦;在世紀交替千禧年回歸的黑夜,點燃自身而企望照亮黑暗的前景;在人類文明的碎片與盲目中,通過自我的解構與重合渴望重新確立與世界的關系;在人類精神遠征的沙漠荒原上,通過悲壯的家園尋找宣告家園的不復存在,而只能“以無可奈何的微笑或者以停止判斷后極致的單純和天真認同家園”……靈焚以一種現代人崩潰散失的意志力和血液中喚醒的原始力量掘進突入自我和人類的心靈腹地,將經驗生存不斷向幻象生存超越,從“自我”人格煉獄中提升出“一代人”的英雄形象,而“西西弗神話”原型在駱駝和馬的重合中(即在靈焚身上)重現,從肉體到精神,從“世俗時間”躍向“文本時間”,靈焚“尋找情人”——“人類的所有精神的苦難性努力”——的歷程,則已潛藏著靈焚渴望著獲得進一步的升華,達成修繕人類整體人格,提升整體人類精神的企圖。
黃昏落日輝煌的景象背后,詩歌王子們在夜色中列隊前行,更遠處,我仿佛看見了歌德和但丁閃過的背影,深邃高遠的蔚藍夜空閃爍著星座的光芒。
海子說:“偉大的詩歌,不是感性的詩歌,也不是抒情的詩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斷流動,而是主體人類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是主體人類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詩歌行動。……但丁將中世紀經院體系和民間信仰、傳說和文獻、祖國與個人的憂患以及新世紀的曙光——將這些原始材料化為詩歌;歌德將個人自傳類型上升到一種文明類型,與將神話宏觀背景的原始材料化為詩歌,都在于有一種偉大的創造性人格和偉大的一次性詩歌行動。”
我在想,用點燃自身的一場大火向真正偉大的詩人致敬,以詩歌王子噴射燃燒的熱血向詩歌王座沖刺,以現實生存的徹底失敗去換取詩歌的最后勝利,是否就是“這一代詩人”(六十年代出生)決絕追求的一種幻象生存?!海子如是,喝下《世界的血》的駱一禾如是,靈焚幾乎走在同一條道上。
大火燃燒,靈焚經歷著《地獄一季》,大火光焰誘惑和逼迫我們走向他的苦難和悲劇性命運時,遭遇與他的靈魂對視與心靈穿透就成為無法逃脫的“劫難”,好在靈焚依然存活,并給予了我們相應的撫慰和喜悅:火依然在燒,在時間水域的寂靜中心,此刻馬與駱駝已成為一體,藍色席卷而來之時,喚醒天空、大地,草木、河流,喚醒我冬眠已久的詩歌幻象:
那么就讓我們出發吧
從我們失而復得的一棵植物里啟程
收拾好秋天的落葉
收拾好黑夜的星光
收拾好我們碎落一地的骨頭懷抱一束露水晶瑩的野花像一把琴
那么就讓我們出發吧
從五月的河水順流而下
兩岸芳草青青兩岸鼓點隱隱
那些流浪的藝人從四面八方趕來
陸續來自山岡和平原上的眾人齊集河畔
那穿透五千年時光蒼涼優美的號子歌聲正輕輕哼起拂曉即將來臨
走吧讓我們放下手中的活計
放下肩上的包袱
讓我們掩埋好親人的尸骨、故鄉的碑文
讓我們摘下月亮的舊馬燈
備好馬匹、糧草、留傳的古經書帶上老人、孩子和女人一起出發
走吧讓我們乘著夜色還未消退
點燃灰燼中那不曾熄滅的火種高舉火把
穿越大地碎裂的頭顱幽昧子宮
穿越山頂洞、莫高窟、金字塔狹長的隧道
走吧讓我們邀請山川草木、飛禽走獸
邀請四大河、五大洲不同膚色的兄弟一起出發
拂曉即將來臨
讓我們以神的名義再次命名我們為人類
讓我們高舉火把引領眾人齊唱荷馬向著黎明、向著太陽一起出發……
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靈焚的幻象,或許靈焚早已走得更遠,他當下有關詩歌話語的行跡愈發顯示出他的詩歌行動的未來野心,無論成或敗,我們都只能一如既往地關注他,并致以深深的祝福!
火依然在燒,沒有熄滅的可能,水域寂靜之火,藍色瀑布,靈焚會為我們帶來新的驚奇和喜悅,讓我們靜靜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