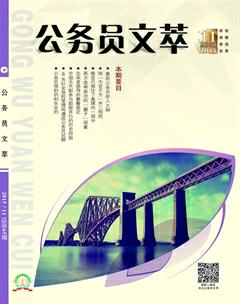“農民市長”李豆羅的田園夢
韋星

和李豆羅“認識”,很偶然。
5月的一天,微信朋友圈里,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惠州市旅游局局長黃細花轉發了一段視頻,并配有她的評語:這是我們江西人的驕傲。
出于好奇,點擊進去。視頻中,一位老人正登臺表演,勸募新農村建設所需的資金。
老人名叫李豆羅,69歲,是南昌市原市長。
休政歸田
李豆羅的家在西湖李家,這是進賢縣前坊鎮下屬的自然村。村里有李、黃、胡、萬四姓,共2000多村民,95%以上屬李姓。
600多年前,他們祖先在這個濱湖丘陵的村莊里,世代以農耕為生。人均耕地僅一畝多。現在,很多人對這些歷史不感興趣,他們津津樂道的是:2010年1月22日,李豆羅最后以南昌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身份做完報告后,旋即回到家鄉犁田。
這時,距離他上午做完報告,只有4個小時。
很多人做不到這點,特別是領導干部。他們即便退休了,仍爭取到官方協會謀一官半職。否則,—下子沒人請示匯報,內心空空的。李豆羅不是這樣的人,他說,退出官場后,他做到了“四不”:腦子不想,耳朵不聽,眼睛不看,嘴巴不說。
甚至,南昌電視臺、江西電視臺,他都不去看了,看到就換臺。他說:“電視上面都是熟悉的人和事,忍不住去想一些問題,所以干脆不看。”晚上,他主要陪孫女看動畫片。白天,則要忙于新農村建設。李豆羅的新農村建設,是一場讓傳統回家的建構,他要讓傳統的禮儀和文化回歸。
這有別于很多地方大力提倡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他帶領村民走的“新三化”,即“山水化、田園化、農耕文化”。
2006年,還在官場時,李豆羅就已推動這事。不過,當時忙,他主要通過電話遙控的方式,讓村干部貫徹實施。
李豆羅喜歡琢磨事,而且講話都是一套套的。他還喜歡用通俗易懂的順口溜來總結。一次,他回村發表動員講話,回應西湖李家要打造怎樣的新農村時說:“我們新農村的宗旨是:傳承中華文化,恢復古村精華,重墨青山綠水,美我故鄉天下。”
老百姓未必聽得懂,但他們認為,市長見多識廣,跟著走應該就對了。問題是,如何下手?
李豆羅和村民一次次描繪西湖李家新農村的特色,就是做出“紅石路、馬頭墻、碧綠水、滿村樹”的調調來。這時,一些人似懂非懂。后來,李豆羅干脆把宋代著名詞人秦觀的《行香子·樹繞村莊》給打印出來,釘到村中祠堂的墻壁上。
看著這首詞所描繪的“……桃花紅,李花白,菜花黃……鶯兒啼,燕兒舞,蝶兒忙”,村民明白村里就是要打造這樣一張“秦觀圖”。
問題是誰來干?和很多農村一樣,村的年輕人基本外出打工了。李豆羅將目光鎖定在西湖李家籍的公務員身上,特別是退休的公務員。他尋思著:一來,這些人素質高,能很好理解自己;二來,這些人經濟有保障,可全身心撲到家鄉建設上。
這樣,西湖李家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團隊,除了李豆羅和他夫人,還有進賢縣人大常委會原主任黃華明、進賢縣衛生局辦公室原主任李旺根,以及前坊鎮副鎮長、西湖李家村支書李新華等人。
這些老干部盡管家在縣城,但落葉歸根是共同心愿,他們希望發揮余熱,把家鄉建設好。深具號召力的李豆羅,剛好可以把他們這種心愿凝結起來,演變成行動。
改變的代價
新農村建設不只是鋪路、裝飾房屋外墻這么簡單,它還涉及對村民傳統行為習慣的沖擊,一開始就伴隨著不適應,也遭到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反對。
拆掉各家各戶牛棚后,為方便群眾關牛,李豆羅在村子四周建了4個牛棚場。和以前相比,人畜分開居住,人居環境自然好很多,村里也變得干凈了。但關牛、喂牛,沒有過去那么方便了。
村里修路時,一些地方設置了臺階,看起來更整齊、美觀、防滑,但老百姓要干農活,有時候,他們拉著板車通過,就不大方便了,所以他們也有一些意見。加上早期,村里沒路燈,新修的路,村民還不熟悉,摸不準哪些地方上下臺階,因此會滑倒,這引發個別村民不滿。不過,坦白講,路比以前好走多了,只是村民的習慣需要磨合期。另一種習慣是,隨手扔垃圾,如今規定到統一的地方去倒,村民也感覺不方便了。
“過去是自選動作,如今是規范動作,一輩子的習慣,村民很難—下子適應。”李豆羅說,“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是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問題,但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2010年退休后,李豆羅就在村里居住,他們夫妻住在村邊林場的一間公房里。白天,李豆羅會會朋友,找人捐助,或開著他那部破車,四處巡查工地。
李豆羅還有更大的夢想,他要在西湖李家打造一座農博館,里面設有米鋪、茶鋪、匠鋪等等,以此展示農耕文化。他說,他要把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都濃縮在這座農博館里。
這需要很多資金,所以,李豆羅常調侃自己,“我成了南昌最大的乞丐了”。
辛勞付出的,還有他那支由老干部、村干部組成的團隊。前幾年,剛起步時,他們沒日沒夜在村里種樹、除草、請人翻修村里的老房子。長期以來,他們和家人兩地分居,逢年過節,村里搞活動,也沒辦法回家團聚。
即便這樣,村民們也不一定都感激他們。
錢多嘴雜
不感激,和“一定搞了很多錢”的猜疑有關。
搞新農村建設前,李豆羅就囑咐黃華明管好錢,不能出亂子,“否則是要倒霉的”。為此,黃華明想了一周,沒睡好。最后,他建議:一、所有資金不能進西湖李家。二、西湖李家不設會計。讓鎮財政所管賬,信用社管錢。其中財政所所長當李家的會計,財政所會計當李家的出納。募捐到的錢,賬到鎮財政所,現金到信用社。李豆羅批準了這一方案。
支付工程款的流程是,黃華明等人簽字——前坊鎮鎮長簽字——鎮財政所開轉賬支票——當事人拿支票去信用社提現金。
這樣,除了當事人,沒人能碰到錢。西湖李家的錢,不是一個人就能拿到的。“你不這樣做,別人會說你拿了錢。”黃華明說,“前幾年,很多人以為我們搞了錢,但清楚流程后,就都不說話了。”
新農村建設中,為避嫌,西湖李家的人可以打工,但不可包工程。這也得罪一些村民。不過,村民打工是有錢拿的,但這幫老干部——包括李豆羅和他夫人,是白打工的,沒領村里的錢。
即便這樣,還是有村民和李豆羅說:“老板,搞了這么多錢回來,如果分給大家(不搞建設)的話,都發財了。”
李旺根聽后,搖搖頭。
李豆羅早年在進賢縣委做書記時,村里的小孩讀書交不起學費的,他都會給校長打電話申請緩交;有人生病住院了,他再忙也會到病床前站一會,所以深得民心。
不過,如今的李豆羅卻說:“回到村子以前,沒幾個人說我壞話。回到村子以后,沒幾個人說我好話。”
村里有家飯店,外面的人來吃飯了,看著端菜上來的中年婦女,會問一句:“這飯店是李豆羅的老婆開的嗎?”有的會問:“這些房子都是李豆羅的嗎?”
他們問到的這位中年婦女,就是李豆羅的夫人胡桂蓮。胡桂蓮告訴《南風窗》記者,有時挺氣的,但還是憋住解釋說:“飯店是村集體的,收入都入賬。這些房子也是集體的公房。李豆羅只有60平的祖屋,算是村里最小的了。”可是別人不相信。
胡桂蓮有時也很郁悶,甚至會對李豆羅發脾氣,但李豆羅總安慰她說:“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感覺他就像神一樣保護我,從來不生我的氣。”說這話時,胡桂蓮像一個還處在戀愛中的女孩一樣。
不過,人心確實變了,現在似乎做什么事都難,做好事也是如此。更多的時候,解釋,已沒有了意義。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