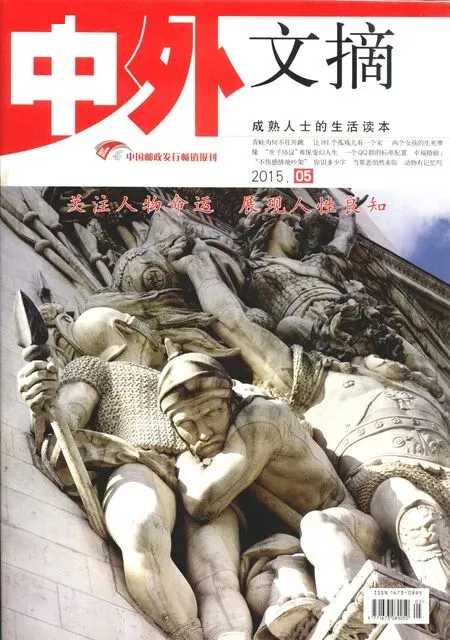當罪惡悄然來臨
當罪惡悄然來臨
□ 劉 波
小時候讀歷史故事書,常常感慨為什么古代的皇帝那么“笨”:明明是“奸臣”,卻非要寵信,明明是“忠臣”,卻非要疏遠,乃至迫害,也常常想,假如我是皇帝,一定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只要始終信用忠臣,國家一定會長治久安。長大后,讀了更嚴肅的歷史書,才慢慢意識到,所謂的“忠”與“奸”并不像戲曲舞臺上的紅臉白臉一樣顯明昭彰,王朝的衰敗,也不像道德化的傳統中國史家所宣稱的那樣,都是寵信奸佞導致的結果,通常的情況是,渺小的人受大潮的裹挾,無能為力。
問題是,現代的成熟的成年人,真的不會在更復雜也離我們更近的問題上,有類似的幼稚想法嗎?希特勒的德國也許是個好例子。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導致納粹德國興起最大的罪魁禍首,一直被歸為英法美的綏靖主義政策。全世界幾乎會公認,當年綏靖政策的低級和愚蠢是明顯可見的,這種“事后諸葛亮”式的聰明,好像是不證自明,而當年與希特勒妥協的英國首相張伯倫等人,也似乎已經坐穩了“歷史笑柄”的位子。
事實上,當時許多非常明智的人,都對希特勒政權有著極為混亂的認識。曾任美國《新聞周刊》駐外總編的安德魯·納戈爾斯基的《希特勒的土地:美國人親歷的納粹瘋狂之路》(重慶出版社)一書,在某種意義上說,其主題就是,記錄當時人們對希特勒看法的困惑、混沌與互相矛盾。不過,納戈爾斯基選取的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身處德國的普通人,從他們的視角來回溯希特勒的崛起歷程,以及他給德國社會帶來的變化。
即使在希特勒已經緊鑼密鼓準備戰爭的時候,許多非常睿智、非常了解德國的觀察家,仍然對他抱有幻想,對和平抱著一廂情愿的虛幻期待。比如,直到1939年5月,就在二戰全面爆發前幾個月,曾在1920年代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美國記者韋根還在美國媒體發表長文分析說,希特勒幾乎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實際的威脅,因為他不大可能用他“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做賭注來冒險。
這并不奇怪,在本書最精彩的一個段落里,曾在德國做記者、后來成為著名播音員的霍華德·K·史密斯總結了外國人認識希特勒德國的四個過程,以此說明德國的迷惑性。首先,即使是很多堅決反對納粹的人,到了德國之后,都會被第一印象迅速征服,在心理上繳械投降,因為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在表面上整潔優雅,井然有序,不由得人不心生好感,尤其是英俊瀟灑,身穿制服的德國男人,對女性頗有殺傷力。到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意識到,這是個制服和槍支構成的國家,正處于高度戰備狀態。第三階段是,你會嗅到危險,你會認識到,這些干凈整潔的人,只要一聲令下,就會變成殺人機器。第四階段則是一種至為深切的恐懼:這是一股全世界迄今沒有見到過的陌生的黑暗力量,對文明社會本身造成了真實、直接而迫切的威脅。但可惜的是,大多數人都會停留在前兩個階段。
(摘自《經濟觀察報》)